《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是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根千枝出生于1926年,是首位担任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学士会会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女性。她主要研究印度、西藏和日本社会体系,创建了著名的日本“纵向社会论”。
作为日本较早涉及印度田野调查的书籍,《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被认为提高了当时日本社会对异文化的关心,其世界范围的调查和将调查理论化的行动力获得了高度评价。这本书自1959年在日本出版以来多次再版,今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它的中文版。
在自序中她开篇就强调:
本书集中了在1953年6月到1957年8月之间,我从印度到欧洲的留学记录。这一记录不是研究报告,也不是探险记、旅行记,而是我在研究、旅行途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素描。
…… ……
这些素描是我通过对访问地人们的面貌、行动、人际关系、思考方式等的观察,进而来理解和思考简单社会和文明社会等问题的结果。
尽管书中近一半的篇幅写到印度未开化地区的土地制度、家庭结构、婚姻关系,但如作者所说,它并不是田野调查的研究报告,它其实是一本个人随笔,记录了作者在印度未开化地区以及欧洲的瑞典、英国、罗马和希腊、埃及等地学习研究时的见闻。它的视角,是社会人类学女性研究者的视角。它的笔法,是文学性的,简洁内敛而又繁复饱满。它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提起的追问,依然尖锐地刺中我们今天的现实。
女性研究者的视角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根千枝从读小学高年级开始,在中国北京生活过六年。后来在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学习时,她发现,研究中国史的老师们对中国的印象,与她在北京生活时看到的、感受到的完全不同。老师们是根据文献来研究中国,她认为这样无法了解真正的“活的社会”。于是,她开始查找什么学科研究“活的社会”,结果找到了“人类学”,走上了人类学的研究之路。1953年,27岁的中根千枝获得印度政府的奖学金,前往印度阿萨姆地区、喜马拉雅地区探险、调查、研究,后获得瑞典财团的奖学金,继续调查研究印度母系制度。而后赴欧,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在罗马师从西藏学权威杜齐(Giuseppe Tucci)从事藏学研究。
《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它当然首先具有社会人类学研究者的视角,有对印度未开化族群社会结构、婚姻制度的调查,也有对印度人、英国人、罗马人等人群特征的把握、对照,包括与日本社会、日本人特征的比较。作者的视线并不仅仅投向专业领域,她灵敏细致的女性视角,为这本书抹上了一层真实可触的感性魅力。
女性研究者比较容易有一种故意掩盖甚至抹杀性别特征的倾向,也许是为了在以男性为主的环境争夺平等的话语权,不授人以女性“情绪化、多愁善感、幼稚浅薄”的口实。而在这本书里,中根千枝既保有一名社会人类学学者的专业素养,同时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性视角,不回避自己在田野调查中所感觉到的情绪、情感的波动和变化。
“乡愁”这个词和情绪多次在书中出现。她在印度热带丛林艰苦的环境里真心享受着自己的小帐篷,声称即使王侯贵族的宫殿也不愿与之交换。又坦言,经过两三个月和未开化人的生活后,也开始浮上一股思念“文明人”的乡愁。体会到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所关心的事情、喜怒哀乐和“文明人”有本质的差别。文明人的抽象化思考、意志上出现的烦恼和为了解除精神压力和痛苦所进行的平衡训练,在未开化地区人们日复一日循环着的单纯生活里,无法取得共鸣。但她一旦回到文明人之中,又会对文明人的抽象思维、含蓄的言谈感到不适。
她也曾在欧洲想念印度,也曾在雅典进入某个酒吧的瞬间,涌上对欧洲的乡愁。四年多国游学的研究结束,在加尔各答机场办理手续,看到自己的行李上贴着的“东方”的标签,她惊喜地感受到那是自己迫切想回到的故乡,同时又对将要结束快乐的异国之旅矛盾的依依不舍。
她所体会到的文明的“乡愁”,并非一个文明人身处未开化人群中的孤独那般单薄。它也包含着那些带着未开化地区的影响痕迹回到文明社会后的不适和再认识,还包含着在文明社会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穿行时辞旧迎新、迎新怀旧的心理调适的艰难。
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她跟当地一个官员去猎虎那一段,给人留下至深印象。月光下、村落的人们围着篝火狂饮狂跳,她感觉到官员那“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印度文明所孕育出的神秘深渊中的热情和奔放”,记下了自己“像热带丛林中的小鸟那样自由生活的野生的喜悦”,还清楚地看到“他的魅力形成于成熟的孟加拉文化和欧洲式的教养以及野生的世界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再次确认不仅要领会未开化人的心,也要认识在东京长大的自己本身。不吝且不贪恋女性视角的叙述、女性心理的描述,不忘研究者立场的分析。这一段猎虎体验写得热情又冷静,给人非常“惊艳”的阅读体验,常被读过的人提起。
另外,当她观察描画所接触到的女性时,也是以女性的目光去打量的。富于素养学识的喜马拉雅公主、加尔各答夜总会里的各色女人、热情怪异的罗马的房东老太太……都被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书的最后写到,与落到以乞讨为生依然坚持研究西藏佛教的法国女性研究者重逢,中根千枝在她身上看到一种纯粹,也看到自己的罗曼蒂克已然消失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雄心壮志不是没有,而谋生是需要条件的,况且眼下的研究是成功的……讲别人的故事,照映自己,谈女性研究者的不同遭遇和道路,带着几分淡然轻愁为这本书作结,余韵深长。
文学性的笔法
《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1959年由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作为优秀的随笔得到了很高评价,获得了该年度日本每日出版文化奖。书的内容曾出现在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的日语和社会学科的试题,还常常被面向外国人的日语教材引用,足证其文笔之典范优美。
在这本书中,中根千枝并没有像其他专业研究者一样,以专业研究习惯,时刻注意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对所见所闻作深奥刻板的简单记录。因为没打算写成研究报告,她的笔法是富于文学性的。
她善于写景,尤其善于捕捉景色中的光影变幻和灵动的一瞬。在船上逆流而上,去往随时可能被野象群袭击的未知世界,她看到了“热带丛林树木的倒影映在河流的两边,美丽的热带鸟,展开鲜艳的双翼,随着我们飞来飞去。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浪花四溅”,还看到“在前方浅紫色的桃拉山系的衬托下,船工红铜色的身体如同一幅动人的剪影”。她不厌其详地描述月光——“月亮从东面山上出来,明亮的月光照射着周围的一切。……到处都是一片冬天的景象,高高的树梢上树叶几乎落完,在月光的沐浴下,耸立在忽明忽暗的天空中。我们的影子在月光的映照下落在地上,骑在鼻子长长的象背上的人影如同在梦中晃晃悠悠地走着”,描述月光下的心境——“在皎洁的月光下,黑沉沉的喜马拉雅山那边的银色的克钦佳卡折射出来的魅力,会让人忘掉人世间的一切,就如同天上的神的星座一样,在蓝色的夜幕下呈现出动人的丰姿,我的魂都好像被它勾走了”,也记录在景色中响起的各种灵动的声音——“当夕阳西下,如果漫步在罗马街上,脚下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和教堂传出的钟声在古老的街道上交织在一起……在教堂的钟声深情地沁入街头匆匆而过的忙碌的都市人胸中的那一瞬间,不可遏制地切身体会到欧洲的美丽和魅力所在”。
写人时,是内敛简洁的——她全身黑色装束,帽子、外套、袜子、鞋子、手提包等都不例外。她上楼时,总要耸耸肩,穿黑袜子的脚从长长的外套中突然就露了出来。从后面看她那样的连续动作,就好像魔女似的。细脚往外一露,两肩非常明显地耸起,脖子也缩在里面。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走的样子,不禁让人想起已经捕捉到了猎物、非常高兴地返回洞穴的魔女那种急不可待和可怕的笑容。
写人群时,又是繁复饱满的。在巴扎的入口处。喇嘛坐在路口念着经,好像在化缘。旁边有一座印度教的小庙,对面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群人在听新教徒的英国牧师用尼泊尔语扯开嗓门大声传教,并用藏语写上圣经的语句送给赶巴扎的西藏人。而在这些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中,身穿黄色衣服的小乘佛教的僧侣静静地托着钵从中走过。随后,天主教的神父和穿着黑色僧衣的尼姑也从中穿过。前来朝圣的贫困的西藏人常常从印度教徒的尼泊尔农民那里得到大米和蔬菜。这一切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境界,创造出边境城镇充满活力的气氛。
这种有温度的文学性描述方式,与我们预设的人类学硬邦邦的理论文字大不一样,有落差,得惊喜,因而大放异彩。
文明要往何处去
毋庸讳言,时隔近六十年,《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中的记录和描述,也有距离今天的现状十分遥远的部分。
比如书中写到英国,看到乘电梯的人们都一律靠左站,把右边留空,作者感叹“除去英国人,哪里的社会能这样呢?”我们知道,日本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虽然这种习惯其实是一种有违电梯安全的习惯。像英国人那样“遵守规矩的文明人”已经越来越多,遵守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和社会性的规则、遵守时间,已经是社会文明发展所趋大势。可是,所谓文明必定指向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恪守时间吗?反之,就是不文明吗?
作者写到了生活在“悠久”中的印度人。他们不守时,交通工具不按时运行,时间散漫。但她认为,说印度人没有时间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印度人的时间与我们所说的时间不一样,印度人的时间是宇宙的时间,而不是钟表上的时间。印度的人们没有诸如5分、10分、1小时等这样的时间观念,他们拥有的是被恒河象征的所谓“悠久”的时间的观念。他们关于时间的观念和度量单位不同于钟表,基于印度哲学“梵”的思想。印度的哲学以个人为中心,自己和宇宙置于同一中心。所以对他们而言,报纸迟一些看到、新闻晚些时候获知,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等朋友的时间可以享受等待的快乐,帐篷可以晚点搭,先喝茶享受清谈的快乐。比起时间来,人类是优先的。“和他们相比,我们不正是被时间追赶的时间的奴隶吗?”她一边指出这种不守时在现代社会造成的工作效率低下,也向所谓文明人抛出了一个个犀利的问题:
住在现代公寓、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平均所得是当时日本人的五倍的斯德哥尔摩人,为什么依然叫穷?到底什么才是贫穷呢?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的追求的欲望变得更强,而精神生活变得非常贫乏,这难道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像瑞典那样有惊人的社会福利保障,对人类来说究竟是好是坏呢?没有事干,只是活着,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与未开化?当社会和平安定,男人失去野性和阳刚之气变得柔弱,只能是一种必然趋势吗?人类如何同自己创建的高度发展的环境相对抗,会不会被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抛弃、灭绝?
这些问题,依然能刺中我们今天的现实。各种媒体每天都在提醒我们,在物质上已然高度发展的今天的社会,人心浮躁、道德缺失、精神世界荒芜等精神失衡现象随处可见。是物质文明走得太快,还是精神文明太蹒跚?物质高度发展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弱化么?人类最终是落入一个无欲无求的世界,还是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消灭?
中根千枝说:“我绝不想解决问题和得出结论。这些内容想必每个读者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去领会和接受。”领会未开世界的模样,追问文明世界的模样,思考世界应有的模样,也许就是这本书想要的模样。
(作者系旅日汉语教育者,日本文化类书籍汉译译者,致力于中日之间语言文化上的介绍和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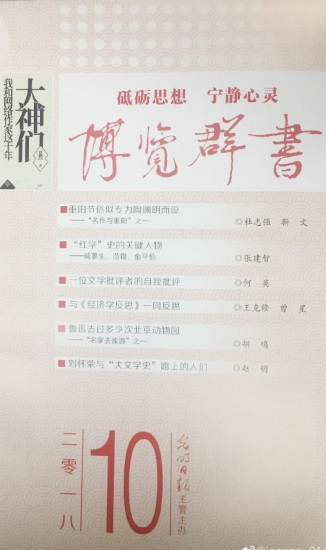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