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山,泰山名气最大,作家登泰山、写泰山的也最多。这样就给雄伟泰山增加了另一道人文风景。同时,泰山本身又成为一面镜子,风格迥异的泰山书写,折射出不同作家独特的人格气质。笔者在阅读大量的泰山散文后,发现存在三种不同的泰山书写:一种侧重于描绘泰山风景,一种既写泰山风景又写泰山人的人生事象,一种则纯粹写泰山的人生事象。第一种方式作家采用最多,大部分泰山书写皆着眼于泰山雄伟秀丽的风景,属于典型的“风景书写”,而在泰山的风景书写中,写泰山日出最多。第二种泰山书写则是第一种泰山书写的添加与变异,作家在写泰山时,既写泰山风物之美,又注意到泰山风景之外的“人事”,关注到泰山人的生活。第三种方式则较为另类,作家的泰山书写,撇开了本应描绘的“风景”,而直指泰山的“人事”,即泰山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相对于泰山的风景书写来说,这种直接指向“人事”的泰山书写,无疑大大丰富了“风景”的含义,使静态的风景成为动态的,使超脱的风景成为现实的,使外在的风景成为与我们相关的。为了更具体说明泰山书写的不同方式,本文选择三位作家进行分析。这三位作家分别是徐志摩、李广田和吴组缃。探讨这三位作家不同的泰山书写方式,不但可以研究泰山在不同作家笔下的变相,而且可以研究散文文体风景书写与人生叙事之间的关系,研究散文的不同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
徐志摩与泰山
徐志摩生在浙江海宁硖石镇,此地风景秀美,镇的东西有两座山,一为东山,一为西山。明秀山水给了诗人人生最初美的教育,但徐志摩认为:“我们爱寻常上原,不如我们爱高山大水,爱市河庸沼,不如流涧大瀑,爱白日广天,不如朝彩晚霞,爱细雨微风,不如疾雷迅雨。”(徐志摩:《雨后虹》,《徐志摩全集》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160)因此,他虽爱身边自然,但他更爱广大自然界的名山大川。家乡的山与水不在名山大川之列,所以故乡山水虽给他最初美的教育,但却并没有得到他尽情表现。关于故乡山水,他表现于诗的只有一首《东山小曲》,表现于文章的只有给朋友王统照的信《山中来函》。他爱自然,也爱山居,曾说“山居是福”。但他说“山居是福”时,这里的“山”指的是天目山,也属名山之列。(徐志摩:《天目山中笔记》,《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132)徐志摩爱自然,国外的名山不说,国内的名山如庐山、天目山,他都去过。不过,与他关系最深的名山当属泰山。因为诗人不但到泰山游玩过,留下了诗歌《泰山》与散文《泰山日出》,而且,诗人最后的魂归之地就在泰山附近。
散文《泰山日出》为徐志摩游历泰山之后所写。文章写于1923年7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期(1923年9月10日)。文前小序称“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句,结合文章写作时间“1923年7月”,可推断诗人登泰山时间大概为1923年六七月间。
徐志摩写泰山,属于典型的风景书写,主要写泰山日出的一刹那,用的是一贯夸饰的浓墨重彩写法: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徐志摩:《泰山日出》,《徐志摩全集》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312)
徐志摩写泰山,为什么要抓住“日出”来写,又为什么采用大泼墨,把泰山日出渲染得那么壮观、华美呢?这还要归于他自己的自然观、生命观。诗人爱自然的名山大川,且认为我们“爱白日广天,不如朝彩晚霞”,所以,他写泰山,要抓住泰山的日出来写。泰山日出既是自然的奇观,又是生命的奇观,他表面写泰山日出,背后写的其实是生命的狂欢。汪曾祺评价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可谓“浓得化不开”。“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自己?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么写。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写日出。”(汪曾祺:《泰山片石》,《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93)的确,徐志摩写泰山日出,其选题、角度和写法都与他浪漫主义的自然观、生命观有关。但汪曾祺认为徐志摩通过写泰山日出而写自己,则只说对了一半。要了解这一点,还要知道徐志摩写此文的特殊背景。
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为欢迎泰戈尔访华,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1923年9月、10月连续出版了上、下两期“泰戈尔专辑”(《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第10号)。“泰戈尔专辑”的打头栏目为“欢迎泰戈尔来华”,“泰戈尔专辑”(上)该栏目发表了3篇文章,除主编郑振铎《欢迎太戈尔》一文外,其他两篇文章皆为徐志摩所作,一篇为《泰山日出》,一篇为《太戈尔来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看似与欢迎泰戈尔的主题毫无关系的《泰山日出》怎么会出现在“欢迎泰戈尔来华”的专栏内呢?作为编辑的郑振铎和该文作者徐志摩并没有搞错。徐志摩写《泰山日出》,其目的就是为了把该文献给他崇敬的印度诗圣泰戈尔。该文结尾一段说得很明白:“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相望太戈尔来华的颂词。”可见,《泰山日出》是徐志摩献给泰戈尔的一篇颂词。因而,也只有作为颂词来读,才能读出该文的微言大义,读出压在纸面背后的意思。如该文的关键一段:
我躯体无限地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徐志摩把自己想象为远远高过泰山的巨人,面向东方,盼望,迎接,崇拜,祈祷。盼望什么,又祈祷什么呢?当然是盼望和祈祷“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太阳”既指真实的太阳又指泰戈尔。徐志摩把泰戈尔比作太阳,以盼望日出的急切心情盼望泰戈尔来华,给中国带来光明,带来阳光。所以,《泰山日出》包含显与隐两层含义,表面写泰山日出,隐含的则是盼望、期待泰戈尔像一轮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早早照射到中国,给中国带来文化之光。
汪曾祺认为“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汪曾祺:《泰山片石》,《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93)的确如此。徐志摩写泰山,那种夸饰、华丽的浪漫主义写法,非常真切地显示了徐志摩的诗性人格。不过,若要真正理解徐志摩《泰山日出》中的“风景”,单单采用新批评的封闭式阅读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泰山日出》的风景书写来说,这种封闭阅读不但进入不了文本内部,且很容易带来文本误读。只有结合《泰山日出》最初刊发的刊物与栏目,熟悉了该文在原始刊发环境中与前后文之间的互文关系,彻底了解泰戈尔访华的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该文,理解该文风景书写的深层含义。
笔者把徐志摩《泰山日出》作为泰山风景书写的代表,并不代表这篇文章在泰山的风景书写中是最好的。从艺术层面上讲,《泰山日出》的语言存在过多夸饰、做作成分,艺术质量并非上乘,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一文中就对徐志摩此文提出过委婉含蓄的批评。在语言外,徐志摩此文还存在诸多可议之处。还是回到“风景书写”来说。写泰山,写其他名山,以及写大自然的万千气象,必然脱离不开风景书写,包括小说家的小说叙事,同样离不开风景书写。不过,风景书写也要讲究艺术的节制,控制不好,很容易由激情滑入滥情,由真诚演为做作。《泰山日出》就存在这种倾向。另外有一点值得提及,就是徐志摩为了表达自己对诗圣的崇拜敬仰之情,竟然把泰戈尔比作东方升起的一轮红太阳。把人比作太阳,在20世纪文学史上,此文可能是首开其端吧。
李广田与泰山
与徐志摩相比,李广田与泰山的关系要更密切一些。这是因为李广田出生于山东邹平,和泰山本是老乡关系。李广田193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济南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妻子王兰馨在泰山脚下的一所中学教书。为了看望妻子,李广田常到泰安,假期就住在泰山脚下,无事就与妻子一起登泰山。因此,李广田不仅是泰山游客,还是泰山住客,与泰山有更长期、更亲密的接触。检视他1935年、1936年创作的散文,会发现不少散文文后皆标注有“泰山”字样,如《成年》文后署“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泰山二虎庙”,《扇子崖》文后署“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泰山中天门”,《影子》文后有“一九三六年夏,泰安”,《雾》后署“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忆山居作”,这里所谓的“山”指的就是泰山。由于李广田有过泰山山居经历,他1936年暑假山居时期写就的散文《扇子崖》与1936年11月在济南写就的《山之子》,都是以泰山为主题的。另一些散文如《影子》《雾》虽没有直接写泰山,但都与泰山有关。
李广田写泰山的散文以《扇子崖》和《山之子》为代表,这两篇散文代表了泰山书写的另一种方式:风景书写加人事书写。《扇子崖》以风景书写为主,但也掺杂了人事书写;《山之子》则以人事书写为主,同时辅之以风景书写。两篇文章都写泰山,但由于风景书写与人事书写所占比例与搭配方式不同,写法就有较大差异。《扇子崖》纯用记游写法,文章以“八月十二日早八时,由中天门出发,游扇子崖。”开头,以“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是傍晚时分。”结束,所叙为一完整的行程。这样一个完整的行程中,作者虽也详尽叙述一路之所见,但所写重点当然是扇子崖,这样才能与题目照应。《山之子》则以“住在‘中天门’的‘泰山旅馆’”始,以离开旅馆下山终,突出了在泰山的居住和离开,已完全不是记游写法。该文写山居,开始重点写泰山的山路之险,属于典型的风景书写,但描写重点已暗暗发生变化,由写“看山”到写“看人”,写起山中居民与上山的香客来,就如文中所写:“我们则乐得看这些乡下人朴实的面孔,听他们以土音说乡下事情,讲山中故事。”也就是说,由“看山”转到“看人”,由风景书写过渡为人事书写。比起风景描写部分,该文人事书写所占比重很大,且人事书写部分写法多样,显得摇曳多姿。人事书写部分,先写香客,再写山居中认识的两位小朋友,再由“我”与两位小朋友有趣的问答过渡到哑巴以及哑巴父亲和哑巴哥哥的悲壮故事,照应到题目“山之子”。
写泰山,“看山”“观景”为题中应有之义,大部分泰山游记都是这样写的,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徐志摩的《泰山日出》皆如此。但李广田的《扇子崖》与《山之子》则一改这种写法。《扇子崖》为纯粹游记写法,但作者之所写已经与一般游记不同,因为作者在写泰山风景的同时,已经关注到泰山风景背后的“人”之存在,如文章先写泰山山坡上几处白色茅屋的清幽可喜,但笔锋一转,转到茅屋的主人乃是“白种妇女,天之骄子”,继之又写了身份为地道农民的香客对于这些茅屋的窥伺与羡慕,以及一个男子听白人妇女讲解《圣经》的可笑神态;在写了黑龙潭的奇险后,又写了行走在盘道上香客所讲的扇子崖故事,比较了泰山东路与西路乞丐的不同;在描绘过月亮洞的阴森景致后,又突出描写了一位只有一只眼的香客,简直像鬼趣图中角色,瞪眼看人时,让你害怕。总之,《扇子崖》虽纯为游记写法,但作者已突破了一般游记写法的窠臼,既写“山景”,又写“人事”,既抓住了泰山独有的自然美,又突出了泰山的社会属性。写《山之子》时,李广田干脆抛开游记写法,“看山”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主要写泰山的山民,通过哑巴父子三人的悲惨故事,写出泰山人的勇敢、执着与坚韧,凸显出泰山的伟大。可以说,《山之子》虽没有把重点放在写山上,但恰恰把泰山的精髓写出了。
现代散文家中,李广田写乡土写得最好。其乡土散文的优长在于能以客观、素朴的语言,通过白描和叙事,刻画出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他写乡土,不重在风景描绘,而重在人事观察,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是他关注的重点。这是一种既朴素又高妙的写法,近于小说,而远离诗,与其朋友何其芳形成鲜明对照。由于他一贯擅长以客观的态度通过人物命运来表现乡土,所以,他的泰山书写能够突破传统游记之窠臼,由《扇子崖》到《山之子》,通过写人来写山,把人写活的同时,把泰山也写活了。
吴组缃与泰山
吴组缃为安徽泾县人,好像与泰山扯不上关系。但1935年他曾作为冯玉祥秘书和国文教员在泰山住过将近一年时间,比李广田到泰山的时间要早一点,比李广田在泰山居住的时间要长。因此,他虽不是山东人,但与泰山的关系,却非同寻常。正是有在泰山的这段经历,吴组缃才创作出散文《泰山风光》。该文结尾注明写作日期为“一九三五,八,十”,这时他正在泰山。因此,文后虽注明写作时间,没标注写作地点,但地点应该就是泰山。这一点从散文内容也可得到印证。
这篇文章题为《泰山风光》,但所写则不是风景,而是对泰山风景之拆解。这篇散文在背离风景书写上比李广田走得更远。李广田的《扇子崖》与《山之子》在写人事之外,也写风景,作者对风景的态度还是完全肯定的。而吴组缃这篇文章,虽命为《泰山风光》,很容易让人想起文章内容为歌颂泰山风光,属于纯粹“风景书写”。但恰相反,作者完全避开“风光”来写。文章只是采用“我”的视角,通过冷眼旁观,以社会剖析方法,运用人物对话,客观呈现泰山朝山香客、逛山游客、寺庙道士、真假乞丐各个阶层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阴暗、凄惨的、带有喜剧性的,可谓是“风光”的反面。文中也写泰山街道与寺庙,但这样的街道是灰色、杂乱、拥挤的,也不能称之为“风光”。文中有一处倒是写了“风光”:
我静静地听着,一面把眼睛眺望前面。这院落,前面说过,是在几重高阶台的上面,正殿屋脊,都低低俯伏在阶台之下。屋脊上,展开的是半个泰安城,闾阎扑地,万家在望。东南西三面都是一望无涯的漠漠平畴,东一堆西一块地缀着些七零八落的村庄。这时夕阳映照,淡青的原野抹上一层浅黄,各处村落缭绕着淡淡的炊烟。对面徂徕山泛了淡蓝颜色,弄得变成瑞士风景照片的派头。汶河弯弯曲曲,从那一头绕过山后,又从这一头钻了出来。再远处,是漠漠平原;更远处,还是漠漠平原。渐渐入了缥缈虚无之间,似乎仍是平原。忽然前面几块晶莹夺目的橙黄色东西,山也似地矗立着,旁边衬护着几抹紫红颜色,分外鲜艳美丽。定睛细看,才知道那是云霞,已经不复是地面的东西了。
“你们这地方真不坏,”我打断他们的话说,“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复如何,齐鲁青未了’,不想这样壮阔的境界,如今就在你们几席之上。真是几生修来的清福!”
我这样酸溜溜地说着,站起来点上一支烟。
细读这一段风景描写,可发现它的写法与通常散文的风景书写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散文的风景书写表达的是对风景的赞美与肯定,但这段风景书写表达的恰恰是对“风景”的否定、讽刺与拆解,是典型的反讽语调。这样的反讽语调与反讽结构贯穿文章始终。文章中除作者“我”之外,几乎每个人以及泰山大庙内所供奉的泰山祖奶奶碧霞元君都是作者的讽刺对象。
吴组缃属于左翼青年作家的后起之秀,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艺术技巧的娴熟程度和社会剖析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一点不逊色于左翼小说大家茅盾,甚至有超越之处。作为一个优秀的左翼小说家,吴组缃对泰山的观察和呈现,在视角、内容方法与风格上,必然既不同于徐志摩,也不同于李广田。徐志摩对于泰山那种诗性、浪漫、夸饰的呈现方式,无疑是吴组缃所反对,也是他看不上眼的;而李广田对于泰山“山之子”的呈现,固然生动,令人印象深刻,但单单讲述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故事,在吴组缃看来同样远远不够。吴组缃所要做的,是把泰山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对之进行冷静的解剖,把它的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生活,都以文学的方式生动、立体地呈现出来。左翼作家的社会观和艺术观,以及整体呈现“泰山社会”的艺术企图,都决定了吴组缃的泰山书写不可能是传统的“风景书写”,而只能是“反风景书写”。
(作者系黄淮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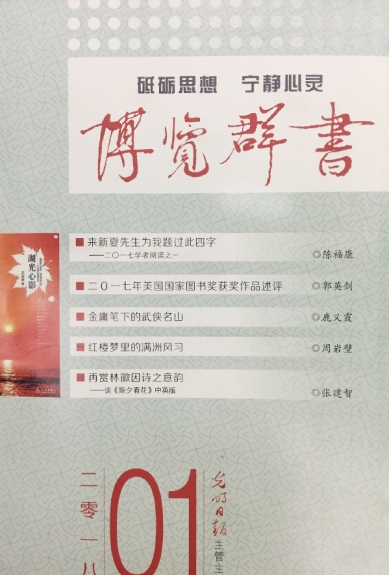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