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山系之一,大别山横亘鄂豫皖三省接合处,重峦覆翠,千沟万壑,其腹地更是山环水绕,层层叠叠,易守难攻。在中国现代史上,大别山是罕有的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都发生过重要战事的著名山区。
/壹/
姚雪垠自认是“平原的孩子”,他出生的邓县姚营位于伏牛山系前怀盆地的西南角。尽管向西隔着一条河便是丘陵和小山,但他不是幼年就在山里爬上爬下的孩子,因而大山对他有种神秘的诱惑,年轻时就“十分爱山”(《姚雪垠文集》第14卷,P63)。似乎是天助人愿,从14岁起,姚雪垠就与大别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年,他来到大别山北麓的信阳,在一所教会学校就读,晴天时,他会痴痴地望着远处的山峦发呆,幻想着山里的神奇故事。不到一个学期,为躲避战火,学校将学生遣散,姚雪垠与二哥及另外两位同学一道回邓县,途中就发生了那件对他创作有深刻影响的土匪绑票事件(参见《长夜·前言》)。
1932年秋,因生活无着,姚雪垠又来到信阳,在信义中学教书。两次信阳之旅,使他对大别山产生了浪漫的文学幻想。1934年,他创作了以大别山著名峰峦鸡公山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山上》。保罗老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上帝乃至洋人抱着无上的膜拜,认为只有洋人才是中国人的救星。然而,他的信念却受到唯一的亲人——孙子马可的怀疑与鄙弃。随着孙子的成长,这种冲突日趋强烈,马可终于弃他也弃上帝而去,下山到了花花世界的武汉,在做工与失业的交替中走上了青年一代抗争的人生道路。保罗老爹的痛心疾首阻止不了孙子按照自己意愿前行的脚步,而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军阀大兵对鸡公山的侵占与破坏。世道变了,人心不古,保罗老爹的信仰一次次受到嘲弄,最终,他在失落中将自己一生的积蓄献给教会,下山回乡养老。小说在隔代的父与子冲突中,否定了崇洋媚外的“父”辈的价值选择,肯定了“子”辈勇敢前行的人生姿态。
抗战爆发后,姚雪垠积极参加了第五战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夏,作为五战区“笔部队”的主要成员,姚雪垠与臧克家从襄樊出发,徒步跋涉千余里,经周口、阜阳辗转来到大别山腹地的立煌(即金寨,国民党政府为表彰卫立煌部攻占这座鄂豫皖边区首府而改名)。
此时,立煌已成为安徽省的战时省会,安徽各界人士会集于此,中共影响下的抗日民众团体在此也比较活跃。姚雪垠与臧克家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徒步出山,经大别山南侧折回襄樊。这次经历,使姚雪垠对从少年时就向往的大别山有了更全面直观的体验。
当年秋季,姚雪垠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将沿途看到的风光写进了这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故事从山里的佃户女儿黄梅写起,随后转到大别山北麓的一个小县城,通过抗日青年的活动展示了大别山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出读者对祖国壮美山河的热爱。
实际上,这部小说构思于平原地区的老河口,在抗战活动之余,姚雪垠与胡绳等几位文人空闲时经常谈论周边的几位年轻女孩。姚雪垠更是深入分析这些女孩的性格、心理,将自己的揣摩心得分享给大家。女人谈论男人,男人谈论女人,本是人生常态,但对作家就不同了。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很精彩,鼓励他写成小说。不久,胡绳前往重庆,出任《读书月报》主编,写信督促姚雪垠把构思形诸笔端。
姚雪垠却临水思山,在小说中把人物活动的区域置于大别山区,并将进步青年的救亡活动与多年前那场惨烈的红色暴动联系起来,有效扩展了人物活动的景深,为进步青年的救亡运动接续上红色血统。不过,在创作中,作者不自觉地把描绘的重点放在青年男女的情感萌动上,其中,描绘太阳、月亮与星星隐喻的三位女性(分别象征黄梅、罗兰与林梦涵)的个性与情态占据了很大篇幅,这是后来这部小说饱受非议的主要原因。男性作者这种日复一日揣摩女性的“花心”,成就了这部小说人物心理和感觉描写的细腻与生动,但也过分突出了罗兰、林梦涵等女孩的小女儿情态,小说前半部给人以甜蜜蜜的感觉。
不过,路翎、阿垄将这部小说斥责为“黄色小说”显然过甚其辞。当然,在整个民族陷入空前危机的年代,《春暖花开的时候》过多地沉浸于儿女私情中,确实也冲淡了小说原本要表现的抗战主题。对此,连为姚雪垠辩护的茅盾也认为,“作者让这一群小鸟(进步青年——作者注)在抗战工作之暇谈谈私情,闹点小别扭”,幸亏小说第二、第三册“在小鸟的啾啁之中有了金戈铁马之声”,才“不使成为抗战红楼梦”(参见《姚雪垠研究资料》,P452—P453)。客观地说,姚雪垠本来要写上百万字的三部,但因为种种原因,小说只写了第一部三册,原先设定的人物性格的成长与思想的分化并没有真正呈现出来,因而给人过分注重儿女情长的感觉。有趣的是,正是因为这种感觉,小说当时在大后方,后来在香港、新加坡都赢得了大量读者的青睐(许建辉:《姚雪垠传》,P105)。这,或许体现了彼时彼地的进步文艺界与不太关注战争痛痒的普通读者对小说好恶的显著区别。
/贰/
1941年春,在皖南事变之后的反共高潮中,国民党最高层直接插手第五战区总部的清共问题,作为著名左翼作家的姚雪垠在老河口难以存身,被借故解职回家。不久,他便接到桂系开明人士韦永成(时任第五战区秘书长兼安徽省文化厅长)的邀请,于这年4月(参见吴永平:《姚雪垠在大别山的文化抗战活动》)又一次来到立煌,挂名安徽省参议员,替韦永成编辑《中原副刊》(后改名《中原文化》)杂志,开始了近一年半的山居生涯。
由于桂系对国共合作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实力已渗透进金寨,政治气候比较严峻,但一些进步的文化人仍在这里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并且同桂系主导的政府文化官员有较多的交流互动:
人们因临时需要,在那座原叫金家寨而如今改名立煌县的荒山中用稻草盖起来各式房屋,开辟马路,成立了新的街市。
…………
陆续地出现了许多座西式草房,大都住的是文化朋友。
…………
在山路口树了个木牌子,上题三个字:“文化村”
…………
山中朋友寂寞,爱开玩笑,爱向人送绰号,于是就把“文化村”改为“文明村”,很快地就叫开了。(《伴侣》)
姚雪垠住在这个“文明村”附近,山里生活也给他不少困扰,夏季被蚊子叮咬,冬季被老鼠骚扰,而闷热潮湿的天气也让他难以消受。但无论怎样炎热,“一到黄昏便凉爽起来,夜间简直凉爽得像平原的秋季,而早晨的气候同黄昏时一样可爱”(《出山》)。
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里,姚雪垠创作了以抗战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戎马恋》。主人公金千里作为一位受到战区高层呵护的军人,身为总部秘书却没有具体事务,有充足的时间与自由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女护士。而教会医院的女孩张惠凤怀抱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替主做着救死扶伤的繁忙工作,她是院长——一位虔诚的外国老女人的宠儿,是这所医院所有护士的楷模。面对金千里咄咄逼人的爱情攻势,她脸红耳热、紧张尴尬、退避三舍,然而终于还是经不住他感情真挚的软缠硬磨、死皮烂打,逐渐由半推半就发展至偷偷订婚。他真诚地想把她从教会医院中拯救出来,使其走出宗教的迷雾,走入抗战工作中去。他成功了!他的说教、他的情热逐渐瓦解了她的宗教信仰。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她对抗战工作又生发出更加赤诚的宗教般的热情,而且很快超越了他感情与思想的双重掌控,在学习班同学的影响下,她越来越向往前线向往大西北那片热土。
金千里作为娇生惯养的官宦子弟,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罗亭一样,虽然以其夸夸其谈与男性情热唤起了纯洁女孩的理想与爱情,但觉醒了的张慧凤像娜塔莉亚一样以勇敢与果决超越了自己的引路人,使其露出了金玉外表下脆弱的败絮。面对张慧凤赤诚的理想与日渐强烈的献身热诚,金千里对后方安定奢华生活的贪恋与痴迷,以及个性中的虚荣与怯弱都暴露无疑。旧的冲突消失了,新的更大的冲突又生出来。一个执意地要奔赴前方,一个却要同回战时首都;一个要去根据地救死扶伤直至赴汤蹈火,一个却要在安逸的大后方构筑爱情雀巢共享荣华富贵。最终,女主人公凭着自己的爱情与执着,终于软化了她的导师兼未婚夫。尽管极不情愿,但在美好爱情与时代理想的感召下,金千里终于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张慧凤要他北上前方的要求。
小说虽然与2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革命浪漫蒂克小说“革命加爱情”的情节比较接近,但《戎马恋》对人物心理轨迹的刻画,对两次矛盾冲突的处理,都显得比较可信,小说语言也亲和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大别山创作的另一部小说是《母爱》(最初刊载时叫《孩子的故事》,后经改写),小说通过对夏光明一家悲惨遭遇的描绘,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普通家庭造成的深重灾难,揭露了日寇在大别山野蛮杀戮的残暴行径。《母爱》突出了夏太太在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中对孩子们的呵护,以及在濒死关头用身躯保护孩子的舍身之举,同时也描述了吴奶奶、陈剑心等对夏光明发自内心的爱与照顾,为中国军民在悲愤中的相互扶助、艰难生存与不屈意志描画了一幅细致入微的图景,这种苦难中的温情给人以乐观、向上的动力。
/叁/
对姚雪垠来说,幽居大别山腹地最大的收获当是捕捉到了《伴侣》的小说素材。立煌这座战时省会,在发挥区域抗战政府首脑功能的同时,也藏污纳垢,生发出各种各样怪诞的新奇事,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伴侣》构思于大别山,但写在作者离开大别山一年多之后。作为姚雪垠为数不多的讽刺小说,它的幽默滑稽与生动流畅在现代文坛罕有其匹。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我”的朋友郑天修夫妇紧张而有趣的夫妻关系。
这是一对活宝儿。男主人公郑天修擅长吹牛拍马,“什么毫无踪影的事在他的嘴里都说得有凭有据。他不仅替他自己吹,也替朋友吹”,而且吹得无边无际,吹得天花乱坠,吹得生动有趣。郑天修的另一特点是通过交际与经营而捞钱,通常情况下,他家的生活要比山坳里其他的人家高一大截,通常他大致能让他那位妖娆的夫人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自然,他的发财总是出人意料,比如在不知不觉间,他突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而与此同时,在临近的一个山坳里,他的一栋更大气更上档次的西式洋房生长出来,像变戏法似的。天修还有一个他人不及之处:作为一位文化人,一位曾经的剧作家,他能完全置抗日宣传、戏剧创作于不顾;作为一位国民党官员,他能根本不在乎上面不准经商的规定,而一心一意地从事自己捞钱的事业,脸皮之厚实胆量之雄壮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人物是抗战文学中继华威先生之后又一个相当成功的官僚形象,他的捞钱能力与华威先生的捞权手段堪相匹敌,小说借此鞭挞了国民党文化官员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的社会现实。
人道是:不是夫妻不进一家门。有一雄性俗物必有另一雌性俗物与之相伴,不然便难以达至阴阳之平衡。这个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的女主人公(作者可真够委屈她的)给读者带来的愉悦比她那位奇伟的老公更丰富。她极善于利用一个女人的优势驯服她手中的这个男人,如同驯服一只哈巴狗。她最常用的一招就是直接“打脸”!在郑天修正吹得语酣耳热之际,她会大声地直接地说出大家的心里话:“郑天修,你吹牛,看你快把房子吹塌了!”“故意当着人面给他难看”,每当此时,大家便一下子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他的势头便被她一把夺了过来,他便乖乖地停下来。她的第二神招便是“绝交”,即不让老公动他一手指头,视情况给以或长或短的惩罚,严重了则是长时间的“绝交”。这招数显然很有效,尤其是对郑天修这个“一天都离不开女人”的男人,所以他往往败下阵来。这女人的第三招是声称“离婚”,而且是“非离婚不可!”这最后一招不到万不得已不怎么使用,即便用起来,也主要是对朋友、邻居们诉说,以便营造悲剧氛围,博取周围的同情与照顾。当然,当郑天修搞来钱的时候,她也会适度地奖赏老公,比如“复交”,比如甜甜地把天修叫作“甜休”。
这个女人不仅会驯化老公,也很现代。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她居然把自己的眉毛全部剃掉,然后每天在原来的眉毛处细心描画,“起床后单收拾脸孔这一件事就需花上个把钟头”。她不怎么照顾孩子,甚至会因为嫌麻烦,故意造成早产。她奢华的生活欲求不因为抗战而稍减,她毫不顾忌的谈吐不因为是女性而分毫羞怯。总之,这是一个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鲜活生动的奢华女性的形象。
/肆/
一个人在生命中成就一番事业,必定要有“感动自己的时候”,对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感动自己是感动他人的前提。姚雪垠年轻时期不乏这种时候。他幼年时家庭几经变故,完全败落。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破落户”子弟一样,姚雪垠饱尝人生冷暖,充满了辛酸与艰难。在开封、北京期间,他经常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有时靠朋友同学的接济才渡过难关,但他一路前行,努力克服困难,不断超越自我。尤其是后来染上了那个时代的绝症——肺结核,有时每周数次咯血,但他仍然拼命读书、写作,置疾病、生死于度外。他初期的多篇小说真可谓是“呕心沥血”的产物。
蛰居大别山是姚雪垠人生中又一次“感动自己的时候”,这是一次几近封闭自我的生命体验,近乎一次人生的修炼。“夏天,黄昏后山中不仅凉爽,而且是那么静谧,使我感觉得方佛是处身神秘境界。”当前来求教的孩子们走后,“我往往仍旧寂寞的坐在院里,任露水暗暗的打湿衣裳,直坐到夜深人静”。这种夜间的孤独,“就像是一个失踪的旅人只身漂泊在荒凉的万里草原之上”(《出山》)。
在这寂寞难耐又时时面临政治危险的状态下,姚雪垠在编刊物之余,还奋力构思与写作,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亮色。有意思的是,他后来说自己的肺结核无药自愈,“在抗战中不知不觉地好了”。考虑到在老河口时他还偶尔咯血,甚至有长时间卧床不起的经历,这简直近乎奇迹。他在《出山》中已没有提及疾病,这一年半是他青年时期少有的没被疾病困扰的时期,也就是说,他的肺结核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地好了”。这里,无疑是他的福地。显然,大别山蛰居是他人生的一次幸运之旅。
1942年9月,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阴影日渐扩散,大别山的政治氛围愈加冷峻,姚雪垠及时离开了已成是非之地的立煌。他动身不久,多位进步青年就惨遭迫害。他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青年时期最长的一次山居就此结束了,这段生活为姚雪垠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别样的人生体验。长篇小说《李自成》对商洛山区的描绘就明显带有这段山居体验的影子。但这是后话。
(作者简介:刘骥鹏,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4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创作研究”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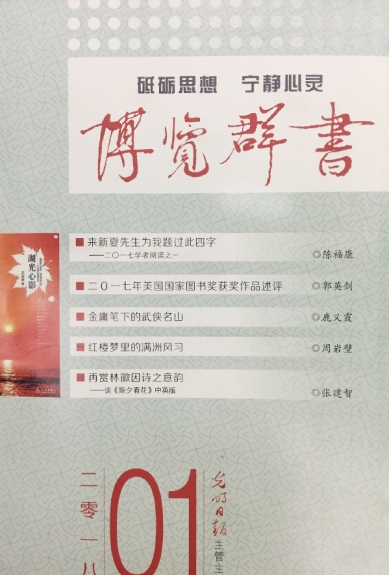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