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作为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的后辈同行,如今也服务于社科院历史所的笔者, 读了王先生的杂文, 首先被吸引的是在“文”有其“纹”之外, 行文中所独具的“史”家特色。先试举一例, 以便下文述评。
《请饮一杯屠苏酒》是王春瑜先生早年撰写的杂文,全文共五段文字,第一段引王安石的名诗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开篇之后,便信手拾例,谈到东汉崔寔(103-170)在《四民月令》中就有对元旦(即现在的农历春节)日饮屠苏酒的记载,此后,是见于宋代庄绰(12世纪)《鸡肋编》中饮用屠苏酒的顺序和由之而来的负面评价: “自小饮至大,老人最后,所余惟多, 则亦有贪婪之意。”对此说, 引者这里并不径作定评, 而是用《时镜新书》中“少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之说来驳斥, 并示以己意。如是, 王春瑜先生以古人的说话回应古人,其间因明自现,毋庸再赘笔置评。故而,作者仅以赞誉式的结论来表明主张:“这是多么合理, 并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呵!”此后, 荡开笔墨, 以刘梦得、 白乐天元日举酒所和 “与君同甲子, 寿酒让先杯”及“与君同甲子, 岁酒合先谁”印证此说。再后, 以白乐天“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补缀行文,令这段借古代名士之手来描述屠苏酒的文字, 雅趣兼偕,读来极有兴味。
但屠苏酒是什么,并不一定为普通读者所能详细了解, 或者听者知其名而不得其实;况且作者是以“请饮一杯屠苏酒”命题,若读者都不知这酒为何物,何谈被劝饮!于是,在接下来的两段中, 王春瑜先生征引明代的著名药典《本草纲目》以及明代著名博物学者郎瑛的 《七修类稿》,指出这用于酒名的“屠苏”一词,既有名医孙思邈庵名之说, 也有另为古代庵名的看法,且指明两说并存,其疑难定。接着,用《七修类稿·辩证类上》和《本草纲目》来介绍屠苏酒的配方, 并号召酒厂不妨试着恢复这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制酒工艺,在尊长敬老的文化氛围之中, 再饮屠苏酒。
这是一篇最初刊登在1992年2月4日《光明日报》 第2版上的短文。 篇幅虽短,却解决了好几个有关屠苏酒历史的重要问题, 读后不仅能了解此酒之由来和在历史上就其饮用顺序而生的争论, 更能体会中国历史上尊上亲下的传统已经融入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而非互为皮相的浮泛之辞。况且,作者在文末感慨道,若是能恢复屠苏酒的生产,在一年一度万象更新的春节, “我们能够像先辈们那样, 团团而坐, 由少及老,道声:请饮一杯屠苏酒。
不亦快哉!”老一辈史学家行文中的意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甚至对屠苏酒的喜爱,都其意难掩。
但这篇短文引起笔者更大兴趣的是作者据以持论的文献。《鸡肋编》先后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这两部大部头的丛书中,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整理点校本,令此书便览易查。但《时镜新书》却是如今不存的。 我们可以从宋代洪迈《容斋随笔》、陈元靓《岁时广记》以及明代另一位博学学者王世贞 (1526- 1590)《弇州四部稿》及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等子部古籍中, 间接读到《时镜新书》中被王春瑜先生引用的那段文字。 姑且先不论这篇短文中引用史料的稀见性, 单从文献的运用方法看, 王春瑜征引的这几则有关屠苏酒的文字, 是沿着诸家争论此酒饮用顺序之合理性的产生时序, 由源头而下, 择其要者, 而非舍源从流, 甚或从子书先后征引所形成的脉络中随意截取——后者看似信手拈来, 其实难称有史才眼光和在全面掌握史料后方才发言论事的史学自觉。 这是从王春瑜史学杂文所用史料的选择角度说。
下面再以《烧书考》(《书墨》,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为例, 看看作者引用史料的范围。这篇文章仍然不是长篇大论的高头讲章, 也非历数中国历史上禁毁书籍的考订之作,但内容却不显单薄, 且没有令人望题生义的错觉——以为还是批评秦始皇、 乾隆帝等帝王焚烧和禁毁古籍的事——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子、 史二部中选择的例子, 告诉了读者一些儒学士大夫鼓吹和经历的焚书、禁书事件。例如认为当时天下之书已多, 主张禁绝杨、墨等子书以及佛书的元代吴海(1307-1375),还有焚烧自己著作如南宋顾禧者, 以及因得罪当道而书籍被焚如永乐朝朱季友者等。 作者罗列这些例子, 并未在类型上作严格区分, 而是径按时序,析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烧书事情。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复杂,原因也多样而不能一以概之, 甚至都可以作为有价值的个案来逐个研究,但那是史学工作者面对同行的专业处理,当面向学界内外兼有的读者群时, 惟有以例取胜,才有助于传递概括的印象,也便于观览。这就要求有相当的取例范围。 就该文而言,从时间轴上的近处往远处说,《明清内阁大库史料》 是现代史学名家整理的一手档案汇编,此外,该文的取材涵盖了南宋王明清、顾禧、孙奕,元代的吴海和明代的陈建、莫是龙、顾炎武、王士禛、严有禧等著名士大夫。从读者角度说, 有趣的是,我们从这些学者著作被影印出版的情况,可以大概了解到王春瑜先生读史的范围和撰文时阅读的轨迹。宋代的王明清《挥麈后录》是收录在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宋代史料笔记丛刊》里;吴海的《闻过斋集》被《四库全书》和《嘉业堂丛书》收录,在1987年《文渊阁四库全书》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嘉业堂丛书》被文物出版社影印后, 可方便观览;孙奕《履斋示儿编》、陈建《学蔀通辨》、莫是龙《笔麈》、王士禛《陇蜀馀闻》和严有禧《漱华随笔》 都收录在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值得留意的是,王春瑜先生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 1980年《书林》第2期上, 当时文中所引古籍并未像如今被影印之后那样方便取阅, 可以想见, 作者当日研读时翻阅子、 集二部的辛劳, 绝无今日古籍电子化之后读用的方便与检索的便捷。
·贰·
王春瑜先生专研的领域是明代历史。他在20世纪60年代负笈上海复旦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陈守实先生 (1 894-1 974)攻读明清史研究生。在“文革”中,研究被迫中辍,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重新开始史学研究。 但那段随名师从学的史学训练,对王春瑜先生而言, 无疑是重要的学术积淀,进而有助于形成笔者在上文信手二例中所示他对传统文献采择的思考。
对王春瑜先生读书的眼光和用功的程度,我们从他在1977年的一则日记中,能捕捉到一些讯息。6月29日, “星期四,大热。 至上图翻检《明清史料》甲、 乙、丙编, 有所获。”(《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重印〈明清史料〉序》,载《书墨》,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明清史料》是指原存于清朝内阁大库中的明清两朝档册,1911年清朝灭亡后,被罗振玉等人从商家手中高价收购, 之后在1928年入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该所随即成立了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等当世著名史学家组成的 “明清史料编刊会”,主持明清史料的编辑和出版。这批残余档案, 先后被分为甲、乙、丙三编出版, 内容涉及明末清初辽东战事、 明末农民运动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等重要史事,是研习明末至清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 由是可知, 王春瑜先生自重返学术界伊始, 着手研读并摘抄整理的就是当时可见的学术价值非常高的一手档案, 而非从二手文献中辗转贩抄, 这当是成就他之后史学建树的基础。
从这年开始,至2000年,王春瑜先生后来回忆说已经积累了近百万字的读史札记。这些读书的成果,后来很大部分是以杂文的面貌展现给读者的。 (《老牛堂札记》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就文体而言, 杂文与明代盛行的与“高文大册”相区隔的小品文有些关联, 但也不能说杂文便是源自小品文;就形式来说,史学杂文与“模样”严整的史学论文在论证模式和铺陈思路上,也迥然有异。但史学家笔下的杂文,从王春瑜先生的作品来看,还可能告诉读者文字之外的更多含义。
在《书墨》的自序中,作者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时, 鲁迅、阿英、郑振铎、唐弢的书话, 深深启迪了我。”提到的这几位, 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杂文家。现代杂文,一般被认为是以1916年开设在《新青年》杂志上的“读者论坛”专栏为开端, 但杂文成为一种抒发感情兼发表评论的重要文体,还是要到1935年底,标志性的事件是鲁迅将1934年、 1935年发表的杂文结集成《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并将之后要发表的杂文集定名为《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之后, 现代杂文便逐渐成为了一种撰写和阅读都似轻而实重的载体, 成了文史甚至理工各路专家或杂家所钟爱的表达方式。在此, 笔者无意也无力评论史学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形象和在读者群中产生的作用, 惟想就史学杂文所处理的历史问题的选题,以王春瑜先生作品中颇带有个人特色的社会关怀和史学情怀为本, 尝试着略陈一孔之见。
·叁·
对于杂文与时代的关系, 著名作家马识途在《时代还需要杂文》 中提出过一个值得思考的观察。他说:“凡是杂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是国步维艰的时候,凡是杂文兴盛的时候,也是国运走向兴隆,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 这当然是马先生基于他丰富的社会阅历、 人生经验以及创作成就所得出的概观之言, 不是必然而然的因果定见。 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批评的杂文不杂之现状, 已是文史学界的常识;对杂文不是言不及义的侃文, 也不是无病呻吟的闲文的定性,也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然而对杂文要有深刻的思想性、 艺术魅力和历史思辨性以及艺术感染力的定位, 就不是所有杂文家所能准确把握和轻易呈现的了。 马先生这段呼唤盛世杂文的文字, 最早见于他为1994年出版的“当代名家杂文系列”撰写的序言中。该“系列”中收录的,都是一代名家之作,如马识途《盛世微言》、黄裳《春夜随笔》、何满子《无杂侃》、邵燕祥《杂文作坊》等。在这几位著名的老辈作家中, 惟有当年尚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王春瑜先生是历史学家, 他被收录这一系列的《牛屋杂俎》,是作者的第一部杂文集。
然而在此之前, 王春瑜在明史学界已出版了若干种重要的成果。 如今反观他当时着力的史学研究及史料整理的选题,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他对明代宦官的讨论以及从经济史角度围绕该主题所进行的文献整理工作。相关的系列成果是 《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 以及两年后出版的《明清史散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到如今,这一领域虽然已经有了中英文专著数种, 各国研究者的单篇论文更见其多, 但从经济史角度关注明代宦官问题,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而言,王春瑜应该是力着先鞭的。
但对于王春瑜的杂文写作和史学研究,读者也许能从下面这句话中, 体会出作者在寻求两者间的平衡上所做的努力, 以及他对史学杂文抒情达意作用的理解。 他坦言, 笔下的杂文“对史料的搜集、诠释,远非尽善尽美”,但“重要的是,我写出了我心中的话”。 (《今古何妨一线牵》)很明显, 作者是想借用杂文形式灵活并能轻松驾驭的特点,来表达他对社会的关怀, 而所反映的问题, 恰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实,或许在如今的社会中,仍有其影子,因此有提出再谈的必要。也许, 过于“热心”的读者即使寻章摘句,也不容易从作者的著作中找到谩骂的畅快和猎奇的巷谈,但真正“细心”的读者, 却能从中体会作者对历史上中国的情怀和对现实中国的关怀。
在《牛屋杂俎》的后记中, 王春瑜先生在谈到自1977年以来杂文写作的经历时说:“杂文作者的作品, 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这句话看似平常得几乎与“作家的作品来自生活” 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说话口吻一致, 但与上述马识途先生对杂文社会性的表述, 却能凿枘相合。读者若能从史家与其生活之时代的关系角度略做些引申性思考,则会有更多的收获。
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读到王汎森先生在其新书《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出版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的说话。他提到自己的部分研究主题, 其实带有着自传性。这便是说经历过的时代在他作为历史学者进行学术思考时, 竟然起着先暗后明的矩范作用。他自陈的经历有具体所指:年少时, 台湾正围绕传统与反传统进行激烈争辩, 于是着手研究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1987年台湾“解严”之前,宣讲“主义”是件热闹事儿,便开始研究近代史上的主义与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而对后者的关注,一直延续到2011年王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一场演讲。
王春瑜先生的类似表述则更显其阅历与性格。他说, 自他的杂文出版后,有海外的读者来信问, 为什么要写《“万岁”考》之类的文章。先生直率,说有这样的提问, 便是隔膜。不过他还说, 如果看一下《今古何妨一线牵》也就有了答案。在这篇被屡屡收入作者的杂文集作为后记的文章中, 王春瑜回忆了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见闻, 说正是因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对当时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 才写出了《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而且, 他的这些文章绝不是信口之言和不实之词,相反我们从《“万岁”考》是首发在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上, 就能看出作者的用心和当时的学术环境。
从读者角度说,王汎森先生认为一般人读史, 应该从中获得价值和勇气上的收获。其中,收获价值无疑是有助于作方向性的判断,便于弄清何者应该持定;勇气则关乎行动, 是既落实于行为上的表现与结果,也建基于个人的心性修持。要想令这二者在读了史学著作后有所精进, 所读之书要接近普罗大众, 易懂、好读必然是首要的要求。他通过《南方人物周刊》表示了对普通读者而言, 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史学著作不具可读性、 无法承担史鉴作用的担忧。而这显然不是解决了史学研究当前碎片化纷呈而缺乏后续提升的问题,就能改善得了的。 如果史学家对所研究和论述的问题, 既无同情,又少了解, 徒作寻章摘句的功夫, 即使先抛开读者是否爱读的衡量标准,单就掌握的论据是否全面、准确,以及所用的例子是否有代表性而言,就可能会出现本文开篇借王春瑜先生之例为对比所批评的那种舍源取流的研究路数。
其实,两位史家谈到的,归根到底是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与其现代表现问题。具体而言,是这一古典的学术传统在当代历史学学科的体系规范之内,该如何展现与具体化,并施惠于专业领域外的、数量更多的当代有心读者的问题。当下的史学研究在数量上不可谓不盛,但即使是历史学的专业人士,当面对着每年以上万部的速度出版的,有的还相当艰涩难懂的琳琅满 目的历史学著作时,也很难轻易地将之与史学经世这条在传统中国被视为史学编纂原则的要求联系起来。于是,王汎森先生在强调“人”在历史发生过程中作用的同时,还表示了对史学与现实缺少联系的担忧:“20世纪的史学非常专业化,到最后常常是一般人没法读,或是与现实不发生任何联系。我觉得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来好好思考、论证和梳理这个问题。”
但当我顺着这一思路再读王春瑜先生的杂文时,突然觉得史学家的杂文或可成为在当前社会中, 肩负起史学经世责任的一种文体表现。 史家有本领域内的术业专攻,言辞故而可信,进而可为据, 如果研究的课题再能恰好带着那么点儿对现世的关怀, 则可能方便读者入一山而得两重境,既懂了历史,又能据以关照我们生活的时代,作出合理的判断, 并鼓励自己坚持立场。若果真如是,则何乐而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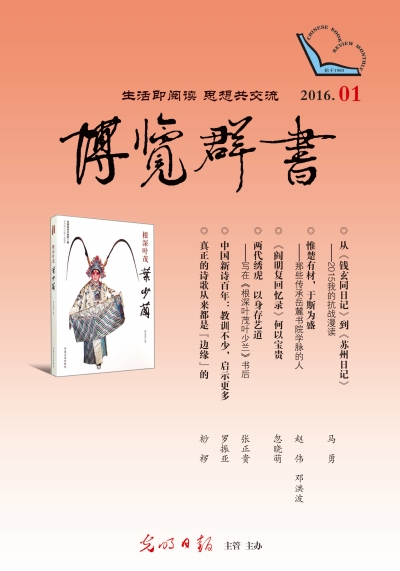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