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喜欢读书的人, 多半不习惯正襟危坐、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样子,而是平日里率性随意地广泛涉猎, 一遇好书则手不释卷、废寝忘食。让人喜闻乐见的书,也绝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头讲章,或是面目可憎的心灵鸡汤, 而是活泼泼的有趣有益之书。所谓活泼泼的,就不能板起面孔说教,也不能口无遮拦大放厥词;有趣,强调的是可读性,而不是斧凿痕迹历历可见的匠人之作;有益,则是可以引发读者思考、带来思维启迪, 至少能够让读者产生与之对话的欲望。
近来读到聂友军主编的《取醇集:日本五山文学研究》, 一部由青年教师与研究生读书会成果汇编而成的论文集,颇称得上是活泼泼的有趣有益之书。一般而言,针对特定研究对象的单人独著与多人合作的论文集各有擅场。专著一般更为系统、严整,但也往往难脱自我重复或单调沉闷的不足;论文集可以在不同层面上精彩纷呈, 但体系难臻完备。《取醇集》既有宏观鸟瞰式的整体总论, 也有单篇深入精微的文本分析解读,所收文章大都有趣味、有见地, 能引人入胜。比如单以论题所及,就包括五山文学中的杜甫骑驴,梅妻鹤子,杨贵妃,牡丹花;有关西湖的诗文、西湖图、西湖意象;禅僧的思归、 交游与归国路线考;东亚视域内的国交文书 ; 禅僧身份与儒学教养的一体两面、相反相成,等等。
在内容方面,《取醇集》以“舍疵取醇” 作为立论的基础与开展论述的进阶路径,通过细密地研读日本五山文学,一方面梳理日本汉诗文与禅宗的关系, 分析文学的承传、赓续及社会功用;另一方面整合内在与外在视角,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世时期的日本;最终将落脚点落实到探究古代中国文化到对日本文化建设所起的推动与反拨作用。
编者与著者都着意用力, 究明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的范围、 力度与方向。 这一层面的考虑,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作为一种明确的意识被提出并贯彻执行。 不要说普通民众, 即便学者中视古代中国为日本文化债权国者亦大有人在, 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少读到能够放下身段去细密分析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什么, 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学, 学习过程中又是如何取舍、改造的, 这一切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如何,以及博弈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取醇集》的多篇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促成《取醇集》成书的“读书会”值得大张旗鼓地倡扬。聂友军在“前言”中提及他们的读书会“侧重学术方法入门”, “逻辑思维训练”与“表达能力锻炼”三个方面的学术训练。 不必说中国高等教育盲目扩招后有些导师认不全自己所带的博士生、 硕士生, 也不必说高校科研量化目标管理体制下许多学者忙于发论文、 做项目而无暇他顾,单说确立以上三个方面作为学术训练的主攻方向, 已然为当下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树立了模范的标杆, 再辅以“读书会”的形式,搭建起师生定期、常态化学术交流的平台,确保了学术训练的可操作性。
愚见所及,《取醇集》著者与编者的用心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从研究对象出发明确的学科意识。从《取醇集》所收的多篇论文可以看出,“五山文学读书会”较为注重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训练, 求真、求实、注重材料的原典性的意识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五山文学毕竟隶属于文学学科,所以文学研究的方法亦得到着力彰显,那就是在求真的前提下,不仅明了“其然”,而且勉力探求“其所以然”。以聂友军的《道出文字言说,舍疵取醇》一文为例,较为清晰地体现出“是什么”(what)——“怎么样”(how)——“为什么”(why)的三个层面。 尽管在原因探析方面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但毕竟在方法论层面上超迈前贤,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并且三个层面没有削足适履地纳入三段论式结构,而是命笔从容,应付裕如, 表现出作者丰厚的学养与相当卓越的识见。
受欧美学界影响, 中国当下的文学研究者中言必称种族、性别、阶级分析的大有人在。这些原本属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在文学研究中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且过于政治化、哲学化和理念化的表达损害了文学研究应有的艺术价值。 但是,乐此不疲的作者与叫苦不迭的读者诸君是否曾经深思过,当我们在谈论文学时,我们事实上在谈论什么? 不应亟亟于做西方层出不穷但往往短命的术语、方法的搬运工,因为但凡移植就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不宜用貌似复杂高深的理论将文学文本搞得越发晦涩艰深,正如有理不在声高,学问也不是如绕口令一般,以唬人为能事;也不必将以“描述性”见长的文学文本生拉硬扯成“规定性”的特定解读, 因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悉心经营、定于一尊也难免导致千疮百孔、破绽百出的宿命。究其根本,文学研究立足于应挖掘并彰显研究对象的文学性与思想性。
二是治学层面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思想。 治学方面, 拒绝跟风, 强调脚踏实地;并有意识地汇通中外文化思想。聂友军在“前言”中提到:“做学问最忌跟风、赶时髦, 人人趋之若鹜的显学极易变为俗学。”在“编后记”中说:“近代以来在人文学领域能成一家之言的方家大多既具备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又对特定的外来思想文化有学理上的把握。”并称《取醇集》是 “着意加强上述两方面修养的一个尝试”。
事实上做学问也罢, 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也好, 在个人层面, 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的, 最终都落实到做人方面。 聂友军提及他坚信引领在读研究生 “逐步找到探索学问的门径, 比想方设法帮他们发一篇文章来得要紧”。在“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语)思想充斥大学校园的当下, 能够坚持这份初心实属不易。聂友军还提到自己读书时得到师长的奖掖提携,感佩老一辈学者“少一些锦上添花、多一点雪中送炭”的情怀,遂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呵护“读书种子”的意愿。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却实实在在地透露出言说者内敛的学术抱负。
三是文化比较体现出诚挚的家国情怀。《取醇集》 的多位著者倡扬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以及文化的交流、回还与往复。 他们用一种历史研究极为珍视的客观态度和笔法,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并比较具体周到地叙述中国文化如何为日本五山禅僧所识、所用。他们从观念上超越了“影响——接受”与“冲击——反应”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 突出五山禅僧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过滤、吸纳、重组与改造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文化观与论述方式对于读者准确而真切地把握有关信息,告别人云亦云,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念大有裨益。
当年萧统在为《陶渊明集》作序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落实到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方面, 无论针对历史研究还是外国问题研究, 该论断仍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对历史资料的梳理与解读过程中丝毫不考虑其当下意义, 不从中借鉴并获得教益, 这种梳理与解读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如此说并不意味着将一切历史都视作当代史, 或者牵强地硬性从历史资料中生发出对当代的启示。
同理, 对外国资料的占有与分析, 如果没有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清醒的主体意识作为观照, 那么基本可以断言相关研究难以做出一流的成就。 比如用英国学界通行的理念与方法研究莎士比亚, 或者与日本学者取相同的路径研究本居宣长,单就语言层面而论, 我们中国学者就很难超越一般的英国学者抑或日本学者。 这时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知识背景成为不可多得的优势, 我们必然会从中国人的关切入手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 与研究对象拉开适当的距离, 有助于客观审视, 并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细密的解读, 俾可发现对象国学者司空见惯而不知设问、 存疑的地方, 深入探究下去,造就对象国学者做不出的成果也就成为可能。 从自身的知识背景与问题意识出发, 充分发挥主体性, 这正是比较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 也是比较得以顺畅开展的有效路径。
在一个西方话语占据中国人文学界制高点的当前, 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都应该致力于营造独立而自由的学术格局与气象。 正如论文集标题《取醇集》所蕴含的“舍疵取醇”所示, “取醇”首先是一种姿态,既避免自视甚高、无视他者的虚无主义,也避免自我否定、迷信外国的自卑主义;还应成为一种方法,对研究对象、外来理论尽量保持平视姿态,以客观公允为旨归,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更进而上升为一种理念,既充分揭示对象丰富复杂的面貌, 又着眼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整合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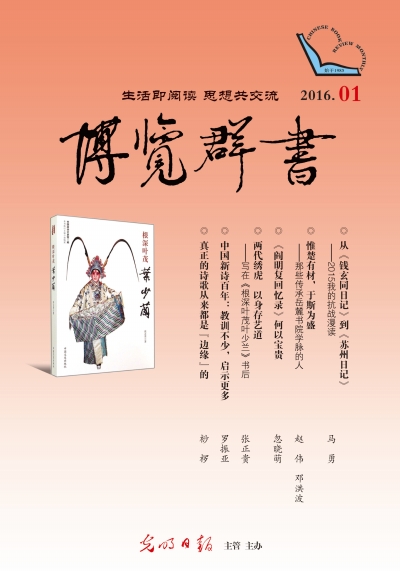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