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等5部作品成为新的文学“宠儿”。从总体上看,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着怎样的风格特征?有哪些获奖作品至今魅力依旧?设立这个重大奖项的作家茅盾先生在文学创作上有着什么样的艺术追求?我们邀请三位学者撰文,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他们各自的看法。
根据茅盾先生以捐献稿费设立长篇小说奖金的生前意愿,中国作协于1981年3月正式设立了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12月开评首届以来,以大致四年一届的频次(前两届分别为5年和3年),已在33年间评选了9届,先后有43部作品荣获彰奖。
自“茅奖”开评以来,围绕着各届获奖作品看法各各不一,议论持续不断,可以说,茅盾文学奖就是伴随着种种争议一路前行的,并越来越为文坛内外所广泛关注。
一个奖项是否评选权威,是否运作得当,关键还在于获奖作品本身。客观地说,茅盾文学奖在30多年的评选中,每届都不乏遗珠之憾,但比较而言,还是做到了在同个时期的作品中选优拔萃。因此,这些作品既是不同时期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与典型代表,把它们总合起来,又构成了对新时期到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巡礼。
采用一届“茅奖”一部作品的方式,对“茅奖”进行一种历时性的文本考察,借此向那些贡献了优秀成果的作家表达敬意,也以此来对3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作一个以点带面的回顾与勾勒。
第一届《芙蓉镇》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77年至1981年间的长篇小说。
这个时期正是文坛的劫后复苏和新时期的初开序幕。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对于“四人帮”文艺路线及其极左文艺思潮的批判与清算之后,文学创作随着文学论争逐步复苏,走在前边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创作属于刚刚起步,写作的作家和发表的作品,数量都还不多,这也使得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普遍较高。这一届的获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东方》(魏巍)、《将军吟》(莫应丰)、《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芙蓉镇》(古华)、《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就从不同的题材领域和迥异的艺术风格,显示了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作者多为文学名家、作品质量也普遍较高的基本情形。
写作《芙蓉镇》的古华,当时还属一个文学新人。这部主写“文革”前后各色人等的命运转承的作品,从题材上和题旨上看,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血脉勾连,但在写法上,却完全走出了其他作品滞留于“运动”反思的通病,从民俗、民情入手,为人性、人情把脉,由胡玉音、秦书田等人的基本生存被压抑,简单愿望被遏制的日常生活图景,揭示了“极左”与“文革”作为“人祸”的本相与影响。作者胸间不无愤懑,笔端也不乏幽怨,但却以忧伤的田园牧歌的方式款款道来,在引人入胜中引人思忖,思想的内力与艺术的魅力水乳交融,忧郁的内在情绪与悠扬的外在情调相得益彰。在一定意义上,这部作品可看作是当代作家从“伤痕”、“反思”淡出,走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的一个转折。
第二届 《沉重的翅膀》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82年至1984年间的长篇小说。
当时,在理论批评由思潮批判转向理论建设的有力推动下,也在其他文学体裁普遍转入对于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影响下,一些作家开始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写出了一批有新意又有分量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改革文学”由此应运而生。这一届的三部获奖作品,除去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之外,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的《钟鼓楼》,都属于现实题材的写作。
《沉重的翅膀》是作家张洁的首部长篇小说,曾首发于《十月》1981年第5期。作品甫一发表,便争议不断。肯定者认为作品“全面反映经济改革”,“代表了改革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而批评者则认为,作品有“明显的政治性错误”,写法上也“显得过于放肆”。因此,从1982年到1984年,张洁先后修改了四次,最终以修订本获取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就作品的主要内容来看,作品以重工业部和所属工厂的整顿改革为背景,描写了从正副部长、司局长,到普通工人群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态状态和内心世界,堪称描摹了一幅工业战线在改革初期的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和锐利的语言,不加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爱与憎、臧与否。正是这种充分展现作者主体性的写作,引起了文坛内外的种种争议。这部作品终于获取茅盾文学奖,也证明主流文坛在渐次走向宽松与开放,对于又新意又有争议的作品,勇于敞开胸怀予以宽容,敢于表明态度给予支持。
《沉重的翅膀》最终以“修订本”获奖,可谓各有退让,皆大欢喜,这既有一定的意味,也开创了一个先例。
第三届 《平凡的世界》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85年至1988年间的长篇小说。
80年代中后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新时期文学对内总结自身的发展经验,对外借鉴新异的文学养分,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开始走向写作的多样化,风格的多元化。因此,置身于活跃不羁的文学场域,长篇小说的写作,较前数量有所增多,质量也有所提升。这一届的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路遥)、《少年天子》(凌力)、《都市风流》(孙力,余小慧)、《第二个太阳》(刘白羽)、《穆斯林的葬礼》(霍达),就显得题材较为广泛,写法也更为多样。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他倾其心力与体力完成的长篇巨制。路遥在中篇小说《人生》获得成功之后,开始构思更大规模的长篇小说,力求在40岁前完成自己的宏伟计划。因此,从1982年到1988年,他像一个不怠不懈的马拉松长跑者一样,用两年一部的频率写完三部作品,并最终倒在了终点线上。三部曲作品总体来看,是以平铺直叙的写实方式,巨细无遗地反映了“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城乡社会生活的悄然变动,及其在人们心里激起的种种回响。作品更为突出的,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在前行中辄遇挫折,在挫折中又不断奋起,来歌吟青年一代坚持自己的理想的顽强抗争精神,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正因为作品葆有深刻的人生启迪意义和青春励志作用,在出版之后,一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特别受到青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平凡的世界》的长销不衰,也向人们表明,卓具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既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有力度,也在读者阅读中有热度。
第四届 《白鹿原》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89年至1994年间的长篇小说。
进入90年代之后,因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学、文化领域兴起“通俗文学热”、“港台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文学的生存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在长篇小说领域,更多的作家甘于寂寞,潜心创作,使得长篇小说较之过去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在看取生活和表现生活上,表现出更广阔的观察力与更深邃的历史感,这一届的获奖作品,除去现实题材的《骚动之秋》(刘玉民)外,《战争与人》(王火)、《白鹿原》(陈忠实)、《白门柳》(刘斯奋),均为过往历史的个人回望与艺术想象。
作为陈忠实的首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作品以临近西安的城乡交叉地带的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于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气韵与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作品在富含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文化内蕴的同时,还在艺术表现上以宏微相间,虚实相致,卓具与史志意蕴相得益彰的史诗品格。可以说,一部《白鹿原》,既把陈忠实个人的小说写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也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选择了《白鹿原》,在慧眼识珠地彰奖作者陈忠实的同时,也使茅盾文学奖自身的权威性,得到有力的增强,拥有了切实的佐证。
有意味的是,《白鹿原》因评奖中存有较大争议,在确定作者可对作品作适当修订后授予了奖项,这也说明“修订”作为文学方式的妥协,不失为一种获取共识的有效方法。
第五届 《尘埃落定》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95年至1998年间的长篇小说。
90年代中后期,正是长篇小说数量激增的时期。从1998年起,长篇小说的年产量,由过去的每年几百部,上到了每年一千部以上。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因网络文学的兴盛,年轻作者的崛起,长篇小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较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严肃文学领域,直面现实与回望历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主要取向。这一届的获奖作品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张平的《抉择》属于前者,而阿来的《尘埃落定》、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属于后者。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汉藏交界地区的康巴藏族最后一个土司家族两代人的故事,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康巴藏地风土人情的种种神秘,又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土司家族父子、兄弟之间的种种人性隐秘,作品在家族与民族的历史叙事中,蕴含了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诸多意蕴。尤其是作品所着力打造的主角——麦琪土司的二儿子,聪傻难辨,善恶并举,又自然而然地痴守着本色为人的自尊与自立,称得上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典型形象。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也以感觉的朴茂与灵敏,语言的精准与氤氲,令人读来满纸清奇,品来意味深长。《尘埃落定》的出版与获奖,对于作家阿来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给予了有力的肯定,也标示了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以新的高度实现了与中国和世界优秀文学的艺术接轨。
第六届 《历史的天空》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99年至2002年间的长篇小说。
由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文学确实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冲击,那就是网络文学领域里群雄竟起,文学图书市场更看重流行作品,如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等。这种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严肃文学的与时俱进和适时更新。这一届获奖的五部作品,《张居正》(三卷,熊召政)、《无字》(张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英雄时代》(柳建伟)、《东藏记》(宗璞),就是不同题材领域里的出新之作。
写作《历史的天空》之前的徐贵祥,已在军旅文学写作中屡屡获奖,小有影响,但这部作品不仅超越了他之前的小说写作,而且在当代军事题材领域也卓具代表性。《历史的天空》在表现战争和触摸人性上,都有脱出常轨的突破与创新。作品的主人公梁必达(外号梁大牙),原本是一懵懂莽撞之人,误打误撞地参加了八路军,但在一次次的生死之战的磨砺与锤炼中,逐渐成长为英勇的战士乃至高级的将领。作品写出了我军干部从文盲到文明,从自发到自觉真实成长过程,同时又写出了职业军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冷漠和遇到的苦闷,革命精神、军人气息与英雄气魄浑然凝聚,充沛的刚劲、天然的兵味和内在的雄性交织一起,使作品读来引人入胜,鼓荡人心。作品的叙事大开大阖,人物的命运大起大落,也格外显示出了作者张弛有致的超强艺术把控力。
第七届 《秦腔》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2003年至2006年间的长篇小说。
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新的力量介入文化,各种新的元素渗入文学,使得文学、文化领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丰繁与混杂,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注重审美的严肃性写作,靠近市场的类型化写作,日益表现出两极分化和分道扬镳的明显趋向。这也给严肃文学借鉴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学习严肃文学,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新的可能。这一届获奖作品,分别是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其中麦家的《暗算》一作,就属于严肃文学的魂魄与类型小说的手法深度结合的一部力作。
从《浮躁》起,贾平凹写过许多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但《秦腔》超越了他此前的写作,颇具一种集大成的意味。写作这部作品,他动用了他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关于家乡的积累、记忆与困惑。作品在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大变革中,写了农村的新旧交替与农民的游离土地。一边是新兴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强劲冲击,一边是传统村社经济的江河日下的日益解体,农民们在忙活自己的家常生活的同时,无不对目下的出路与今后的前景感到惶惶然、茫茫然。作品里,关于村社文化的式微,关于秦腔艺术的衰落,都使作品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作品像是用苍凉而悲怆的“秦腔”,在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异吟唱一曲悠深致远的挽歌,让人惆怅,引人深思。因为语言表述的方言化和叙事的“鸡零狗碎”,《秦腔》这部作品不是很好读,但难读的《秦腔》费人咀嚼,耐人寻味,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成功。
第八届 《一句顶一万句》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2007年至2010年间的长篇小说。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为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不断加大,过去以严肃文学为主的长篇小说,类型化的作品陡然增多,长篇小说的年生产量也上到了3千到4千部之间,这使长篇小说领域较之过去,更加丰繁,也更加混杂。但严肃文学领域里的长篇小说写作,一些实力派作家坚守自我,锐意探索,使得长篇小说领域总体上保持了应有的平衡,严肃文学板块自身也赢得了内在的丰硕。这一届的获奖作品,张炜的《你爱高原》(10卷本)、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都以各具千秋的佳作力构,反映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在激烈竞争中不断进取的最新斩获。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他的小说写作日渐炉火纯青的一个例证。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有关。主人公就这样在找人过话的过程中,机会不断地失去,人生不断地岔开,走向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方向。这部作品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丰沛与丰盈。从阅读感觉上看,由起初的友人与友人的隔阂,父亲与儿子的嫌隙,似乎是写人与人之间难以“过心”的症结;后来又由杨百顺等人的无常又无定的漂泊,感觉似乎又在写人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乖蹇;细细琢磨,个中又有对乡土性的反思,国民性的审视,乃至人的孤独性的剖示。可以说,作品在由乡土之国的探究中,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就语言与故事的相得益彰来看,这部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第九届 《江南三部曲》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2011年至2014年间的长篇小说。
文学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发生了一件文坛大事,那就是上届茅奖获得者莫言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给严肃文学作家以极大的激励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莫言所代表的以个人叙事讲述中国故事的莫大兴味,这也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创作中追求个性化的叙事与中国化的故事的基本趋向。这一届的获奖作品,除去王蒙的《这边风景》属于旧作新出外,格非《江南三部曲》、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都在以个人化的叙事讲述中国化的故事上,实属自出机杼的新异成果。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包含《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部作品。这个原想表现“乌托邦”主题的三部曲,《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都还比较切题,到第三部《春尽江南》,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从主题到故事,从人物到意趣,都接续着《人面桃花》、《山河入梦》顺势而来,而是把那个“乌托邦”意象为“花家舍”,作了一种完全虚化的处理,甚至以一些商人的附庸风雅,让它变成了物质社会的一处风景。而作品则把叙事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丈夫谭端午与俗世社会的格格不入,妻子庞家玉在生活潮动中的如鱼得水。这种错位的人生,不仅导致了这对大学生夫妇的无奈分手,背后还进而隐喻了青年知识分子在生活冲刷中的日渐分化。在这里,不仅“花家舍”变味了,而且象谭功达那样钟情于“花家舍”的理想者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谭端午这样守住了理想却守不住妻子的失败者。作品在谭端午与庞家玉的看似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中,严峻地审视着现实,也严厉地反省着“自我”,苦涩的现实观照之中,别具一种精神拷问的深长意味。格非的小说写作,数量不多,质量很高。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小说创作是当下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代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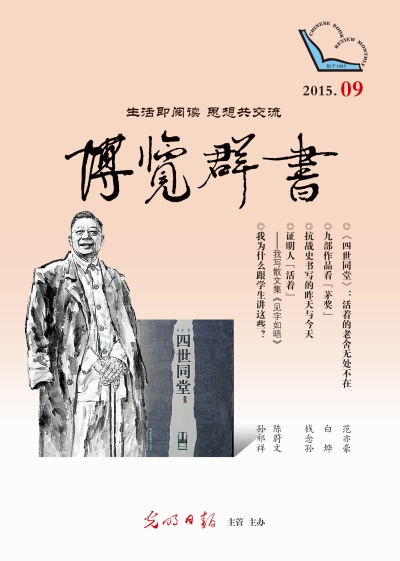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