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茅盾文学奖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它逐渐成为了中国的最高文学奖,并被誉为当代文学的高峰走势与存在真景。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它长期遭到争议、批评甚至否定,尤其是“遗珠之憾”更使其成为文学风暴的核心所在。不过,尽管“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但它却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中愈来愈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风格及美学走向。
·家国情怀的沉潜·
当下的文学创作,无论私人叙事还是集体叙事,甚至是零度叙事,都不自觉地继承了宏大叙事的精魂,犹如沙子中藏着宇宙,滴水见证太阳,茅盾文学奖的对象选择始终也蕴含着宏大叙事所承传的家国情怀。
这种“家国”情怀首先表现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冬天里的春天》《黄河东流去》《你在高原》《白鹿原》《战争和人》到“茶人三部曲”等,都在总体上更关注时代动荡中国家的生死存亡;作者往往会通过诸多个体跌宕起伏的命运传奇而聚焦了整个国家在历史关头的重大变迁。
在价值取向上,这些获奖作品往往是集体性的价值指标压倒了个体化的价值需求。“人”,首先表现为国家的存在符号,然后才是生命个体。因此,为国家而无私奉献一切成了人物典型至高的人生追求。如《张居正》所表达的改革行动,就带有林则徐的一往无前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尽管仕途风险重重,但同名主人公张居正仍怀着造福于国、于民的宗旨,霹雳改革,成效显著;尽管逝后毁谤在身,并遭遇了最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整个著作却充满了荡气回肠的崇高精神,以及贯穿着对这种牺牲精神的伟大讴歌。
除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体价值观念体系的构建之外,这种家国情怀还体现为对现代人格、现代社会与现代民族形成的关注。《蛙》以批判的形式、《推拿》以温情的建构、《天行者》以无私的奉献、《英雄时代》以大刀阔斧的开拓精神,显示了从人格、社会与民族层面的现代化建构。茅盾文学奖把握住这种“主旋律”,既从否定的方面批判了“逆现代化”的现象,也以“时代”作为剖析的对象,对这种现代化予以了“过程分析”及横截面的呈现,从正面对这种建构能量进行了典型的释放。
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家国情怀成为评委们至为深刻的寄托;他们又以“潜在”的方式,将之牢牢地深植于获奖作品所形成的美学价值体系中。也可以这样说,茅盾文学奖的家国情怀成了当代文学的价值矢量,不断地引领着主旋律文学的漫漫前行。
·史诗精神的拓展·
从新时期之初茅盾文学奖举办以来,无论是从评奖“条例”,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来看,史诗性仿佛都成了当代文学的最高标准,也相应地成了茅盾文学奖评选的内在规范。
所谓史诗,普遍说法就是能够全面地反映某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等的长篇小说。当然,正是由于对史诗性的如此理解,所以,茅盾文学奖早期获奖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黄河东流去》《战争和人》《白鹿原》及“茶人三部曲”等,确实成了当代文学的典范。但对开放的、审美多元化的,以及愈来愈向内发展的文学潮流来说,这种史诗标准也遭遇到了愈来愈多的挑战,以至于当《白鹿原》出来之时,遭遇了一些人极为苛刻的评价,认为是“史诗的空洞”,甚至还认为是作者陈忠实首先依据过去的传统的史诗理念,然后设定了空洞的史诗框架,将人物、故事、情节无序地塞入史诗的框架。尽管作者为追求史诗的魅力而殚精竭虑,但却违背了自己的审美才华而胡乱拼凑与堆砌,呈现给读者的只是生硬、虚伪、臃肿的生活素材,而缺乏作者最为珍贵的生命参与。因此,这些史诗小说不过就是了无生气的素材而已。
这种批评在揭示了某些史诗著作所呈现的弊端之时,也武断地将史诗固化,甚至绝对化了。尽管文学创作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十年的文学年轮已今非昔比,但茅盾文学奖的传统、担当与自主的美学意识,使它的史诗情节不可能轻易地消逝。也可以说,史诗性追求成了茅盾文学奖“原乡”情结。不过,在汹涌而来的文学新潮面前,茅盾文学奖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地拓展史诗的概念、内涵、类型与形式。就以对茅盾文学奖八届获奖作品的考察来看,约略可以将之分为如下几种史诗类型:
国家史诗。也就是比较吻合“主旋律”的史诗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身上,寄托了强烈的国家意志,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思考,尤其是对国家在伟大的历史关头所呈现出来的苦难、转型与奋起。相对而言,它们更注重对国家现实层面的思考,并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传奇来展现历史的理想逻辑,像《东方》《将军》《英雄时代》等都可算为此类。
民族史诗。如果说国家史诗表现的是对国家主旋律的横截面的思考的话,民族史诗则是对主旋律的溯源之旅,这些作品的思考是更为深沉的,所展现的时空也更为广大。同时,其所表现的内涵也更为深刻、细腻与琐碎,《白门柳》《无字》《你在高原》《张居正》等小说可以归入此类。
社会史诗。这主要呈现出社会本身的生态,尽管也有着对民族国家的宏大思考,但这些作品更呈现出对社会现实的痴恋,以及对中国人生活常态的描述和表现。可以说,这类史诗描绘出了现实中某种稳定的常态的日常的事物及其生活,呈现的是一幅恒久的、静态的生存图像,《推拿》《天行者》《长恨歌》《平凡的世界》即是如此。
个体史诗。尽管人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些典型的个体身上,往往聚焦了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种种因素。个体就是一面镜子,聚焦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内涵。但相对于集体史诗而言,个体史诗更为强调的还是人的命运遭际,个体永远是表现的“核心”,那些宏大的因素则成了背景。法国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即是这种私人史诗的典型。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像《李自成》《穆斯林的葬礼》《无字》等即是如此。同时,这种个体有时候又会分化为不同形象,或者说,以性格的不同方面而演绎成种种的“人”,《天行者》《推拿》等作品亦可算是。
生命史诗。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考察。与个体史诗相比,其更体现在对生命本身的思考,而渐渐淡化了社会的背景,呈现出人与自然的亲近,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即是如此。
灵魂史诗。亦可叫心灵史诗,主要是对内表现广阔的心灵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这类心灵史诗并非仅仅是对内在宇宙的绝对表述,而主要是表现了心灵对外在世界的映射,如《尘埃落定》即是如此。或者说,这类作品是将外在的社会生活融入进内在的心灵叙述之中,而非西方的那种对自我心灵宇宙的绝对探索。
这几类对茅盾文学奖史诗类型的概括未必完全准确,因为,获奖作品是复杂、丰富的,也往往因跨界而呈现多种史诗类型的态势。所以,本文对这种史诗类型的划分,更多是基于对其核心指标的某种确认。其实,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史诗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史诗精神也始终不曾离开。相信在以后的评选中,这种史诗精神还将以其他的形式存在,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式。
·艺术表达的丰富·
长期以来,几乎每届茅盾文学奖都会遭遇到这样的指责,即“滞后”或者“忽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最新潮流,因此所评选出来的作品总是比时代慢了步调,尤其是被誉为文学“敏感的神经”之先锋文学创作,以及新世纪兴起来的网络文学,往往很难成为它的关注对象。这种批评尽管有其充分的理由,但也表现出其对茅盾文学奖在艺术表现方面所做的开拓缺乏深度关注。作为中国的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难以接受失败的代价的。事实上,茅盾文学奖并没有忽略文学新潮及其对文坛冲击带来的艺术变革,它以更成熟的方式,呈现出了多彩的艺术新面貌。
这其中就包括艺术元素复合化,即茅盾文学奖更青睐那些创造性地转化了文学新的技巧之作品。纵横西方的诸多文学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法,在同步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步伐的同时,也难免因为生吞活剥或者水土不服而出现了许多文学次品。其实,真正的成功者往往能够将诸多的艺术手法与中国的题材、资源与审美习惯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化的意识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作品。这些作品,在总体上呈现出东方风貌,但在细节、局部与具体的表现手段上已充分地融合了西方那些文学技巧。这样,由“大东方”与“小西方”所创造的“陌生感”,往往给文学作品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作品将诸多文学技巧融为一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实际上也体现了古今中外的艺术元素因杂糅而出现的创化与复合化,如《你在高原》《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
话语表达简单化也是一个方面。茅盾文学奖的诸多获奖作品,在兼收并蓄不同艺术的流派、观念与技巧之时,又期待以最简单的表达,直抵事物的本身,尤其是与当代读者的审美传统实现无缝对接。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诸多获奖作品总是皈依现实主义的精魂,在“极简”中呈现社会的真相、时代的趋势、民族的精神、个体的命运、灵魂的更变等等内容。这种“极简主义”也将许多表现手法的复杂的内涵、曲折以及论证剥离,而仅留下直接的表现手段,从而将意义裸露。
还有就是意义宗旨的丰富化。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总是追求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境界,同时追求“杯子效应”,即不同的读者面对获奖作品时,都可以有自己的意义关注,从而实现作品意义的自我实现。可以说,《红楼梦》的“千面效应”亦成了茅盾文学奖的追求目标。这一点从《穆斯林的葬礼》即可窥见一斑,它既是女性的精神史,也是穆斯林的命运史,还是中华民族的个体叙事史;又如《长恨歌》这部作品,可谓既是生命史,也是社会史,还是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这种意义丰富、繁复驳杂及其开放性,成为茅盾文学奖评奖时不可移易的考量。
以复合的技术为支撑,以简单的表达为路径,以丰富的意义为宗旨,成了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内在指标体系。茅盾文学奖的每部获奖作品,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体系、特色与风格,而从美学层面来看,它们又以合理的方式,不断地推进着茅盾文学奖美学风格的建构。作为一种开放的结构,茅盾文学奖既容纳着当代文学新潮对成规的不断挑战,又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新意境的开拓与创化。正是在这种源源不断的新陈代谢中,茅盾文学奖以闪亮的登场方式,深沉地聚焦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者为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著有《茅盾文学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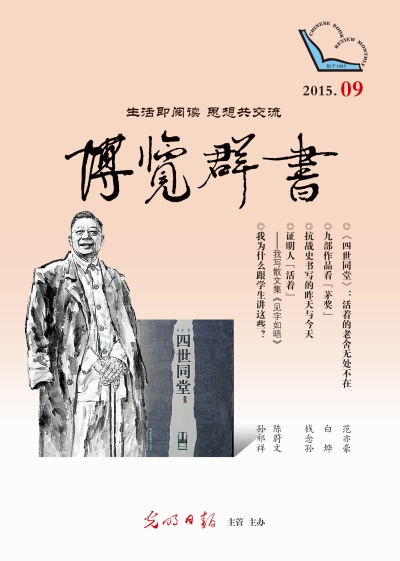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