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女权主义通常是对男权的反动,然而在近代中国却不尽然。日本学者须藤瑞代的研究表明,晚清“女权”概念的发生不是针对男权,而是指向其他民族国家及其国民。一方面,列强环伺的衰弱中国,被象征性地投射在中国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女子受教育,倡议女子放足,提倡晚婚,其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女性的身心素质,从而有利于生育优良的后代,改善国民素质,进而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得很清楚:“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女学为保种之权舆”。以“国民之母”来理解女性在当时甚为流行,对女性“权利”的主张多以此为据,并往往再加上一条理由:女性接受教育,增强能力,在经济上由“分利”之人转变为“生利”之人,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正因为晚清“女权”概念的形成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梁启超当时虽然提倡女权,却根本不提“男女平等”,因为他们矛头所向不是男权对女权的压迫。
这种状况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较大的变化。随着女性运动、自由恋爱和贞操论等欧美思想传入中国,作为女权主题的“女人”才从“母亲”的身份下剥离出来,不必继续保持与救亡图存的逻辑勾连,尽管仍有不少人继续以母亲形象理解女性。从母亲形象中剥离出来的“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和权利得以突显出来,“男女平等”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口号,对男性的盲从和依赖成为批判对象。尽管像陈撷芬、张竹君等人仍然把女性的自立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但是男女平等、基于天赋人权的“女权”的矛头所向的确是男权。到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刘师培之妻)那里,这种倾向就尤为突出:她批判儒教给女性指定的社会职责主要是生育教养后代和家政服务;她讽刺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论者之所以提倡放足和女子教育,是为了解决男性经济上的困窘,是为了培养优秀孩子;她断言近代中国“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与前人的妇女解放论分庭抗礼。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从救国轨迹中脱离出来的“女权主义”,甚至一度超越了国家界线。在1920-1925年期间,中国的《妇女杂志》频频关注“被压迫的日本女性”,把“女性”从“日本”中剥离出来:她们把日本女性称为“东邻姊妹”,其根据即在于同为“被压迫的女性”的身份认同;她们有着共同的抗争对象——“男权”,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女权”跨越了国家主权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权利主体的女人与作为国民之母的女人两个身份指认之间不仅截然分立,而且呈针锋相对之势。
因为这些争论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因而《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一书的作者须藤瑞代认为近代中国围绕“女权”概念的争论折射出西方国家体制与人权思想之间的内在矛盾。她说:
如果完全实现“天赋人权”的理念,是不可以有根据性别而出现的差别的。可是在西方诸国,女性是在家庭内作为妻子或母亲担任再生产劳动的存在。换言之,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文明”的西方诸国,却是没有根据“天赋人权”保障男女平等的国家。
她说清末出现多种不同的女权论述,是因为西方诸国的国家体制与源于西方的人权思想之间本来就隐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国的女权议论里浮现出来,并表面化了。我以为这种论述有待商榷。西方诸国女性是否主要是在家庭内担任妻子或母亲的角色,需以就业率为据;西方的国家体制与性别分工之间是否有必然性勾连,值得怀疑;性别分工是否违背“天赋人权”理念,更恐非定论。窃以为,以“天赋人权”为由否定性别分工,背后的预设是女性和男性具有完全相同的先天条件,且把性别分工归罪于男权压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体育运动要分男女比赛,为什么在许多文化中常有“男不与女斗”、“女士优先”的风尚,为什么在大多数法律中强奸罪仅适用于男性而不适用于女性?那是因为性别歧视呢,还是出于对男女天生差异给予尊重?笔者的意见倾向于后者,而且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值得珍视的高贵传统。无可讳言,历史和现实中都不缺少男权中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的证成不应建立在否定男女天生差异上。窃以为正因为作者抱持着女权主义的理论僭妄,才导致对近代中国关于“女权”概念的争论做出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和判断。
我以为,与其以女权主义的理论预设去看待近代中国的“女权”争论,不如把它放置到近代中国更为广阔的思想脉络中去理解。正如众多研究所揭示的,不少清末知识分子在理解西方的自由、权利、人权概念时,是从救亡图存的路径进入的。从这种视角去理解自由、权利,再加上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他们往往难以深入体会到“天赋人权”这几个字背后的深意;因而,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常常倡议“人人牺牲一点自由,为国家争自由”。这种倾向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五四时期,种种机缘促使个人主义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深入的理解,自由、权利才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个人自由遭到更严重侵犯之后,知识分子才更多地体会天赋人权的的深意。我所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张佛泉1949年流寓台湾之后,沉痛地说:
以前我们读英美人“无法出让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说,辄将它轻易放过,实在并未懂得。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理解近代中国女权论述的竞争和变迁,则比较容易理解其所由自。梁启超等人以“国民之母”理解女性自不待言,尽管他们也常以“天赋人权”来论证“女权”,然作为自然权利的女性人权并未深入他们脑中;1920-1925年间,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作为权利主体的“女性”从救国轨道中脱离出来是顺理成章的;1925年之后“妇女回家”的倡议,则与党国体制的意识形态主导有很大关系。当然,主流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歧异意见不存在,它们作为潜流暗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地下层,与社会局势暗通款曲,随着局势的变迁,暗流往往重回地面,支流变为主流,在中国思想史中奔涌向前。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本文编辑 宋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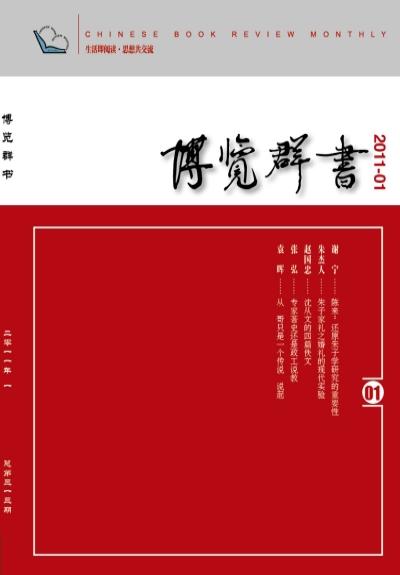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