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以下简称《1988》)的畅销及其限量版“黄金甲”再一次把韩寒推入戏剧性的中心,成为网络上下舆论的热点。
正如作家田耳所言,这是一个戏剧丛生的时代。写下这个题目,我想表达三层意思:首先,韩寒的成名本身就是当代社会戏剧性的绝佳体现;其次,韩寒围绕《1988》限量版所导演的是一出以商业化机制中某些固有模式为目标的“微型反抗”戏剧;再次,《1988》所展示的韩寒小说的力量在于其捕捉当代社会戏剧性的宏大野心。
一
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的失落”状况在学者的呼吁声中并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状况在文学场中表现为文学场向商业化原则的倾斜,畅销书体制的建立。除了若干大奖、小奖,文学引起普通读者关注的恐怕只剩下书商们及文化掮客们竭力炒作的各种概念。从“身体写作”到“美女文学”到“胸口写作”,写作这一精神性事业与身体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美女文学”衰落之后,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热潮,“青春文学”、“低龄写作”很快登场,各种“天才少年”、“天才少女”应运而生。这些文学天才一出场就抛开传统作家先写短篇、中篇而后攻克长篇的陈旧套路,直接冲击长篇小说市场,并且很快获得骄人战绩,在畅销书排行榜上遥遥领先。80后作家中的代表人物郭敬明、张悦然也趁势而上,利用自身在网络上下积累的人气,主编杂志,安营扎寨。畅销书机制的运作、网络时代博客作文的兴起、文学粉丝的聚集、年轻一代网民的文化消费能力的形成与对同代作家的兴趣,使80后作家一夜之间从后排站到了前排,从而创造了类似郭敬明这样虽然屡屡被指抄袭、作品却越来越畅销的怪现状,郭敬明的近作《爵迹》还创造了首印200万册的奇迹。
韩寒无疑是“青春文学热”中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其中最好的部分。与其他青春文学作家不同,韩寒的文字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需要别人检阅的“忧伤”,也没有参与“小时代”的洋洋得意,而是充满了一个青年对时代病症的清醒观察与深刻批判。从《三重门》对应试教育体制的批评,到“韩白之争”对文学界权威的质疑,到博客文章中直接介入各种社会议题,韩寒以其执着的批判精神成为80后最具公共意识、影响最大的作家。时势造英雄,它既能造就郭敬明这样的伪英雄、伪作家,也能使韩寒这样有担当的作家脱颖而出。当代社会的戏剧性并不总是生产“芙蓉姐姐”、“凤姐”这样的闹剧,它偶尔也能结出好果子。
80后与市场、图书商业化机制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完全被动接受商业化机制的摆布。韩寒受益于90年代以来建立的畅销书体制,但他并没有臣服于这个体制,他的反叛精神无处不在。限量版本是出版社与作者为提升作者象征资本并收获额外经济资本的商业行为。与郭敬明的《爵迹》在赚得盆满钵满后还利用两万本限量版狠捞一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寒在《1988》限量版中给心仪自己的读者赠送黄金。黄金虽少,意义重大。它使得韩寒与读者的关系超越了商业化机制下的利益依存关系。韩寒的行为不可复制,这一行为的意义毋宁说在于解构了“限量版”这一名利双收的固有商业模式,反讽了“限量版”的营利性实质。送钱这个“行为艺术”无疑是韩寒导演的一出绝妙戏剧,再一次证明了韩寒的目光远大、前途不可“限量”。
二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同样,文学作品中的戏剧性冲突取材于生活,又通过作者的想象、加工以相对集中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现实生活的戏剧性有时候甚至超出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反过来说,能否最大限度地捕捉现实生活的戏剧性,揭示社会生活的种种症候,是考察当代作家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最重要的标准。
《1988》是韩寒的第六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自认为迄今写得最好的小说。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很多人把这部小说与公路片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我认为,这篇小说在结构上的渊源可以上溯到西方的流浪汉小说。韩寒《三重门》之后的所有小说,《像少年啦飞驰》、《一座城池》、《光荣日》、《他的国》都可以归入流浪汉小说的范畴,包括仿武侠小说《长安乱》。流浪汉小说大多通过底层小人物在民间的流浪经历反映社会生活的种种病症与问题,表达底层人物的辛酸。韩寒有意无意间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接续了这一传统。同样,《1988》也讲述了“我”与底层妓女娜娜在318国道上的流浪历程。与前述作品相比,《1988》在题旨的野心上更为宏大;在结构上更加明晰、完整,安排了现实之旅与成长历程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并加强了两条线索之间的相互参照、对比,从而强化了整个作品的思想涵盖力与讽喻性。
《1988》在题目上与此前出版热销的村上春树的作品《1Q84》的戏剧性相遇,在我看来不是巧合,而是“英雄所见略同”。《1Q84》,据村上所言,是向奥威尔致敬的小说,因为它同样是关注人类生存体制与精神困境的小说。《1Q84》对现代邪教等人类“精神囚笼”的抨击不遗余力,是对奥威尔所代表的“反乌托邦小说”传统的延续,虽然讲述过去,但“意在未来”。《1988》副标题“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同样表达了作者对这个世界存在病症的深度关切与思考。虽然在思想深度上韩寒可能与前辈作家尚有很大距离,但其思考向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1988”在文本中指代主人公“我”开的一辆1988年产的旧车,在文本潜在的含义中,“1988”所象征的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成为批判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全面沉沦的一面旗帜。
在“现实之旅”这条线上,小说聚焦于底层妓女的“非人”处境。娜娜怀了身孕,因为某个客人干活时偷偷拿掉了避孕套。虽然她不能为这个孩子的未来提供物质、精神、身份的保障,但她还是希望以自己的劳动养活这个孩子,只要她不重复自己的可悲人生。这种可悲的生涯首先体现在她不能使用自己的本名而只能使用假名,也因此,她除了要遭遇类似与“我”一起经历的暴力执法,还要受到城管之流从金钱到身体的野蛮盘剥以及无良医生的掠夺。不仅如此,甚至连她的爱情和梦想都受到盘剥。她喜欢的人是桑拿中心老板孙老板,理由很充分。对于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姑娘,这样一个能干的男人不可能不成为她的理想对象。但她或许不明白的是,自己的青春与爱情从一开始就被引进歧途。她因为爱唱歌,所以除了进桑拿中心,在潜意识中还有一个梦想。一个号称王菲音乐制作人的嫖客声称回去后要包装她,她痴痴等待他的电话,给他免单,幻想自己出名,幻想自己和他谈恋爱,结果自然是一场空。这个无耻的男人,同样对她进行了从身体到梦想的双重盘剥。
“成长历程”由“我”的回忆及与娜娜的对话完成,回忆的重心是1988前后那几年自己的成长历程,或者说是成长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影响自己最大的有两个同性,一个是丁丁哥哥,一个是10号。丁丁哥哥因其敢作敢为、果敢成熟成为“我”的偶像。10号有着同龄孩子没有的胆量,他敢于反抗大哥哥的压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把玻璃珠子吞到肚子里。后来他成了镇上的“大哥”,在飙车事故中死亡。作者还讲述了“我”的两次爱情经历。“我”的第一次爱情颇具戏剧性,由于不小心爬到旗杆上下不来,在万人瞩目时我看中了底下看热闹的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子刘茵茵,并毫无理由地爱上了她。这一段爱情书写可以说是对“校园爱情”的反讽。后来,这个女孩与10号一起在飙车事故中身亡。“我”的第二段恋情是在当记者时与明星班学生孟孟谈恋爱。这段爱情更是戏剧丛生。更具戏剧性的是,娜娜看了孟孟的照片,指出孟孟就是她们行业里的“一姐”孟欣童。就像孟孟的实验所表明的,丁丁哥哥的说法是不现实的,温水里的青蛙在跳出之前被锅盖盖死在里面,这才是现实。这也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的可怕之处在于“我”的成长历程中所经历的人物在“现实之旅”中发生了重大变动,丁丁哥哥突然死亡了,10号变成了“大哥”,孟孟变成了孟欣童,执法者、医生、记者的现实形象与我想象中的天差地别。
延续了传统流浪汉小说的渊源,《1988》暴露了现实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样在传统流浪汉小说中存在的主人公价值观念模糊等问题在这篇小说中也某种程度地存在。作者与叙述者第一人称“我”之间距离模糊,容易使读者将叙述者“我”的行为与作者直接划上等号。由于作者本人在年轻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叙述者“我”的一些行为比如与娜娜之间的性交易容易对读者产生认识上的误导。从叙述者“我”在小说文本中承担的功能而言,如果“我”自身的行为都是不干净的,那么对诸多不良现象的巨大的批判力显然也会因此大打折扣。“1988”是辆好车,“从来没有把我撂在路上”,因此,“我”也不能辜负这辆好车。
作者单位:武警福州指挥学院文化教研室
(本文编辑 李文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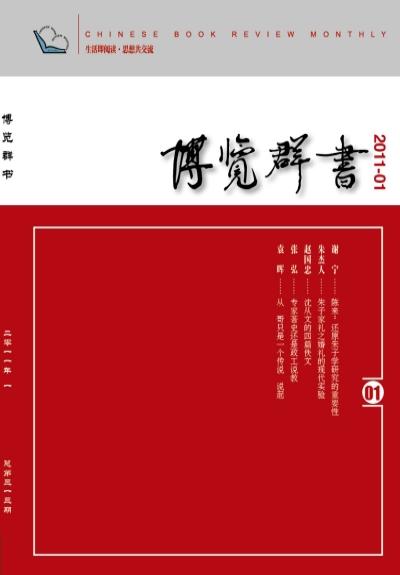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