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城市带来的辉煌和面临问题之时,我们发现,我们所能依赖的东西其实更多的是想象。城市就那样现实地存在着,就那样将我们包容其间,并不断扩展着它的内涵与外延,约翰·里德说:“到2030年的时候,每三个人里将会有两个生活在城市。”对于这个庞大的存在物,我们肯定有许多具体的科学的手法探究它的方方面面,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很大程度却出自想象,或者被想象所支配。
这看上去更像一种诗歌的表达而不是关于城市问题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与人们所喜爱的大自然一样,确实激发诗性,“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母语》,哥布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P174)这是置身于城市但又并不认同和融入的心灵写照,出自云南边地一位青年诗人之手。我借它说明的是,不管你喜欢与否,城市都会直指心灵,同时打开你的想象。
这也就是对城市的评价历来毁誉参半一个根源。不管城市被高楼、街区、林荫大道和霓虹装饰得多么美轮美奂,城市最可亲近的一面只会是它的个性,或者它的个人化存在。当然要使钢筋、水泥、石块的堆砌产生温情甚至生命的活力,有史以来尝试颇多却并不容易实现。许多时候,人们对城市的成就心照不宣,对它的负面却印象深刻。约翰·里德在回顾城市的历史状态时认为,城市给天才和暴君提供了激发他们雄心壮志的土壤,但同时更有成千上万人没有从城市中得到半点好处。“城市就是人类文明的明确产物。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都微缩进它的物质和社会结构。”刘易斯·芒福德在他极富理性的经典著作《城市发展史》中,十分详细地梳理了城市的起源、演变和前景,也不时地谴责城市,因为它帮助造成了不幸或是促使其居民做出任性而无用的决定。因此,里德写道:城市被定义为文明的产物,但是它们也是危险的寄生物,能够祸害远离其边界的广大地区。
约翰·里德这本叫《城市》的书2004年在英国出版,2010年郝笑丛先生将之译为中文,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被译者誉为堪与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媲美。通过对最初的城市毁灭到现在的城市状况的系列研究,约翰·里德探索了城市如何联合、发展、兴盛,如何衰落和消亡,如何能够自我重建。里德还研究了城市与其周围乡村的寄生关系,城市赖以为生的贸易网络和外来移民,城市如何为居民提供食物和用水,如何处理排出的废物。他着力聚焦奥斯曼男爵对巴黎下水道的创造性,在此花费的笔墨一点也不逊于男爵的林荫大道规划,他对疾病和政府问题同样关注;在描述人类生活和建筑物上不分伯仲。总而言之,这是一次对城市为何以及曾经为何的全面探究。但最为动人的是,里德复活了城市。作为一个作家和摄影记者的里德,拥有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的荣誉研究学位,是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皇家地理科学学院的成员。
城市并非天生存在,它像孩子一样长大,形成了不可遏制的活力,以及缺点。关于城市的产生,一般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农夫们发现了一种增产粮食超过了自己需求的方法。但里德似乎更赞成这样的观念:城市首先出现,随后,出于对城市需求的积极反应,农业技术得以推进。在苏美尔地区的加泰土丘,这个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的地方,里德想象性的描述复活了古老的城市生活(当然他运用了充分的史料),也为这个观点找到了依据。但我们也许会更看重他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表达:尽管城市一直是由周边地区的农业盈余维持着,但是它们却不是由其创造的。事实刚好相反,就是因为城市的建立,才刺激了农业的过剩生产。不是农夫,而是相关的手工艺人、商人和管理者组成平等的部落,同时在观念和在物质表达两个方面,为城市和城市生活奠定了基础。这种认识具有启示性,现代社会的城市发展是否也体现了早期城市的这种功能与价值?这是值得深思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由于城市机制及其运作链条的失衡,城市最朴素的带动作用难以保持并不断放大,城市转而成为依赖性资源消费的场所,它以攫取周边广大地区的养分成活,这类寄生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回顾历史,违背城市初衷的行为时有发生,因而即使那些最著名的城市在成长中也显现了粗鲁和尴尬。中世纪的伦敦在垃圾特别是人的排泄物的处理上就让人吃惊。据里德描述,伦敦城制定了关于处置垃圾的规章制度,但人们并不总是遵守或者严格执行。在1349年,国王爱德华三世亲自写信给伦敦市长,抱怨“白天黑夜都有污秽之物从房子里扔出来,在大街小巷里穿行的人们经常会被人的排泄物弄脏,城市的空气有毒,给过往人群带来极大危险……”他因此命令城市和郊区净化所有气味,并且像古代一样保持清洁。这不单单是伦敦的情况,巴黎和米兰这些城市也遭遇了这类情形,以至于达·芬奇要在公共建筑中设计螺旋形楼梯,这样人们就不能在黑暗的拐角处小便了(因为人们通常在方形楼梯的平台上干这种事)。但是我们知道,垃圾以及城市所有废弃物的处理是城市永远的难题,与城市一道诞生,与食物、能源和水的供给一样重要,由于处理废弃物肮脏复杂,往往低人一等,因此这些什物以及它们带着的问题往往在城市的暗处长久徘徊,考量着城市的文明程度,直至现代。今天,那些光鲜亮丽的城市有几个能够自信地宣称已经彻底干净?包括垃圾的处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这里不妨引述一段里德的原文:
从中世纪伦敦的污物处理问题到现代发达国家城市的杀菌清洁卫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是,这个进程还远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迅速和普及。例如,纽约市在1986年每天还仍然将未经处理的7.5亿升污水直接排入哈得孙河,排污口就在乔治华盛顿桥的南边。到1996年,污水处理厂在清除百分之九十的有机物之后再排放。与此同时,一份1997年的报告披露,中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污水在排放到土地里作肥料之前接受过某些处理。(《城市》,P252)
我们知道,受污染的河流和土地不仅只属于城市,它们覆盖了更广的地区,城市把它的负面转嫁到了别处,同时也把一个技术问题转化为一个社会伦理问题,使城市面临道德的挑战。虽然时间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可以肯定这种状态依然存在,而且范围已大大扩展。在某些发展中的城市,甚至还保留着中世纪类似垃圾处理的“遗风”。的确,城市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在城市的现实世界中,城市负面效应和它的显赫成就一样直观。交通拥堵、住房压力、贫富差异、热岛现象、环境噪声、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种种非宜居或不和谐现象使发展中的城市饱受诟病,引发诸多质疑,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是否真的已让生活更加美好?
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必须找到更为积极的路径,想象在这里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城市》中,里德把这个通向未来的话题命名为“沉重的脚步”,并把它放在了书的最后位置。“生活质量”成为这节关注的重点。里德引用了一个世界领先的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年度报告来说明问题。报告所列指标的范围很广,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到气候、住房、公共服务、交通、医疗和卫生设施、学校、犯罪率、审查制度、消费品的适用性,还有餐馆的大体水准及休闲娱乐活动等等,共39项关键的决定因素。我们看到,在这些因素中,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价值侧重和处理方式,有的达到了很高层次,有的却在低点徘徊。问题是人的期望与日俱增,即使是最完善的城市也存在着永无止境的困难,这些困难又往往纠结于整体性困惑与挑战,城市文明问题最终汇入了人类文明的长河,必须在更高的境界中才能解决。
比如环境问题,每一个城市都在改善自己的环境,但是种种努力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一种整体情形,那就是环境恶化、资源损耗、地球变暖、气候变化。在此背景下,里德发现,我们不断地遭到坏消息和阴沉预言的轰击:上升的海平面将要淹没成千上万的城市和国家;转基因的农作物将会永远改变植物界;森林正在消失;鱼类资源正在减少;动物、鸟类和昆虫种类正在灭绝;土壤被投毒;河流被污染;空气本身已不再适合呼吸;而且,当臭氧层变薄,连太阳光也成了杀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这些都已经成为确定无误的事实,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
芒福德曾寄托于共同信仰来解决过去城市存在的麻烦,里德则着眼于未来,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乐观,因此也代表了我们的观点。他认为,即使是最有眼光的梦想家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知识局限,为未来做的规划也许符合当时对需求和增长的理解,但他们无法考虑到自发的适应、创造更新及技术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城市是一个永远充满了挑战的世界,创造与改变在这里有着无限宽广的需要和可行之途。这实际上正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规律。“石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没有了石头,而是因为某人发现了如何制造青铜。”
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使里德注意到中国的城市,虽然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正面临众多问题。里德认为,在中国,一个理想化的城市概念一直存在并且超越了物质现实。当然里德并没有说明这个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理想化的城市概念”具有何种现实启发意义。这使我想到最近看到的美国城市生态学家、城市设计师、作家理查德·瑞吉斯特的《生态城市》(王如松、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只要注意到它的副标题“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更具想象力的著作。它着眼于未来,试图以全新的方式“重建”更合于自然规律也更人性化的城市。这种生态化的城市设想令人鼓舞,而且他注意到了中国,并提出了富有吸引力的建议:“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城市投资、建设和大规模改变自然与人类环境的关键时期。中国城市要么按照美国的‘汽车-城市蔓延-高速公路-石油’的模式去发展经济,重蹈美国破坏世界环境的覆辙;要么就必须利用这个人类历史的重要时机,正视汽车时代固有缺陷的挑战,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大的资源潜力去建设一个比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好得多的生态城市。”无疑,这个建议中包含着更加美好的想象,这其实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美好想象。2010年上海举办了世界城市博览会,这种想象得到证实。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我认为它的鼓舞性作用以及成功的展出并非要在理念上校正人们对城市的看法,而是传达出一个共同的预期。上海世博会用人类在城市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表达了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应该达到的目标。2010年10月6日,在杭州举行的上海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主题论坛上,路甬祥先生致辞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体现了人类对未来城市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上海世博会为世界城市多元文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展现了和谐城市和宜居生活的未来城市多彩多姿的范本。路先生说的是“未来城市”多彩多姿的范本,如果说这是上海世博会重要意义的深入概括,那么我确信我们再一次使用了想象。这个想象包含并强化了一种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思路,那就是尊重城市多元文化,重视环境与城市和谐发展,创新,继承与借鉴人类城市文化的优秀成果等等。无疑,这些词语的共同指向是未来,是我们正在行走的城市化道路和我们正在建设的城市,它们对我们如何有效避免城市发展史上的负面因素提供了想象的指引。
(本文编辑 杨剑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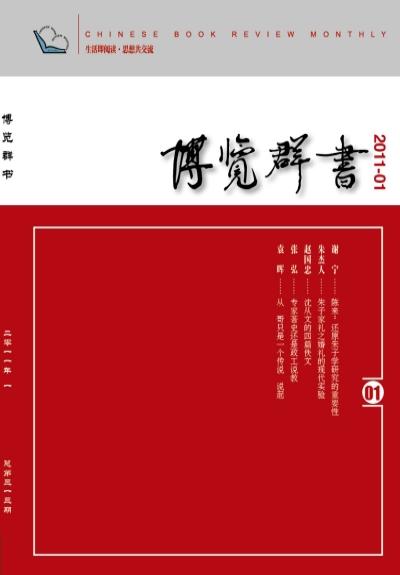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