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一大千”,典出徐悲鸿对老友张大千绘画艺事的推许赞美之辞。徐氏的原话是:“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自序》)时在20世纪30年代。友人李永翘推断说是1936年徐悲鸿邀请张氏任中央大学国画教授期间对友人所说[《荣宝斋》2004年第一期:《张大千图话》(九)]。张氏友人圈遂将此话概括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后演变成媒体评说张氏绘事的常用口语。台湾资深记者、张氏忘年交黄天才先生专以此语制题,写了一部皇皇数十万言的大著。但是有关徐氏此语的内涵,似乎尚无人细究。本文仅就此事谈一点管窥之见,以求证于黄天才先生及海内方家。
徐悲鸿的弦外音
熟悉徐悲鸿艺事的,深知徐氏是一位谦恭、自重又爱才若渴之士,他在赞叹友人或有才之人时,往往采用“天下第一”的形容词来褒扬对方,而对自己则又退居其后说“天下第二”。这个口语习惯迥异于同时代的艺术名家刘海粟。刘氏谈艺,每喜用“老子天下第一”的自负自夸之辞。令人奇怪的是,徐氏在友人前推许张大千,却一改“天下第一”之辞,而用了“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说。这两个说法,有何不同?
众所周知,徐悲鸿不仅是一位绘画大家,而且是开现代美术教育的一代宗师,他对中国绘画史自是知之甚详,对唐宋元明清的各大流派名家更是如数家珍。从他口中说出“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怕不是“天下第一”的翻版,也不仅是泛泛的应酬之辞,而是有深意存焉。
“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起点是20世纪,上推五百年,是15世纪。翻开中国绘画史,15世纪正是明代中期——以沈周、文征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及文征明、唐寅、沈周、周臣史称“明四家”的活动时期。明乎此,徐氏的五百年来之说,是说张大千是继“明四家”和“吴门画派”后的第一人。倘若再深究一步,明四家中的唐寅,既是“吴门画派”的鼻祖沈周的学生,又是“明四家”殿后的周臣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影响超过了两位老师。唐寅号伯虎,多才多艺,命运跌宕起伏,后人为他编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和戏曲,《唐伯虎点秋香》就是其中最为人激赏的一折。而张大千既是李瑞清的学生,又是曾熙的学生,曾、李的学生众多,人称“曾李同门”,在“曾李同门”中,张大千是小师弟,但是后来居上,无论在同门中,还是在社会上,张大千的成就和影响超过了同门其他师兄弟,甚至两位老师。何况二三十年代的张大千也是一位多才多艺风流才子,他的桃色新闻,尤其是他与李秋君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传闻,更是小报记者猎取花边新闻的众多素材。想必徐悲鸿必有耳闻,但是洞悉人间恋情、尝够“师生恋”花边新闻之苦的徐悲鸿,当然心知肚明,这层窗户纸不能点破,只能点到为止,点到五百年,不点“明四家”和“吴门画派”,更不点出唐伯虎。由此看来徐氏不说千年(唐五代),不说八九百年(宋),不说六百年(元),也不说二百年(明末清初),而偏说五百年,其深意庶几在此。当时张氏刚巧自上海迁居苏州网师园,而苏州又正是明四家和吴门画派的集居地。
1936年春,张大千应徐悲鸿推荐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任执教艺术科,同时又在南京举办画展。徐氏先后在《中央日报》发表了《论今日中国之名画家》和《张大千先生》两篇文章,对张氏的绘画艺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论今日中国之名画家》一文中徐氏写道:“夫挟技而成名者,必有一长足可取。至若以艺名千古者,必有多种惊人之才艺,乃得为人所倾倒。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其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仅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几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徐氏认为张氏的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已达到了“大家”的境地,也许是大千自谦,认为不够,但徐氏又加重语气反问道:“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
同年,又经徐氏向老友舒新城推荐,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氏又作序评论。在评论中,徐氏认为大千“生于二百年后,而友八大、石涛、金农、华喦,心与之契,不止发冬心之发,而髯新罗之髯。其登罗浮,早流苦瓜之汗;入莲塘,忍剜朱耷之心”。言外之意是,20世纪的张大千,可与18世纪的明末遗僧、扬州八怪诸画杰结为友侣,心与之契。不仅能师其法,学谁像谁,尤其是石涛、八大,更是形神兼备,可以乱真;而且能师其心,师造化之心,所谓“登罗浮”、“入莲塘”,在名山大川,自然造化中写生领悟,手挥目送,熔铸古今,化古为今,借古开今。无论从画风画艺上,还是在言行习性上,大千与明末八大石涛金冬心华新罗更为贴近,说他为“二百年来第一人”似更确切。但徐氏认为大千的画艺和志向似不能为二百年前贤所囿,当更上追,如若上追到唐五代、宋元,以他当年的功力来说,尚不够,于是退而取其中。倘若再推后十年,张大千赴敦煌礼佛,面壁莫高窟三载归来,也许徐氏会改口说“张大千,千年以来第一人也”。
张大千的回应
读者可能会问:徐悲鸿这句话说得有点太随意,不知张大千听后有何表示?作何回应?我最早见到的回应文字是1972年张氏在旧金山举办《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他在“自序”中写道:
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恶,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高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茭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境囿,吾仰钱瘦铁;花鸟鱼虫,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丈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辞焉。五百年来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悲鸿笑曰:“处世之道,对人自称天下第二,自然无怍。君子伪谦,不亦同予之天下第二者,非耶?”此一时笑乐,忽忽已是四十余年前事,言念及此,可胜感叹!
这段文字写于70年代,却是记录了30年代张氏回应徐氏的一段对话,应该说这段对话不会是张大千的杜撰。那末张氏的回应主旨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五百年来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翻成白话文来说是:“五百年来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
为了说明主旨,张氏又列举比较了南北两地的平世同辈画家的强项优长,以人之长较己之短,来说明“五百年来一人”之不确。应该说,这段论述平心静气,是对老友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难怪徐氏听后要坦言直陈:“处世之道,对人自称天下第二,自然无怍(不会脸红惭愧)”,但对大千处处扬人之长,也一语道破为:“君子伪谦,不亦同予之天下第二者,非耶?”翻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是假谦虚,不是与我自称天下第二的说法一样吗?是不是啊!”
张大千是一位十分自信又颇为自负的绘画大家,但对艺术创作的成就,他确有自知之明,五百年来一大千,他无法做到,也不可能做到。除了他对徐氏所说的这段论述外,还有一段罕为人知的“私房话”:“自己创作的好坏,没有一定标准,各人看法不同,某甲可以把你的作品捧上天,某乙却可以把你的作品批评得体无完肤。一件艺术作品的评价,完全决定于观赏者的主观意识,并无客观标准,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人人都会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谁会服气谁是五百年来第一人?”
这段“私房话”出自张大千对忘年交黄天才的私下交谈,出自黄天才的专著《五百年来一大千》(见台北羲之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11月初版)。黄天才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奉派驻日采访,长达24年,与大千居士结识于东京。六七十年代,张氏几乎每年必到日本,黄天才经常与之出游,谈古论今,多年相聚,相知日深。大千居士对这位小老弟有问必答,从不设防,从而听到了许多罕为人知的大千艺事珍闻。此书就是他与大千居士长期交往的所见所闻,也是一部翔实而生动的文字记录。在此书十一章《张大千奇才异能》中,黄天才曾婉转问过大千,为什么徐悲鸿说他的画是五百年来一大千,他表示不敢接受?大千没有直接答复,却婉婉转转讲了许多话,总结他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就是上面引述的一段“私房话”。黄天才说大千婉婉转转讲了许多话,我的猜想可能就是《四十回顾展》的那段文字。这段“私房话”与自序中的对白一脉相承,但说得更直白更透辟。
紧接谈画话题,转入书画鉴定,张氏却语出惊人地自命为“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1954年日本出版的《大风堂名迹》序言中,他就结合自身数十年收藏鉴定的经验,大言不惭地宣称:“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黄天才就此又进一步求证询问,大千的回答是:“所谓鉴定,是鉴识、研判一幅无款古画的年代和作者是谁。这些鉴识、研判或推断的结论,完全决定于客观因素,鉴赏者的主观意识发生不了作用,任何主观意识都改变不了客观事实。一幅画,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事实只有一个,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综上所述,张氏对徐氏“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回应,可以概括为:艺术成就上不与人争高低,而在书画鉴定上决不让人。换一句话来说,徐氏的“五百年来第一人”,并没有说错,只是说错了门类,归错了队。借用黄天才先生的归纳:“照大千的说法,他在艺术方面的种种成就,都有可能被别人否定掉,但他的鉴识能力,却是谁也否定不掉的”。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张大千的回应?换言之,如何看待张氏的艺术成就?如何评价张氏的鉴定水平?
诚然,书画艺术评比没有客观硬件标准,全凭观赏者的主观意识、审美兴趣爱好,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无法定量分析,品评高下。同是一位书画大家,诸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派系的爱好者眼中,品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张大千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张大千确有自知之明,不在名位上与人一争高低。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品评书画艺术虽然没有绝对硬件标准,但也有相对软件标尺,这杆尺子就是人们常说的画内功夫和画外功夫。画内功夫主要指技法、技能;画外功夫是指天赋、秉性、人生阅历、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因为有了这两大软件,评审员和艺评家才能形成相对接近的品评标准。不然,历代诸如“俗品”、“能品”、“妙品”、“神品”、“逸品”等品级,现当代的画家、名家、大家、巨匠等称谓,也就无法产生了。说到张大千的艺术成就,我十分同意傅申先生的评论:“张大千在绘画上,范围之广,幅度之宽,功夫之深,天赋之高,精进之勤,超越之速,自期之远,自负之高,成就之大,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但是近代大家之一,也是绘画史上的大家之一。”(《雄狮》第250期1991年12月)
至于如何评价张氏的鉴定水平,作为对书画鉴定纯属外行的后生小子,实在不敢置喙一词。不过他与黄天才谈鉴定的“完全决定于客观因素,鉴赏者的主观意识发生不了作用,任何主观意识都改变不了客观事实。一幅画,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事实只有一个,这是绝不能改变的”,据我对鉴定考古界的见闻看,似乎不完全是这样。书画鉴定,虽说决定于客观因素,有些客观因素,如墨、纸、印而今可以用科学仪器来测定年代,但是在张氏所处的时代(乃至五百年间),书画鉴定主要还是凭经验感觉。所谓“夫艺事之极,故与道通。衡鉴之微,唯以神遇”;所谓“一触纸墨,便别宋元;间抚签贉,即区真赝。意之所向,因以目随。神之所驱,宁以迹论”。(见张大千《大风堂名迹序》)张氏在文中所说的神遇、气韵、一触纸墨,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何谓经验?经验者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也可说经验是实践的总结,实践越多,经验越丰富。与古人相比,张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遍览海内公私收藏,诚如他自负言道:“人间名迹,所见逾十九;而敦煌遗迹,时时萦心目间。所见之博,差足傲古人。”见闻是鉴识的前提,没有见闻,也就无法鉴识,更谈不上经验。但是经验不等同客观因素,经验中也包含着鉴赏者的天赋禀性、习惯好恶,乃至特殊的感情因素。以上种种主观意识往往会左右影响鉴赏者的眼力,令你有意无意地“看走眼”。更何况还有高手作伪者(随着高科技的应用,高仿真应运而生)师生合作者(实际上是学生代作者)等诸多复杂因素,更考验着鉴定者的主观意识水平。有鉴于此,“任何主观意识都改变不了客观事实”,怕很难绝对做到。就拿张氏鉴定过的古代书画名迹的断代和真伪而言(尤其台北故宫一些藏品),不是在鉴定界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很难定于一尊?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句话确是真理,但由哪位“绝对权威”来宣示呢?古代书画作家早已长眠地下,终不能起地下之作家求证对质罢。早在二三十年代,张大千气盛好强,仿造石涛,向海内“鉴定权威”挑战,不是先后让罗振玉、黄宾虹、陈半丁看走眼;他制造的梁风子《睡猿图》不是也令大收藏家吴湖帆、叶恭绰上当受骗吗?据悉,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所藏中国古代书画名迹中,有些就是张大千的伪作——被世界著名鉴定家鉴定为真迹的伪作(包括黄宾虹看走眼的“自云荆关一只眼”的假石涛,以及吴湖帆请叶恭绰题签的“天下第一梁风子”的伪作《睡猿图》在内),要不是张氏亲口供认,又有谁来揭示这个谜底呢?开一个玩笑,如果把张氏在这句话中的“吾之精鉴”改成“吾之造假”,足使振玉推诚,宾虹却步,仪周歛手,湖帆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倒也说得过去。
五百年独一无二的出版物
屈指算来,大千先生离别人间已有28年了,他离别大陆如果从1949年12月6日离渝赴台算起,已有62年。他的前半生是在大陆度过的,而后半生则是浪迹飘泊海外30年,直到晚年才叶落归根,回到祖国的宝岛台湾。他一生辛勤笔耕,创作了数以万计(有人统计在三万幅以上)的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国艺术宝库,也在国际艺坛上赢得了一席地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研究张大千的同行还没有名正言顺地坐到一起交谈研讨,这是令人遗憾的。随着两岸文化交流逐步开放,我深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我是80年代初从张氏老友和大风堂门人口中才获知张大千其人其艺及其传奇经历的,由此开始着手搜集张氏素材。皇天不负苦心人,二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的报刊介绍文章找到了不少,但出版物却凤毛麟角,遍寻难见。随着港台出版物的逐步解禁,我在张氏老友叶浅予、黄苗子的帮助下,购藏到一些港台出版的张大千画集、诗文集、纪念集及有关记述张氏生平事迹的出版物,诸如《张大千的世界》、《摩耶精舍梅丘梦》、《形象之外》、《环荜菴琐记》(原著买不到,是友人寄赠的复印本)等。二十多年来,连同购藏的大陆版张氏图书,书架上也放上了几十种,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张大千出版物大概可以尽收架上了。可是,当我翻阅台湾吴女士寄来的文献图目时,不禁哑然失笑。文献图目所列海内外出版物竟达482种之多,其中张大千或以张善子、张大千署名编印的出版物也逾百种。就是说,我所藏张氏出版物,不及文献图目的一个零头,不少图书我见都未见过。例如1921年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的《魏张黑女志铭集联拓本》(张大千撰句),这本拓本曾听大风堂早期门人刘力上说起过。说大千先生随曾太老师学魏碑,是由此入门的。但拓本至今未见。
张大千出生在四川内江,但从师学艺乃至成名成家却是在上海。他在上海继继续续生活了十多年,几乎占据了他在大陆的一半岁月。上海是20世纪崛起的国际大都会之一,随着商品经济繁荣,新闻报刊、文艺小说、金石书画等出版物风起云涌、浩浩荡荡汇入了精神产品的大潮。书画金石,作为高档精神产品之一,也得了经济起飞之助,较之内地大城市捷足先登,登入了艺术市场。“海派”文人,“海派”书画家亦应运而生,大批文人墨客纷纷集居上海,一展身手。张大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入了新旧交错、中西混杂的十里洋场。曾熙、李瑞清两位前清名师,把他引进了古色古香传统书画的文人雅集,但五光十色的市场经济,又潜移默化地熏陶着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职业画家。
不知是否有高人指点,抑或是无师自通,几乎在投师学艺的同时,他就把目光投向了出版物。从“文献图目”中可以看到,早在20年代,他就在上海好几家书局持续出版由他或与二哥张善子合作署名编印的图册,其中除了前面提到十来本大风堂石涛藏画集外,还有一本打造自己的《己巳自画像小像题咏册》(由黄宾虹作序、杨度、陈散原、方地山等海内数十位名流名家的题咏)。果然,在一鼓作气出版物的鼓吹下,在群星(诸多名家)捧月(己巳年三十自画像)下,张大千大步走入而立之年,他的知名度也由此打造出来。出版物的功效实在不小!这许是张氏关注编印出版物的初衷和动力。
三四十年代,张氏声誉日隆,南征北战,京津画展告捷,艺术市场不断拓宽,在画商的策划下,名目繁多的带专题性的画展、画册也就不断出版。诸如《黄山画景》、《华山画景》、《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合作山君真相集》、《西康游履》、《旅印近作展》等,至于旅居海外后,进军巴黎花都,闯荡欧美艺坛,在世界各地办画展出画集,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张大千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一生充满了传奇故事。他那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自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绝妙写作素材,他的身边总是聚集一大批文友、诗友和报刊新闻记者,这些文人墨客每有所见闻,必然舞文弄墨写下诗文,见诸报刊。这也为日后众多掌故、趣闻、传奇、传记之类的出版物的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据文献图目统计,张氏生前身后的出版物截止2009年,已近五百种。张大千成了画商、出版商、文人墨客、青年学子眼中的一座金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他的书画在艺术市场上不断创高,散在民间的藏品不断浮出市面,又会演绎出不少传奇故事,张大千拍卖画集更添新章。张氏出版物成了近现代艺术家出版物中的最亮丽风景线。徐悲鸿说,张大千的绘画是五百年来第一人;张大千说,他的鉴定水平,五百年来没有第二人。我看是,张大千的出版物,倒名副其实是五百年来(不,应该说千古以来)的独一无二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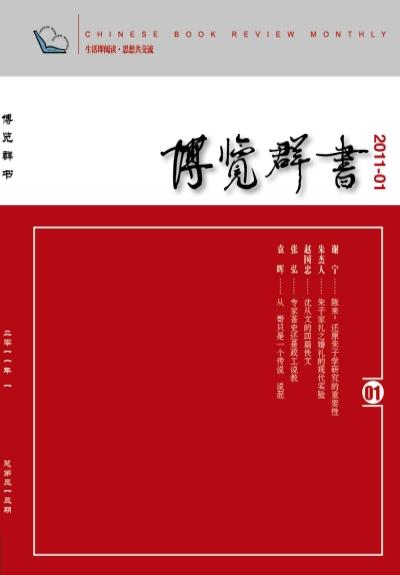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