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
长期从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王琛,作为北京民办博物馆行业的亲历者、见证人,因工作便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她创作完成的《乘物游心:北京民办博物馆纪实》是对“博物馆之城”这一文化形象的文学建构。
这种文学建构是如何实现的呢? 依笔者浅见,其具备三个鲜明的特点:用形象说话,“我”的主体性凸显,细节出彩。
报告文学的第一性是“文学”,这其中必然涉及素材的取舍、详略和重新组织,也就是“文学性”的体现。报告文学本质上是作家对事物的看法的呈现,或者说它必然包含了作家对事物的看法。作为描写对象的民办博物馆人和他们创办经管的博物馆(及藏品展品)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形象”;作家如何利用这些形象来说话,来表达她对民办博物馆事业的看法,就是一个文学命题。
本书中的形象,场景如画,人物鲜活。这是作家对“博物馆之城”所作的文学贡献之一,让“博物馆之城”中的人、馆、物,成为读者接受和理解民办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发言人”。笔者注意到,本书中对每一个博物馆的介绍都会落实至少一个具体的场景,人物在场景中行动,在情节中展示自己。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自带人设,对他的描写很难出新。作家设置了一个巧妙的情节,以“我”看走眼为引子,带出那句“马先生问你是不是特别有钱”,小小的反讽中折射出马未都的专业、幽默、亲和、委婉。这个情节设置可谓另辟蹊径,一句通幽。在工地上“猛然踢到一块石头”的路东之,那副神魂颠倒、仿佛命中注定要从事古陶收藏的人物性格呼之欲出。一些显然很真实的场景和情节,经过被采访人的回忆、讲述和作家的处理,呈现为文学的样貌。这些文学场景中的人物,不仅鲜活,而且更显真实,更有感召力。
作家通过栩栩如生的“金乌瓦当”,注解了什么叫“道在瓦砾”。科举匾额博物馆中小孩子们参加“开笔礼”的场面描写,为这家博物馆的办馆理念做了情节化注脚。对东旭民族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塑造从他如何得到一把榆木椅子开始,那一段情节叙事跌宕,波澜不断,单拿出来都可以成为一篇精彩的小小说。
书中“我”充沛的情感亦为本书营造了一个理想的叙述氛围。一方面,“我”的主体性感受增强了结构的整一性,理顺了叙事的逻辑脉络;另一方面,“我”的在场保证了叙述的情感穿透力,直抵人心。
作家对民办博物馆事业的一腔热情,对博物家们命运的关注,对馆藏万物的爱惜之心,拳拳殷切,构成本书一条强大的结构纽带,保证了作品的整一性。同时因“我”的始终在场,营造了浓厚的情感氛围。在一条“我”高度存在的情感线上,19家民办博物馆的发展史及31位民办博物馆人的性格形象被有效统摄起来,百川归一,汇入了“博物馆之城”这条汤汤大河。
在叙述观复博物馆的段落,作家形容自己打算收藏古瓷时“像一只蝴蝶飞进了花圃,被每一束花所吸引,流连忘返,沉迷而狂热”,这只“蝴蝶”在反衬收藏家李瑄(以及她背后的马未都)专业高度的同时,多少也暗示了以李、马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对民办博物馆事业的“沉迷”和“狂热”。借助“我”的穿针引线,一个巧妙的复合型转喻就此诞生。书中全程在场的“我”的情感、“我”的叙述,自然是可靠的、有感染力的。在这样的平视的语态中,读者从有“我”之境,抵达了博物馆人的内心——一片澄澈的“无我之境”。
本书给人的突出印象之一就是作家对细节的把握和强调。一些细节呈现,不仅具备塑造人物、烘托氛围的效果,而且符合、强化了民办博物馆这个情怀浓厚的文化事业的行业特质,从而令阅读进入某种不经提醒就难以察觉的“舒适区”。
比如“我”“再一次来到中国紫檀博物馆”的那个“银杏叶飘飞的日子”;写为办博物馆而省吃俭用的雒文有穿着“已经破烂的露出经纬线的灰色涤卡中山装,灰头土脸地蹲在角落里……”;“我”见到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后继人才吴疆时,作家写道“阳光正好,微风不燥”;饿着肚子欣赏藏品的王东旭,在月娥眼里“小叔原本有些佝偻的腰背立刻挺直了,眼睛里闪过熠熠夺目的光”,堪称全书最耀眼的细节。正是这些出彩的细节,于不经意间提升了本书的文学气质。
作为对“博物馆之城”概念的文学建构,这种珍贵的文学实践同时也让王琛的写作视野实现了重大突破。这部值得进行文学讨论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扩充了王琛的创作版图,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对自身的文学建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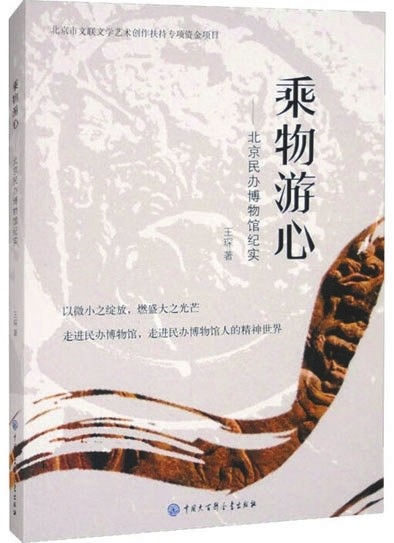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