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在中国艺术的形式构造中占据很高地位。
支离,重在非联系性,各各自在,不在整体中追求意义。而残缺,虽然也是不全,也具有非整体的特点,然其重点在构成的不完整上,习惯上我们认为一个物体该有的部分缺失了,如缺月挂疏桐,就是一种残缺,又如印章线条和边际的残损等。
老子说“大成若缺”——最高的圆满是残缺的,印家说“与其叠,毋宁缺”——与其重重叠叠,左旋右转,线条允宜,整饬充满,还不如断其线,蚀其面,如水冲岸,如虫食叶,缺处就是全处,断时即是连时。
中国人对残缺美感的斟酌,极易使人联想到西方美学中有关残缺美的欣赏,古希腊的断臂维纳斯就是残缺美的典型。有人认为,断臂的维纳斯比身体完整的维纳斯更美,人们在其断臂中,想到完整的手臂,产生一种视觉压强,由此激发更强烈的审美冲动。但如果这样理解中国审美观念中对残缺美的追求,就有些南辕北辙了。这不是形式美感的斟酌。我们常说动人春色不须多,花开十分不算好,需要减一点,损一点。这与重视残缺的思想倾向了无关系。
这种大成若缺的观念,体现了传统艺术哲学的重要倾向——对知识的超越,突破残缺与圆满的斟酌,从长短高下、圆满残缺的外在形式走向内在的生命体验,如九方皋相马,在骊黄牝牡之外,去追求它的真精神。重残缺,是为了破追求圆满的妄念,破秩序计较的迷思。
残缺的基本特征是不完满、不圆融、不全面、不规则。因此,我们说残缺,就意味着先行有一个完全的、完满的、完美的、完整的“原型”存在,就意味着对某种秩序的认同。我们从某种秩序出发,去绳之律之,从而分出高下、美丑、残缺和圆满的种种斟酌,是分别的见解。如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二章)——天下人都知道美的东西是美的时候,就显示出丑来了,美丑是一种知识的见解,是某种秩序、标准的产物。残缺和圆满的思虑也是如此。
传统艺术哲学有“随处圆满,无少欠缺”的定则,核心意思就是超越残缺和圆满这样的妄念。这种观念认为,从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出发,就是俱足的、周备的,没有需要补充的东西,没有什么缺憾。意义不须由外灌注,动能不需填补。当下体验,就是意义的实现,它是天之足。自己是当下境界的唯一成就者。一句话,从真实体验出发的生命创造,并没有残缺。
老子正是用人们认识中的残缺这把利器,来破关于圆满的妄念,从而走出知识的阴影,畅怀自我生命。《老子》不长的篇幅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四十五章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多次谈到“盈”——充满、圆融的问题。大盈若冲,冲者,空也,最高的圆满,就是空无。没有圆满缺憾,就是对圆满缺憾本身的超越。在老子看来,世界并无残缺处,若你有残缺之念,那是你正在对着一本教给你圆满的大书,支配你生命的源头是外在的知识,还不在心源。
《老子》二十二章说“洼则盈”,意思是,低洼处,就是盈满处。《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是此意,即岸即谷,无岸无谷,以谷破岸的思维,以岸掩谷的憾意,不觉得自己在山谷中,不期望登上高岸处,故无洼无盈。中国艺术追求的“空谷之足音”,其实只在乎奏出自己的心音,不关高下,无问南北。“洼则盈”,就是“抱一以为天下式”的另一种表达。老子在本章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曲就是全,缺就是满,洼就是盈,凡此,都在破有为的分别见,而臻于“抱一”之境界。四十一章说“广德若不足”,也在申说此旨。八章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以“已”——停止残缺和圆满的分别之思,为持生之大方。十五章说:“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者旧也,旧的就是新的,无旧无新。
老子对残缺与圆满的深邃见解,给中国艺术创造以极大启发。黄庭坚谈到苏轼的笔情墨趣时说:“东坡居士游戏管城子、楮先生之间,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盖道人之所易,而画工之所难,如印印泥,霜枝风叶先成于胸次者欤?颦申奋迅,六反震动,草书三昧之苖裔者欤?金石之友,质已死而心在,斫泥郢人之鼻,运斤成风之手者欤?”东坡与山谷以萧散淡逸相激赏,其笔墨之道,一变前代之成法,无论是书法,还是水墨之戏,取意在荒古之间,趣味出形式之外,虽为形之缺、色之缺、法之缺,然以缺为逗引,超越完美、葱翠和饬然,得其性之全也。
中国艺术有一种破圆的意识。金农一段画梅破圈的论述,极有思理:“宋释氏泽禅师善画梅,尝云:用心四十年,才能作花圈少圆耳……予画梅率意为之,每当一圈一点处,深领此语之妙。”生命就是生成变坏的过程,残缺是存在的必然。
中国艺术家关注残缺,注满了对生命存在的哀思。元柯九思《有所思》诗云:“云帆何处是天涯,辽海茫茫不见家。况是园林春已暮,有谁明日主残花?”其《题赵千里春景为太朴先生》诗云:“朱楼不识有春寒,隔岸何人尽日看。为惜年光同逝水,肯教桃李等闲残!”一个“残”字,有不凡的精神气质。中国艺术自北宋以来,其实是忍将彩笔作残篇,宋词和元画的主体精神,就是这个“残”字——在生命的不圆满中说圆满。
清金农是残破断碎感的着力提倡者。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是金农的终生密友,时人有“髯金瘦厉”的说法。厉鹗曾见金农所藏唐代景龙观钟铭拓本,对其“墨本烂古色”很是神迷,说:“钟铭最后得,斑驳岂敢唾。”斑驳陆离的感觉征服了那个时代很多艺术家。金农曾赞一位好金石的朋友褚峻,说他“善椎拓,极搜残阙剥蚀之文”。金农好残破,好剥蚀,好断损。其《缺角砚铭》云:“头锐且秃,不修边幅,腹中有墨,君所独。”残破不已的缺角砚,成为他的至爱。他有图画梅花清供,题云:“一枝梅插缺唇瓶,冷香透骨风棱棱,此时宜对尖头僧。”厉鹗评金农云:“折脚铛边残叶冷,缺唇瓶里瘦梅孤。”瓶是缺的,梅是瘦的,孤芳自赏,孤独自怜。“缺唇瓶里瘦梅孤”,是金农艺术的象征。
对这种“以残缺来超越残缺”思想讨论最充分的领域是印学。
明代中期以来,文人之印兴起,重视境界创造,如丁敬诗所云:“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形式之外的妙韵,是印家追求的根本。其以自然天工之妙,来引动生命狂舞,抒发沉着痛快的生命格调。嗜印如命的周亮工在给友人札中说:“拾得古人碎铜散玉诸章,便淋漓痛快,叫号狂舞。古人岂有他异?直是从千百世动到今日耳。”印章激发了他高昂的生命意趣。清末卓越的印论家魏锡曾(?-1882)论奚冈(1746-1803,字铁生)印云:“冬花有殊致,鹤渚无喧流。萧淡任天真,静与心手谋。郑虔擅三绝,篆刻余技优。”碎铜散玉中,有萧散天真之韵,具特别风华。
明文彭、何震等创为文人印,以冷冻石等取代玉、象牙等材料,追求残破感,“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赵之谦语),从而产生特别的审美效果。 一如明末朱简(约1570-?)所说:“断圭残璧,自有可宝处。”印之高境,在自然天成,在非规则性,一有规则,就有工人痕迹。剥蚀和残缺,是对规则的规避。文彭由光滑的牙章,变而为石的创造,就有有意回避人工痕迹的因素。小篆圆润流转,有婉转妩媚之趣,但处理不好,也会流于光滑柔腻。清金一畴说:“近时伧父率为细密光长之白文,伪称文氏物。好古者多不识也,宝而藏之。三桥有知,能无齿冷。”残缺剥蚀,成了治圆滑之病的利器。明末以来很多印人为了追求残破之美,刻石章完毕,常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或以石章掷地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止,一时蔚成风气。
明末沈野认为“锈涩糜烂,大有古色”,他说:“‘清晓空斋坐,庭前修竹清。偶持一片石,闲刻古人名。蓄印仅数钮,论文尽两京。徒然留姓氏,何处问生平。’余之酷好印章有如此者。”在他看来,印章虽为小道,却蕴有锦绣文章。他论印强调打破完整,超越秩序,抛弃表面形式感的追求,摒弃目的性活动,以稚拙、浑一、朴素的面目呈现。所以残缺剥蚀是印之不可少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章以追求残缺剥蚀为标的。印坛做残、做缺之风盛行,所打旗号往往是复兴秦汉传统——秦汉印的烂铜味、剥蚀气,让印家着迷。然而有印人徒然迷恋残缺、剥蚀,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最终滑离印学正道。沈野对此深下针砭,他说:“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若必欲用意破损其笔画,残缺其四角,宛然土中之物,然后谓之汉,不独郑人之为袴者乎?”郑人之为袴(按,袴即裤),出自《韩非子·外储说》:“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毁新,令如故袴。”印重残破,然其命意在残破之外矣,一如老子“大成若缺”,在于对圆满与残缺的超越,而非以残缺为追求目标。
明屠隆(1544-1605)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今之锲家,以汉篆刀笔自负,将字画残缺,刻损边傍,谓有古意。不知顾氏《印薮》六帙,可谓遍括古章,内无十数伤损,即有伤痕,乃入土久远,水锈剥蚀,或贯泥沙,剔洗损伤,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法古篆法、刀法,而窃其伤损形似,可发大噱。若诸名家,自无此等。”程彦明云:“古刻妙者,剥落如断纹,纵横如蠧蚀,此皆自然,非由造作。强为古拙者,如稚子学老人语,失其謦欬之真矣。”这段话说得颇恳切,大成若缺,然成不在缺中,正得老子哲学之古意。
清赵之谦(1829-1884)以为,印之妙不在斑驳,而在浑厚。“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杜甫《对雪》),印要有内在的回旋。他的“何传洙印”边款云:“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
(本文摘自《一花一世界》,朱良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定价:12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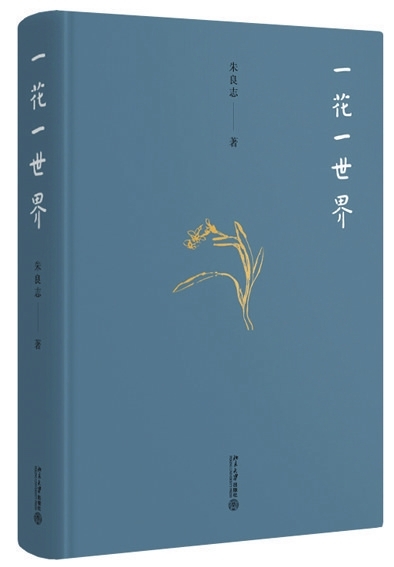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