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文学。自中国新文学发生之日起,鲁迅、周作人、叶圣陶、赵景深、茅盾等文学先驱将关注的焦点投诸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地上,产生了一批引起国人注意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著述。但与中国新文学史的撰写相比,儿童文学史犹如一个在母腹中的难产儿,迟迟未曾露面。上述现象不仅说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基础的贫瘠与薄弱,更折射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体系的不完整与不健全的状况。
直到1987年,蒋风编撰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才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空白。这部采取通史笔法的儿童文学史在时间轴上纵跨三十余年,再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通过对三个时间段(1917—1927、1927—1937、1937—1949)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勾勒,打通了各历史节点之间的界限,准确地把握了文学发展的走向与脉搏。此后,张香还、陈子君、张永健、王泉根、刘绪源等一大批学者也尝试撰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著,他们的加入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片原本贫瘠、荒芜的土地绽放出了绚烂的花朵。其中,不少史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演进采取宏观视角,一方面在时间上填充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生命样态,另一方面在空间上扩充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容量,在对儿童文学“边界”的推移与融合中,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深度。
一般而言,通史、编年史、断代史和专题史是文学史惯常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儿童文学界,通史是众多儿童文学史家选择的撰史方式,史家的通史观念在预设的理论构架中得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以通史为写作范式的儿童文学史,易拘于“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的思维惯性,史家的注意力聚焦在特定时期内具有“共名”色彩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上。反之,一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无名”状态的文学现象鲜有提及。基于此,史家容易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化、观念化的撰史模式,进而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及史料的甄选。
近年来,为弥补通史写作带来的缺失与遗憾,一些学者尝试采用编年史的撰史方式来梳理儿童文学史,以纵向的时间坐标轴为参照系,史料的延伸与拓展围绕着时间轴展开。王泉根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0—2016)》(2017,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即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著采用“大事纪”的撰史方式,着力于以文学编年的方法来推演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形态。
如果说通史是以史观和独特的理论框架见长,那么编年史则以史料的开掘、搜集、整理和研究为根本使命。是否发现新史料是判定一部编年史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假使在史料上没有新发现,那么重撰编年史的结果也只能是重复。吴翔宇、徐建豪的《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正是以重新开掘史料来丰富编年史著的范例,是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一大收获。该著从浩如烟海的民国期刊、报纸等初版本入手,在获取较为详尽、完备、充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后,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加工与编排,力求将史料历史化。这样一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原生形态借助史料的“点”和“线”形构出文学现场的“面”与“体”来,而中国儿童文学内在演进的轨迹也就显隐地呈现出来。由于贯彻了“前承后联”的逻辑,该著没有在时间的切割中阻断文学整体性的脉息,不同历史时期所涌现出的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团体、文学现象以及文学事件等也逐渐清晰起来。
整体来看,《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尝试在保证史料详实可信的前提下,避免对史料平面化、重复化的简单堆砌与罗列,摒弃对史料无秩序的随意铺排,让不同的史料在相互碰撞中激发化学反应。同时,该著力图超越通史写作中存在的思维缺陷,将“以论代史”转换为“论从史出”,在动态历史发展过程中,彰显出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之间前后互补、承前启后的逻辑关联,找寻出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部联系与发展动力,为我们提供着中国儿童文学鲜活的文学事件与文学现场。
在该著的序言中,蒋风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史是有等级、有差异的”,“想要规避这种情况的方法就是采用编年的方式来撰史”。这可谓切中肯綮。与通史体例的儿童文学史不同,编年体体例的儿童文学史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把特定时间段内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放置于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学或文化场域内进行观照,使各种文学元素在动态的文学区域网格内相互缠绕、联系,各要素彼此间形成某种既定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读者还原出一幅鲜活、生动的文学生活的日常图景。在整体的逻辑框架中,《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从儿童文学发生学史料、儿童文学创作史料、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料、儿童文学接受史料四个层面入手,形成比较严格、缜密的立体网络式的儿童文学编年史。在史料的选取方面兼收并蓄,将各个时间、年代进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做到宏观事件与微观事件相互补充,在见微知著中为我们对某些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重新解读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参照。
鲁迅曾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文集不可的。”《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8—1949)》是编年史书写的尝试之作,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与借鉴的儿童文学史写作模式与路径。当然,编年史自有其不可回避的缺憾,如整体性、系统性较为薄弱,无法窥见历史内在演进的规律。但如果能将编年史与通史对读,相信能够为学界留下更为多样且丰富的文学史书写的启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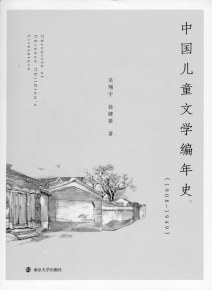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