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晚期以后,伴随着中原龙山文化群的出现,在“多元一体”的史前文化格局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距今4300年以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地体现在聚落间和聚落群之间。
宏大的历史发展与道路进程,需要有相应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洛阳盆地是极为重要的地区。洛阳盆地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原地区文化与文明演进格局、模式的缩影。
基于对洛阳盆地价值意义的判断,中、澳、美等国学者在20世纪末筹划了洛阳盆地的区域系统调查,并以不同的课题形式开展。与同时期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有所不同,调查的学术目标设定没有止步于聚落数量、时空变化,而更明显地侧重于通过聚落的历时与共时性调查,对地区复杂社会兴衰及其资源域的开发和控制,以及当地经济生业模式和环境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探析。这无疑增大了区域系统调查的难度。
经长达数年的田野复查和资料整理,调查团队的最终科研报告《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最终于近期出版,为学术界全面认识、检验调查成果,深化中原地区文化演进格局和文明起源模式研究,提供了关键而系统的资料。
对于如何刊布田野考古报告,学术界近年来热议不断,是对原始资料尽可能刊布,还是在研究之后筛选刊布,各有利弊。如何在整理、发布资料时做到平衡,对于整理人来说必然是非常困难的。从体例设定看,《报告》将原始调查信息与综合研究成果非常清晰地加以区分,分为资料篇和研究篇两部分。
从正式出版的《报告》来看,资料篇不但对调查中发现的每一处遗址进行了介绍,对同一遗址的不同时代遗存,还分别加以叙述,所采集的标本也都精心选择并绘图刊布。在分述之后,资料篇又以调查结果的形式,对分项叙述进行整合总结,对不同考古学文化以时代切片的方式,进行长时段的共时性分布空间化表达,并辅以地图形象表达。这已不限于简单的资料刊布,而是带有整理者认识的总结。这种资料的公布形式,不但尽可能地在资料客观公布与研究成果之间寻找到了最佳的平衡,也无疑大大细化了对不同遗址的认识。
报告中对不同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细化和年代序列相对缺乏遗存的刊布,较以往更为深入。《报告》对调查所发现的遗存,可以细化到“期”别,部分考古学文化(如二里头文化)甚至可区分不同期别的聚落分布。在不可能发掘每处遗址的现实条件制约下,《报告》的材料将是判断当地社会结构和聚落分布等学术问题相对最为精确的依据。比如,既往洛阳盆地缺少殷墟时期居址的信息,在《报告》中,虽然辨识出的殷墟时期遗址数量不多,遗存也不丰富,但新公布的遗址对理解洛阳五女冢晚商墓葬,洛阳盆地西部及盆地以北如灵宝、济源等地的晚商遗存性质,乃至晚商地方经略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报告》的研究篇,突破了既往调查乃至部分发掘工作的理念,尽可能地将不同学科的研究与考古区域聚落调查相联系。土壤微形态分析,在宏观考古调查之外,提供了微观角度的证明。基于浮选所做的植物考古研究,则增加了生业研究的实证力度。基于灰嘴遗址发掘的个案研究,对既往不太受关注的中原地区石器生产和白陶的生产提出了新的认识。
与《报告》的相关研究的理念、结论最具可比性的,无疑是《二里头(1999-2006)》田野发掘报告。两部报告的田野工作时间接近,工作人员亦有重合,所涉及的区域与问题更是有高度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工作理念是十分相近的——都是以田野工作为中心,以遗存系统整理与相对全面的公布为目标,集中不同学科优势,分析所处理对象的社会问题。但若对比具体结论,却又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差异。这些差异将会对中原地区社会格局与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起到调整作用。兹举一例说明。二里头遗址的系列样品测年确定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但区域系统调查所获样品的测年却显示“伊洛地区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不应晚于1890cal.BC……二里头文化年代的总跨度比以前估计的(1750-1530cal.BC)要长”。调查者与《报告》研究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近150年的时间差,他们的解释是“二里头类型陶器在该地区一些中小型聚落中的使用时间要长于这类陶器在二里头中心聚落的使用时间……二里头大型遗址在一期的突然出现,应该是人口迁徙的结果”。换言之,《报告》的逻辑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一期遗存应当是该期遗存的最晚阶段,迁徙到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人群在抵达二里头后,在50年左右的时间(以二里头遗址二期遗存测年结论计)内演变为二里头二期文化。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二里头一期在伊洛地区发展超过150年,是否还能细分?如不能细分,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一考古学文化在不同期别的演变节奏不同?伊洛地区和嵩山南北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是否可以同步发展变化?如果不能,该如何辨识?类似的许多学术问题,从《报告》公布的遗址信息和相关多学科个案研究结论,皆大有深意,是未来研究继续深入的重要起点。
当然,《报告》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其研究篇采用中英双语刊行,而发现篇则只有中文。这或许有设定的读者群体差异考量在内,但显然不利于国外学者从基础材料入手认识洛阳盆地。基础材料的熟悉程度差异,是中国与欧美学者对同一材料产生认识差异,甚至误解的根本原因。欧美学界也罕见对中国以陶器为中心的考古学材料进行非“科技考古”的研究。洛阳盆地区域系统调查是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集体项目,本是双方极好的沟通和推介机会,但《报告》不以英语介绍调查的基础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研究篇与资料篇的脱节,也难于利用资料检验研究成果,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同时,大部分研究个案都是以灰嘴遗址发掘为基础,但个案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如何,《报告》并未深入讨论。采集的动物遗存,《报告》也未反映相关情况。最后,《报告》的发现与研究结论未能进一步与洛阳盆地内、周边的核心性遗址的相关研究进行点、面对比,是比较遗憾的。
但无论如何,对于卷帙宏大的报告来说,上述一些问题近乎理想化,甚至是对一线工作者的苛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洛阳盆地东部区域系统调查是探索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宏观线索。《报告》对田野工作的课题设计、调查内容、报告编写和资料刊布形式,必然会引发学界的持续关注。期待在后续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中,不要放弃对发现线索的追寻,深入相关研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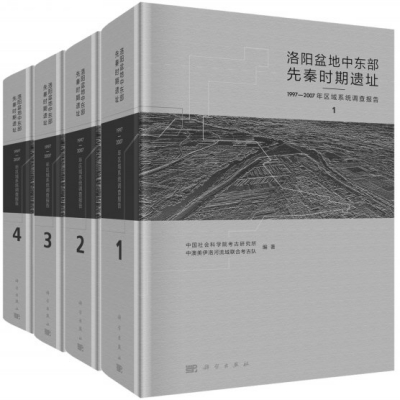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