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文学史专著中的经典,这不需我来重复。它的好处,也自有学术角度的公正评说。然而,好归好,这样一部四百来页的教材,并不适合每个人阅读。它作为教材的面面俱到,论述的不动声色,是一种业内人士方能细细品咂出滋味的博雅贯通。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写给大学文科师生们研读的,那么《中国文学1949-1989》这本小书,则是每个读者都可一览的通识之作。虽然看上去讲的是文学,然而这四十年的社会文化事件,因为历史的特殊性,又有哪一件和文学没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呢。《中国文学1949-1989》不仅仅是一部“极简版”的当代文学史,仿佛看过那本大书之后,这本小书便无甚精义了。这本小书有着完全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是给大家划知识点,而是用朴实的语言,用每个人都可以听懂的方式,把四十年围绕文学发生的史、事,讲透彻,讲清楚。作者自己说:“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有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说很多的话;有时,说得越多就越糊涂,还会把点滴的‘意思’稀释得不见踪影。”
之所以能讲清楚,可能跟它的前身是针对外国受众的讲稿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洪子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他需要面向许多对20世纪中国的面貌缺乏整体印象或知识积累的日本学生讲述当代文学,许多中国读者心领神会、感同身受的前理解,于他们不起作用。这本书努力做到简而明:简有时容易流于浅,那就成了儿童读物,有时容易流于晦,那就成了抽象总结。在这本书里,简明是由博返约的举重若轻。
作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巨大转变过程之中,“现代化”是物质和精神领域的总题目,文学也由此形成某种统一的特征,所以应该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现代化中的“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如何经过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的“改造”,成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学规范,则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问题。左翼文学在30年代已占居重要地位,在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区域,它演变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及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流通、阅读的规则等),在50年代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更凭借政治控制的力量,而成为中国大陆文学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到了80年代,这种一元的文学格局发生了变化,而展现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发展前景。
在作者这样的大局观视野下展开讲述,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辨。以往针对这段时间的文学历史,许多论述者要么全盘肯定,要么盲目否定,这些肯定和否定本身都不是历史的把握,而是个人价值观念的主观投射,是意识形态立场或个人审美阅读的观念表达并以论代史。很少有作者能贴着历史来讲述历史。贴着历史讲述,并非不知道什么是意识形态,也并非没有个人审美阅读,甚至他需要更深厚的审美阅读功力,才能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把历史的骨骼洗刷出来。赞美或批判或许是有压力的,但其得出赞美或批判本身,却是容易的。现在许多人都在为想尽办法找出新颖的赞美之词或竭尽全力发出晦藏支离的批评之词而努力,所以文学史著作越写越长越晦涩而且不尽如人意。这本小书,却以平淡的笔墨、零度写作的控制力,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冷静从容的抒写。
书的上编主要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左翼革命文学规范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作者努力追寻这故事里的种种情节产生的渊源与经历的变数。在这里文学思想甚至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因为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实紧迫问题,尤其是社会政治实践问题,所作出的回答。他有关文艺的论述,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政治含意,就是直接地为着某种政治目的。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讨论文艺问题要从分析“客观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他所列举的“现在的事实”中,包括当时的抗日战争、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文艺运动对战争和革命的配合。毛泽东是十分确定地从政治任务的要求上来看待文学的。这三十年,文学的就是政治的,政治的也是文学的。当作者把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政策这个核心理路抓住并梳理清楚后,那么随之而来的三十年的“规范与控制”,作家群体的嬗变、矛盾与冲突,主流作品的状况与总体风格,以及游离于这一主潮之外的非主流文学作品的面貌,也就势如破竹地获得了清晰的解释与呈现。许多文学史作者,要么不敢抓,要么抓不住。
书的下编揭示了这种支配地位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变化,以及中国作家“重建”多元的文学格局所作的艰苦努力。下编的切入点,又与上编有所不同,作者主要考察控制削弱之后,在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作家心理素质和文化性格的状态,以及这种性格、心理状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当中国当代作家开始获得比较“自由”的写作环境,来表达他们自身、他们对世界的体验时,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的潜在特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但他们这方面的弱点,也得到彰显。作者认为,这种情况,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既让人欣喜又叫人忧虑的现状和前景。有些人以为,这一时期的“自由”创作是摆脱了历史束缚的新篇章,急着与过去划清界限,但作者冷静地诊断出了这一释放背后历史无形的影响。因为,人本身越是抗拒,越是追求释放,就越是受到促使他追求释放的那一对境的反作用力,抗拒本身就是被对境赋予的形状。在这一点上,作者比那些吹嘘当代文学高度的人,更为清醒。
陈平原认为这本小书做到了禅宗所说的“寸铁杀人”,就是欣赏作者的“单刀直入”。观点的“棱角”,是作者真诚、认真、朴实的体现。洪子诚在贴着当代历史进行零度抒写的时候,真正做到了点到即止。许多人都仿佛懂得“即止”,但他们点不到,仿佛驾驶着概念的碰碰车在词语的游乐场碰来碰去,碰完一圈,文章结束,感觉什么都说了,就是抓不住痛点。点到,实在不易。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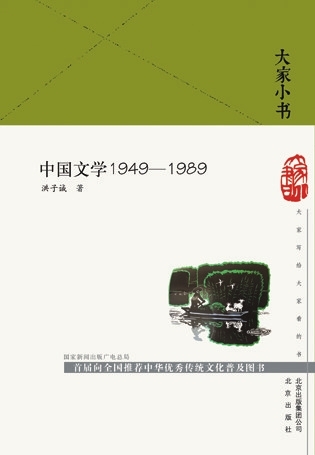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