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我与漠生是儿时的同学,几乎有过相同的童年和少年,走过相同的路,在北方同样生活过二十多年,也同样有过对家乡的思念。我与漠生不同的是,漠生走的是一条直线,从蜀中到北京,在那里定居了,他乡成了故乡。而我划了一个圈,回到出发的地方蜀中,但不是句号,而是没有封闭的圆,剩下那一“点”划在了未闭合圈圈的下面,成了一个问号。
在外的游子为什么总会有对故土的思念?每个年少的人都充满了野心,都像小鸟一样,羽翼未丰就扑腾着翅膀,期待一飞冲天。有一天真的飞走,但在外受伤了、疲倦了、飞不动了,首先想到的却是故乡,功成名就时想到的仍然是故乡。
思念是一种病,想见却不能见,每当想起的时候,总会泪眼婆娑,“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是无奈,“乡音无改鬓毛衰”是伤感,“抱膝灯前影伴身”是哀怨,“明月何时照我还”是期盼,“月是故乡明”是错觉。如今的地球村,所有空间上的阻隔已经消失,直到荡然无存。
但留在心底的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莫言始终忘不了红高粱,漠生一直惦记竹林湾。漠生的思念在他的前一本散文集《炊烟升起》里是同样的浓烈。他的思念有一种能量,让人不禁眼眶湿润,让人感觉得到琼江的水是那琼浆,会把人醉得迷离朦胧。
故乡山水的养育,亲人的陪伴,实现了一个山里娃跳龙门的梦想。家乡人去北京,总会给漠生带点家乡的味道,逢年过节,不顾高昂的邮费都要寄上一些特产,他那抹不去的乡愁才得以抚慰。“而我,回报你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思念。日久岁深,我的思念也成了一条河,从遥远的北方一直向南逶迤着,从年过半百向前追溯着,有千万里千万年,每一处每一刻都是咸咸的,温温的。”
其实,漠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家乡人进京不论公干或私事,只要他知道了,再忙都会陪着喝茶、请吃饭,再晚都要见上一面。只要求他办事,再难都会想办法,而且争取办成。他把对故乡的思念变成了行动。
漠生笔下的家乡很美,他的远方也很美。四川的火锅不能替代北京的涮羊肉,峨眉山的日出不能替代八达岭长城的飞雪。同样,京都高大楼宇是宏伟的,而蜀中低矮的瓦房却是质朴的;飞车高速路会心旷神怡,而漫步乡间小道却别有情趣。他走过的地方,每一朵花儿都是鲜艳的。
他的思念是一道道留声机盘上的印迹,深深记录那个时代。在一个读书会上,一群孩子安静地默读着《又见炊烟》,他们特别羡慕那时代,真的好幸福,学生没有作业,在家里可以养宠物,放学路上可以下河摸鱼,晚上可以听音乐会、可以看电影。那时叔叔伯伯一大堆,村里人都是自己的亲戚,现在,住在隔壁的邻居都不认识。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的亲人都只会用微信交流。
一个时代一重天。
下辈人不理解上一辈的事,就像我们这一辈年轻时候不理解我们的父辈那样,他们为什么一辈子就两件事:生儿子,修房子。当我们明白他们的时候,父母已经老了,想尽点孝心时已经没有机会了。
孩子们对那个时代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大的鱼撒上盐和粉子储存到坛子里,以备客人来了做全大菜”,去馆子里吃鱼多方便;为什么要“清红苕”,上街买几斤多方便。有一天,我带孩子出去吃饭,让孩子随便点餐。孩子说,要点一个特别好的。我有些惊恐,心里希望千万别点四斤重的龙虾,我没带那么多钱。结果孩子点了烤红苕。过去,有人判断小姐和丫鬟的方法是端一只整鸡出来,首先择鸡爪的是小姐,而揪鸡大腿的是丫鬟。也许不一定全对,但物质丰腴的人是不会理解饥饿的。除非他曾经历过。
漠生很执着,非要找到他爷爷的墓地。找到了又怎样?爷爷的爸爸在哪里?爷爷的爷爷又在哪里?他们已经回归了泥土,就在大地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是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
漠生不是哲学家,他没有回答哲学问题,他表达的是记忆深处浓浓的情意。
记忆这东西很奇怪,对于情感,时间越长,情会越来越真切;而对于事和人,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模糊,甚至走样。漠生在写斑鸠的叫声时,用的是“叽叽喳喳”,斑鸠应是“咕咕”的叫。吐火表演他记叙的是“嘴里含着铝粉”,其实是嘴里含着煤油。但瑕不掩瑜,这些“跳针”一点都不影响情真意切对我的感动。
读漠生的散文是闲时的品一杯清茶,大餐后的啃一个苹果,清爽、随和。是在太阳坝下坐在小板凳上摆的龙门阵,温暖的、随意的,不生僻,不隐晦,直截了当,正如他的为人。他的散文看不出他在京城待了几十年的影子,找不到半点京片子的味道,只有充满泥土味的乡音、乡情。
人们永远回不到故乡,即使地理上的回归也不会有儿时的感觉;人们永远找不到过去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是母亲从外婆那里传承、加上自己理解的创造,是遗失的手艺。去年今日此门中,早已物是人非。
但是,有这记忆的故乡和味道,才会有千古文章。故愁是永不枯竭的江水,将会地老天荒。我期待他的“炊烟”第三部。(巴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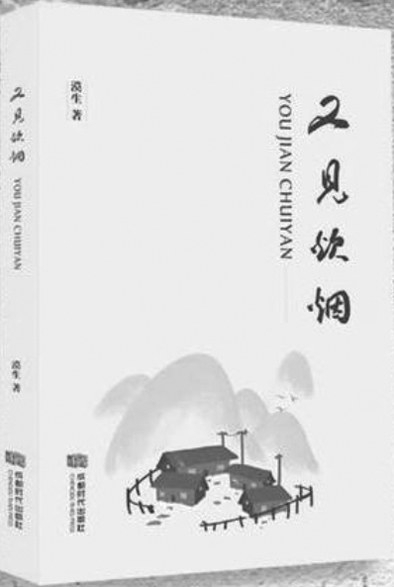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