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志祥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高校教材修订本不久前面世。恰好我们也刚刚出版了一部高校教材《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因为主题相近的关系,最近将祁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仔细拜读了一遍,感到很受教益。这本教材兼具文学理论专著的探索性和文艺学教科书的工具性,既包含作者对文学原理的独到见解,又全方位覆盖了传统文论的众多核心问题。教材以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范畴为枢纽,以儒、道、佛思想和宗法、训诂文化为文论的发生背景,贯穿起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精髓。与此同时,此书将西方文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进行比照,使得作品有了一种中西文论对话的意味。该书堪称重构中国民族文论话语体系的重磅成果,它成为“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高教教材并一版再版,是有道理的。
纵观整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者借用“文艺意为主”的“表现主义”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整体特点进行概括,并以“内重外轻”的文学观念作为线索,将传统文论各个层面与环节的思想贯通起来,完成了表现主义中国文论体系的民族化建构。全书按照阐述文学理论的自然逻辑要求,设计“文学观念论”“创作主体论”“创作发生论”“创作构思论”“创作方法论”“作品论”“风格论”“形式美论”“鉴赏论”“功用论”“价值论”和古代文论的“方法论”为基本框架,最后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收束全书。纵横交错,逻辑与历史相结合,涵盖了“文学”的本体论概念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的规律与特点。
比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方法论”一章中,以“活法”说、“定法”说、“用事”说、“赋比兴”说来表述创作方法。“活法”作为创作的总体方法论,它以“灵活”“活脱”“不主故常”的姿态存在于各个创作环节中。无论是起始阶段的“当机煞活”,还是自然之瞬息万变所引发的“机缘”,或者是艺术表现时的“因情立格”。“活法”来源于通过状物叙事来表情达意的需要,是文学创新的不竭源泉。它以辞达意,不主故常,“不窘一律”,无一定成法可套用死守,所以叫“活法”。但它告诉作家“随物赋形”,“辞达而已”,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所以是“文之大法”。“活法”不是“定法”又并不排斥“定法”,而是主张“因宜适变”地运用它,为表情达意服务,所以“无法”而又“有法”。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历史的维度与文化透视的视角为“活法”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详实的剖析。特别是从佛家“圆智”“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以及破除“法执”“我执”的角度来理解“活法”。如“圆智”强调思维方法的“圆转流动”;“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从“色法”方面探讨“随物应机”;破除“法执”和“我执”,旨在反对用僵死的方法对待创作,要求破除执念,“随遇皆道,触处可悟”。这些阐述为理解“活法”提供了参照,增加了文论著作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厚度。
该书的“作品论”论述也颇具特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论”涉及“文气”“文体”“文质”“言意”“形神”“意境”“情景”“真幻”“通变”九个范畴和章节。这些范畴其实是中国文艺最基本的问题,甚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言意”说是中国文论特有的形式与内容关系论。皎然从读者的角度探讨了“言”与“意”的关系,他提出“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旨在引导读者“披文入情”“得意忘言”。司空图从创作者角度提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告诫作家必须以“意”为目的,调动全部手段来突出“意”,而不是突出表达“意”的“言”。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深入探讨了“诗之言”与“诗之意”的内在规定。“别材”不同于事实堆砌、词句雕琢,“别趣”不同于理论说教、逻辑推理,故而“不落言筌者”为上。从以上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对“言意”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意”在文学作品内容中的主导地位。作者继而通过儒、道、佛、玄中的思想为“言意”提供文化阐释。儒家认为“言”是“达意”的手段,主张“不以辞害志”,突出“志”的主导地位。道家把“言意”安排在“道、意、言”的序列中,认为“意”是“物之精”,而“言”只是“物之粗”。玄学大师王弼指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所表达的“意象”是主体。佛家认为“言语断道”,主张“不立文字”,“心心相传”,更重视“自家心性”的觉悟,同时也对言语文字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告诫“语言能持义”,“若无此言,则义不可得”。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论中的“言意”说一方面视“言”为表达“意”的手段,强调“意”才是文学作品所要传达的重心,另一方面兼顾文字技巧,要求在充分掌握文字艺术的基础上为表情达意服务。
如何看待“情景”说?作者将它定位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境形态,颇有见识。中国古代诗歌以用物抒情为主。咏物不只是单纯的写景,而是为了借景传情。于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意象”“意境”在诗歌中的表现形态就凝聚、体现为“情景”。中国古代文学的“意境”论主张意为主境象为辅,意与境相生相发,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论亦主张景为媒情为胚,以景含情,情景交融。“情景”说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多在“意境”说中得到对应。如“意境”的重心在“意”不在“境”,“情景”说虽强调“情景合一”,但又指出:“诗以情为主,景为宾。”并且说,“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情景”说的代表人物当推明代的谢榛和清初的王夫之。谢榛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诗乃模写情景之具。”从创作发生论的角度指出:“夫情、景相触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指出:“景多则堆垛,情多则暗弱。”“大家无此失”,以其景中含情、情寓景中也。王夫之一方面指出:“神于诗者,妙合无垠”,“情景一合,自然妙语”,另一方面强调:“烟云泉石……寓意则灵”,“景非滞景,景总含情”。这种梳理和抉发,脉络清晰,主次分明,非长期濡染和深入研思,不能道也。
“真幻”说探讨了艺术真实论。“真幻”主要针对诗词歌赋在“言情”的作用下,其所建构的景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之景,而是主体通过想象虚构而形成的“景”。随着明清时期对“美”与“真”认识的不断深入,明代的谢榛、王廷相、陆时雍以及清代的叶燮、刘熙载等人都对“真幻”问题作了富有思辨深度的论述。如王廷相说:“夫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陆时雍说:“诗贵真,诗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叶燮提出:“想象以为事。”这些都说明诗的真实不是客观现实的真实,而是想象的真实,出自于想象的虚构。文学意象正是超越了现实的束缚才能以意象示人,意象的“透莹”“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品质铸造了它们处于真幻之间。艺术的真幻性不是无规律的,艺术中的真实或许比现实的真实更能体现出一种生活逻辑的真实。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那样,诗歌的真实能够体现更深远的意味。
无论是创作论中的“活法”论,还是作品论中的“言意”论、“情景”论、“真幻”说,它们都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历史流变、逻辑义理及其文化成因的深入探索,这种探索别开生面、别具卓识,同时又以其稳妥可靠,便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具有可操作的工具性,被评定为“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高校文科教材。全书在原来祁志祥教授独撰的基础上,会同全国各高校的年轻学者增补了第十三章,使整体结构更趋合理。相信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工作者开卷有益,会如我们一样收获匪浅。(黄意明 刘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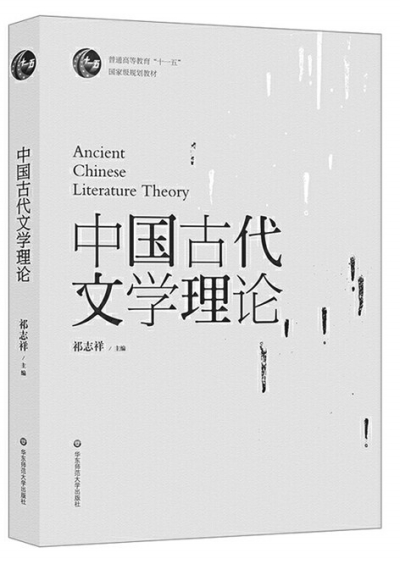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