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中午一点突然接到一黎的电话,他哽咽着告诉我,他的父亲身体情况非常不好,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我的头嗡地一下,本来一直为武汉疫情牵扯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眼泪涌出,一时竟不知对一黎说什么才是。几个小时之后噩耗传来,我的恩师黄鸿森先生仙逝。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我与黄先生相识始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入职。我高中没读完就遭遇了“文革”,下乡插队,进厂谋生,一晃近十年。直到1978 年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才感到有了可以依托的职业和真正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
那时,我虽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北师大夜大学读书达五年,可工作需求和自身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还是会搞得我忐忑不安,一种渴望知识、渴望提高素养的愿望常常在心中涌动。然而,我还是幸运的。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里有一大批知名学者,这使得请益机会多多,其中翻译家、辞书编纂学家黄鸿森先生的谆谆教诲让我时时受益,我从心底认定他是我最可尊敬的老师。
黄先生1921年生于浙江瑞安。幼年丧父,小学毕业后便不得不去做学徒。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日报》等多家报社特约记者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任《大众夜报》《自由论坛晚报》记者,并为《大公报》《经济周报》《财政评论》《观察》等报刊撰写通讯和有关经济问题的时评文章。
解放后黄先生从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分配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谁曾料到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竟遭冤狱五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在狱中他参与翻译了《苏联百科词典》《简明经济学辞典》,主持翻译了《政治辞典》。出狱后,进北京编译社任翻译,翻译校订了《世界通史》《近代史》《古巴地理》等书。以后又译校有《欧文选集》《圣西门学说释译》《自然政治论》《黑格尔评传》《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神话辞典》等多种学术译著和辞书。
1979 年 6 月黄先生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十多年里他像是根本没有休息,一桩接一桩地做了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工作。他参加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排头示范卷,接着又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环境科学》《矿冶》《力学》《交通》《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等学科卷的编辑工作,审读了其他 20 多个学科卷的部分稿件。他还参加制定《全书》编辑体例的工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所包含的智慧与辛劳可想而知。
第一版快要出齐时,他转事对第一版已出的一些学科卷的调研总结和我国第一部地方百科全书——《黑龙江百科全书》的编纂。之后,他参与指导了多类百科全书的编纂,其中有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地方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澳门百科全书》等,专业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全书》《中国湿地百科全书》《北京京剧百科全书》等,以及多部国外百科全书的翻译编撰。如他自己所说,“编百科全书在中国还是破题第一遭,在编书过程中不免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议,有所记,有所述”,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百科全书编纂求索》《回顾和前瞻——百科全书编纂思考》两部阐述百科全书编纂学理论和实践的著作。
黄先生是出版社的编审、中国辞书学会百科全书专业委员会顾问,还是多种辞书和报刊的特约审读员、顾问或专栏撰稿人,多次担任全国性报纸编校质量评审委员。他对这些特约工作,采取的不是你问我才顾的工作态度和方式,因此又有了《报海拾误录》《报刊纠错例说》《文章病案》等著作的问世。
黄先生因年事彻底不上班后仍然心系出版社的每一点进步,关注改革大潮中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他更加集中精力潜心研究百科全书和辞书编纂理论、报刊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规范。先生90高龄笔耕不辍,又写出《当代辞书过眼录》《百科全书编纂纵横》两部著作。正如辞书学会在唁电中所说,先生“为中国的辞书事业做出独特的贡献”。
出版界前辈徐式谷先生读过黄先生的文章后,用了 16 个字加以褒扬,称赞先生“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博学宏词,编辑楷模”。出版界领导也称先生“虽非大官却是大儒”。这些评语先生当之无愧。2008 年,黄先生荣获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中国辞书编辑的最高奖项,可谓实至名归,彪炳史册。
记得 1982 年我被调到《环境科学》卷编辑组做成书阶段的文字加工工作,得以与黄先生一起编书。此前我一直在《物理学》卷做部分分支学科的选条、组稿、初审的工作,还没有逐字逐句地推敲过稿子。到了环境组面对成堆的稿件,怎样删繁补缺,怎样润色文字,怎样统一术语数字,这一切对我来说无疑是个绝大的挑战。我改稿时常常顾此失彼,注意了病句错字又忽略了数字的使用,注意了层次结构又忘了解决条目间的矛盾。一天工作下来,成果不多、问题不少。可能黄先生看我虽有不足但还努力,就说:“你改的稿子我来看,我改好后你再看看,好不好?”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就这样我与黄先生“合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琢磨黄先生改过的稿件就像是在上编辑业务课。他好似不经意修改的一两句话,会使整篇稿子顺畅起来;对层次的调整和标题的斟酌又使条目结构更加严谨;病句错字更是统统逃不过黄先生的眼睛。不仅如此,有时他还会另附一段文字,说明修改的理由。他常对我说,编辑每改一个字都要经得起质询。他如炬的目光、缜密的思维、简约的文字,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黄先生常常谦逊地说自己是“科盲”,可他提出的学术问题之关键,见地之高明,不仅编辑们佩服,就连学科专家也连连称道。我向他讨教个中法门,他回答的原话我已记不得了,大概意思是说,好的文章内容一定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一旦发现文中叙述得因果不清,甚至逻辑混乱,那肯定是作者表达得不准确,甚或作者自己还没完全把握住知识的精髓,对这种稿子编辑就要注意了。有时我的稿子改得还说得过去,黄先生便会帮助我分析,为什么这次改得好,好在哪里。
在编辑彩图说明时,黄先生耐心地教我编写图题,教我在行文中把图题和图注区分开来,以备编辑彩图目录之需。他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走一步看两步的工作方法,也给了我很大教益。
《环境科学》卷发排后,我和黄先生就分开了。我去了地学部,黄先生仍在科技部。无论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会去向黄先生请教,直到先生90高龄离休在家,仍是如此。一个字的用法,一个句子的修改,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个标点的用法,一段汉语拼音的分合,等等,等等。先生真是有求必应,完全不会因为问题的幼稚可笑而推脱。有时不是我得到解答后举一反三,倒是黄先生发现我还有类似问题需要关注,便刻意提醒我加以注意。为能使我从理论的高度看待这些文字问题,他不断向我推荐好书,送我好书。我手头常翻的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林穗芳先生的《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以及《古籍索引概论》《新华拼写词典》《新华新词语词典》等,就是先生送给我的,当然送给我的还有先生自己的译著和著作。他读书有了心得,想到了某个常见语法错误产生的原因,就有新文章见诸报端,碰到我时都会说给我听,询问我的看法,鼓励我写文章。我经常推说工作太忙而迟迟不动笔,先生并不责怪,下次见面又会向我谈起其他题目。
黄先生是位恂恂儒者。他对学生如我的教诲从来是缓缓道来,没有一丝一毫的骄矜之气。这使我不愿对他人讲的话,甚至不愿意对家人讲的话,会向先生倾诉。记得三十七年前我的好朋友、科技部化学组的焦安朝突然不幸去世,当时我正在父母家休产假,听到噩耗,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先生的家与我父母家相距不远,我想都没想就跑到先生家,连哭带比画地向他述说我们的往事。先生只是默默地听着。为安抚我,他翻出解放前《大公报》等刊登着先生的文章剪报,讲起自己半生的坎坷经历。这让我的情绪渐渐平复,感到自己今后如能像先生那样奋进不息,取得那样的成绩该多好啊。
我的祖籍是浙江余姚,与先生是大同乡,但却从没在浙江生活过。闲暇时我爱听先生饶有兴致地讲述故乡瑞安的文人轶事、风俗典故,深深感到先生话里话外透着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一天先生交给我一篇署名阮立成的文章《楼适夷的春天》,说是回家乡拜访老友时老友托他转交给我的。细细看过知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楼适夷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坐牢时,阮立成曾是狱卒,亲眼目睹了父亲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父亲去世后他将见闻写成文章以示纪念。父亲被打成“叛徒”的冤案“文革”后早已得到组织的平反,但这篇文章是普通人对父亲的褒扬,意义自又不同。先生把文章递给我时,那慈祥的面容令我感动不已,心里不住地说谢谢,谢谢。
黄先生不是对我一人这样,他对社里其他同事也同样关爱,特别是对后辈小生更是如此。出版社为提高青年编辑的业务水平,经常组织业务培训和讲座。先生多次就百科全书选条的原则,怎样判断条目的可用性,怎样改稿,怎样确定条目的定义或定性叙述,以及虚词、引文的使用等工作中常见问题给我们讲课。他极其负责,不光赐教还要考试。看到年轻人有了进步,他从心底里高兴;对不负责任的改稿,他绝不通融,一次竟然气晕过去。
这样的老师你遇到过吗?有了这样的老师,你能不敬他、不爱他吗?现在先生离我而去,而限于疫情我却不能再送先生一程,唯一能为先生做的便是写下先生对我的恩情,以寄托我的哀思。
(本文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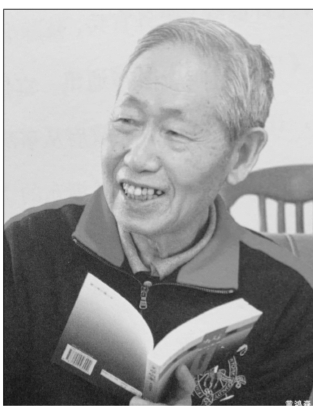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