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食单》按照古人饮食观念分为食、膳、馐、饮四个专题,共6辑,由66篇散文组成,以精细的白描笔法,深情地回溯那些或与我们渐行渐远的粗茶淡饭的乡村日子。本书与作者已出版的六本乡土散文一样,以八公分村为书写空间和精神指向,堪称作者童年的食欲传记,一位乡村母亲的炊事史,一个村庄的生活史。
“食色,性也。”这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欲望,食欲排首位,故有“民以食为天”之说。欲望是人的本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正常的食欲是健康的标志,过度的欲望则会导致人性的异化,饕餮即排在七宗罪之首。现代人日益膨胀的食欲和远离自然的人造食品正在败坏我们的口感,过度的开发等于放纵和变态。人们吃腻了山珍海味,吃遍了野菜药膳,不断变着法子刺激味蕾,虐待自己的味觉,结果越吃越乏味,吃出了食欲麻木症,甚至吃出了一场疫灾。
那个年代的食欲,却纯粹得令人感动。俗话说“饥不择食”,饥饿是食欲旺盛的前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相对贫乏,人们不求吃得好,只求吃得饱,每餐能剩下的除了光盘就是回味。本书以各色饮食所透出的食欲为基点,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记事线索,以村民的农耕劳作和日常生活为铺设背景,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乡村饮食风俗画。如作者第一次吃钵子饭的情境:母亲在生产队为修水库的民工做饭,他在门外出神地看着,不言不语。母亲突然端出一钵热饭,划出一半,夹些萝卜丝,往他张大的嘴里填塞,囫囵吞枣,连汤渣都不剩。这哪里是在吃饭,简直就是在加油站加油。那种吞咽的快感和母亲嘴角的浅浅一笑,至今仍是作者记忆中最美的风景。浅浅的渴望,浅浅的满足,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最经典的表情符号。
作者的故乡八公分村地处丘陵,是一个传统的南方农耕村落。这里旱土多于水田,红薯杂粮一年四季搭配着吃。红薯吃多了返酸水,一吃再吃,小孩子会本能地抵触。经历过“瓜菜代”的上辈人发明了“盖皮饭”,先吃饱红薯再吃两口米饭,将上窜的酸水压下去,胃就舒服了。主妇们则会做成红薯干、红薯丁、红薯粥、红薯汤、红薯酒、红薯糖、红薯粉皮、红薯丝子等等,变着花样把一年十几担红薯喂进一家人的胃里去。这种食欲纯朴得跟村民的眼神一样,即便心中有所隐瞒也会从眼神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那一刻,你无法不感动。
对于各种日常饮食,作者都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在案,意欲为乡村饮食立传。在八公分村,糍粑有多少种做法,每种做法又有多少种吃法,成了男人们猜不透的谜。什么菜可以晒干储藏,什么菜可以半干腌制,也似乎从来不是男人们操心的范畴。他们只知道,楼板上粗糙的瓦陶罐里装满了度饥的预案。就连再简单不过的米饭也能写上好几篇,平时的鼎罐饭,四月八的糯米饭,双抢季节的甑蒸饭等等,都有各自的讲究。甚至隔夜的馊饭都能做成干粮或茶点,有时一碗炒油盐饭又成了给孩子最好的奖赏。自家杀猪留下的猪头猪杂猪下水,样样都能制成待客的佳肴,来自田野的鱼虾小鲜就更是别提了。而逢到四时八节,尤其是新年大节,这里就成了乡村食品博览会的展区,连最不起眼的芋头婆、芋荷杆都腌制成了香辣可口的下酒菜。
再简单的食欲,也需要安抚。对付简单的食欲,往往并不简单。在八公分的主妇们看来,这一切都是饶有兴致的事情,这些就是生活的本身。在作者的记述中,每一个食欲的释放,都有母亲乐此不疲的身影。平时,男人们只管往田里土里、山上岭下耕耘劳作,就像在八公分的土地上绘画。女人们则把这些画小心拾掇起来,装裱一番,挂在家中有模有样。她们可能没工夫梳理自己的头发,可能没心思护理自己的脸蛋,却能凭着智慧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把一年四季的食物搭配得丰俭有致,把一家老小的食欲调理得有滋有味,把一个村庄的日子打理得安安稳稳。那些少油少盐却香甜可口的饭菜,那些偶尔解馋的花样零食,那些精巧别致的随机混搭,直让八公分人吃得依恋,吃出牵挂。即便是最难熬的日子,她们也会把一家人的食欲打发得服服帖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那些主妇们就会拿着瓜勺或团箕,走巷入户,满村去借粮。男人们却在瓜棚下优雅地抽烟吹牛,其实,他们最心知肚明,女人的伟大恰恰体现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一刻也离不开的地方。
在《一个村庄的食单》里,每一款饮食都是纯粹的食欲表达,每一段讲述都是鲜活的生活底色。本书记载的绝不仅仅是八公分村的饮食经历,而是一个时代的饮食记忆。作者流连于农耕岁月的同时,也欣然于时代的进步,以独特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点:返璞归真,或可拯救我们的食欲。(李向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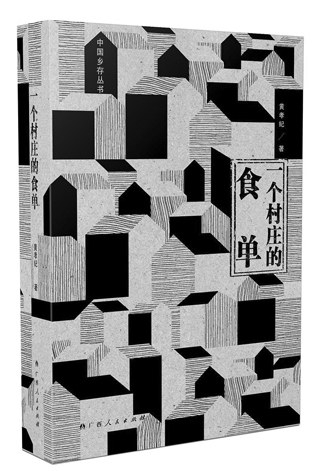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