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诗心是理解张炜儿童文学的关键词。张炜曾说过:“诗心和童心才是文学的核心”(《诗心和童心》)。“儿童文学的深意,可能即在于它更靠近诗意,更贴近生命的原色。童心无限深邃,这里就指生命深处的质地”(《张炜:“听大象旁边的人讲大象故事”》)。可以说,张炜所指的童心和诗心从真善美三个向度抵达了生命和文学的最本质核心。张炜的儿童文学一直试图营造这样具有道德的原初纯洁性、美学的审美愉悦性、哲学的智慧思辨性的童年诗学。最近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张炜新作《海边童话》把这种努力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童话在泛灵论思维基础上诗化世界。凛冬将至,田园歌手蝈蝈再也不能高歌。在严寒的煎熬中,炉火来了。炉火的快乐放歌穿越了寒冷、送来了温暖。蝈蝈被温暖的歌声陶醉,兴之所至,唱起了夏天,唱起了爱情。两个不同季节的朋友因温暖而相遇,因快乐而高歌,一夜无眠,只唱到晨光灿烂。在一间老旧的仓库里谱写着另一曲诗歌。辘轳和水车都是被时代所淘汰的农具,被丢弃在常年不见光明的黑屋里。他们无法抗拒自己被抛弃的命运,但他们可以互相地爱着。他们用爱、用回忆走过了漫漫长夜,并在互相慰藉中坦然地接受死亡。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末日降临,而是被请进了“民俗博物馆”从而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对世界诗意的表达以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写法,传达出的正是儿童文学的“深意”。张炜的童话能直面现实的不完美,并以童心和诗心构建的童年诗学穿透了现实的沉重,抵达了童年的理想国。
童话在故事性思维基础上诗化哲学。哲学命题在真纯的童心面前同样富有诗意。两个小鹌鹑对“可爱”及衍生问题“爱”的讨论形同一场哲学玄思。人人都说小鹌鹑可爱,但小鹌鹑对可爱充满了困惑。他们安静的样子和湛蓝的天空、金黄的树叶不一样,但都是可爱的。那么可爱到底是什么?这显然类似于苏格拉底和诡辩派学者希庇阿斯的辩论。苏格拉底追问的是美的本质,而希庇阿斯把美说成“美的小姐”“美的竖琴”等美的具体事物。张炜要挑战的是比苏格拉底的困惑还要大的哲学难题:如何对儿童讲述爱的表象和本质。根据儿童的认知心理,张炜充分运用儿童的故事性思维,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故事。小鹌鹑在讨论中逐步明晰可爱是一种表层的感官愉悦,再往前进一步才是爱。就像春天的槐林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叫喊,那阵阵沁人心脾的槐香则是爱的低语。童话继续层层深入探究爱的本质,思辨爱的真假、有限无限等命题,在充满童趣的对话中实现了对儿童的哲学启蒙。
童话在诗意栖居基础上呈现儿童个体生命的成长。儿童对世界的表述是万物有灵且美。因而成人常常把儿童浪漫化,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比如宋代“婴戏图”的盛行,而传统年画中更是少不了儿童形象。但儿童的审美符号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抽离了儿童现实生活的困苦和磨难。张炜的童年诗学从不逃离现实的土壤,并对成长的烦恼表现出深切关注。《第一次乘船》中黄狗阿贝向往大海,乘船成为他朝思梦想的心结,但他从来不被允许登船。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周密筹划实现第一次乘船的夙愿。《我变丑的日子》中小羊凡凡有着一身洁白俊美的卷毛。面对第一次理发,凡凡不怕疼和冷,担心“会变丑,那才是最可怕的”。《大熊的故事》中从小被圈在高高院墙里的小狗大壮和小猫小花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虽然外面有人人闻之变色的大熊,他们仍勇敢地选择独自出门。《迷路海水浴场》中金毛老憨更是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第一次:第一次从熟悉的省城来到陌生的海滨、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狗刨式游泳,又在游泳的狂欢中第一次迷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数不清的人生第一次。儿童面对这些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可能会因好奇而充满渴望和期盼,也有可能因害怕而感到痛苦和恐惧,还有可能因困惑而烦躁焦虑等等。儿童的这些心理波动在成人看来大多都微不足道,但对正当其时的孩子却性命攸关。作家最可贵的就是真诚地俯下身子,倾听儿童的心灵呼喊,感受儿童的情感起伏,并引领儿童走向生命的深处。
童话在现实关怀基础上的精神飞翔。张炜“足踏大地”的写作使童年诗学实现了现实的担当。从张炜目前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来看,童年诗学在《海边童话》中有最完整的呈现。童话中儿童对世界乐观诗意的理解达成了对现实的文化批判和对人们的精神救赎。但书中儿童的审美性并没有凌空蹈虚,在对儿童个体生命成长的敬畏中又超越了人生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炜的童年诗学所蕴含的文化的丰赡和思想的厚重绝非仅适用于儿童文学领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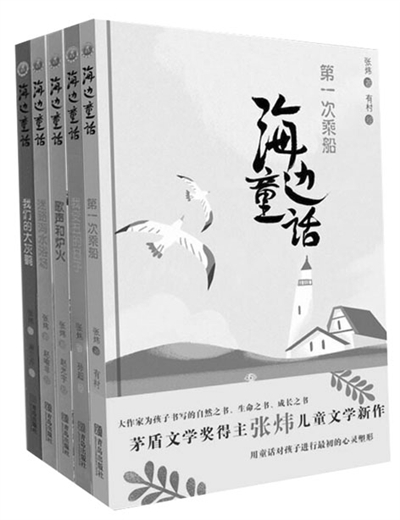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