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是写作的快手,几十天就能写完一部长篇。但是写《京西之南》,他足足用了两年。
“《京西之南》是我生命的证明、情感的书写,是自觉自为之举。”凸凹说,他出生在京西之南,这里是一块极为丰厚的土地。北京最重要的文物遗存,大部分都分布在这里。最著名的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西周燕都遗址,金皇陵遗址、还有云居寺、十字寺、贾岛墓、镇江营等。这里又是北京人、北京城的发祥地,具有鲜明的“源文化”的特征,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源头及核心部分。史地学家一直认为,北京文化的不断带特性,是靠京西之南不断带的文物遗存所证明的,所以它是北京天然的文化博物馆。
在这么一块丰饶的土地之上,历史自然多元,人性自然丰沛,有近乎传奇的人间故事,为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凸凹知道,生活的真实超出想象,艺术的描画难及生活的内部,也就是说,在这里,生活有理,观念失效。因此,“它逼着我,在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间找到‘我的’真实,所以,《京西之南》的创作,是大地道德的艺术呈现,是生活伦理的情感表达,是不得不的心灵登场,是感恩之下的泣血动作。写作的时候,我自然有一点个人的野心,即:描摹了京西之南,就是描摹了乡土中国”。
中华读书报:小说讲述古家人在京郊榆林水村的家族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改革开放年代,有简有繁,有虚有实,有俗有雅,如何既有史实依据,又写得血肉丰满,创作中您觉得有难度吗?
凸凹:家族史叙事一直是中国作家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频繁采用的文本形式,《金瓯缺》《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重要作品均是如此。这些小说将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变局,浓缩于某一家族、家庭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际遇中,以人物命运的转折起伏来折射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我的《京西之南》自然也承袭了这样的写作范式。小说由一则极具创世寓言意味的故事开启,讲述了古姓一家人扎根于京郊榆林水村后的家族史,以古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政权建立直至改革开放年代的经历为线索,以虚实结合的笔法,讲述了近百年来发生在京西之南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
家族史叙事的作品中,一般都会把某一人的命运作为家族兴衰的核心,这样的人物塑造成功了,整部作品的故事脉络和文学品质就具备了扎实的支撑。在《京西之南》中,承担着这一功能的人物显然就是古月。小说中,他的父亲被汉奸杀害,大哥因怪病早逝,弟弟、侄子被日寇的大炮炸得粉身碎骨,嫂子在自残肢体后独自栖身荒屋。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给这一人物的命运镀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感。然而,他不但没有被苦难命运压垮,反而越发呈现出乐观昂扬的人生姿态。家园被毁、亲人遇难后,他加入了抗日队伍,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却在家乡即将解放的时候,因为擅自行动违反军纪而被处分。他丝毫没有因为失去了看似光明的前途而懊丧,反而精神百倍地和妻子乔祺燕回到家乡,并一起建设家乡。
作品里关于抗日战争部分的叙述,我更多依赖于历史资料。而当故事进入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增加了更多的在场感和地域性。在和平年代,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得到了更多的展现。我也努力使语言更加鲜活饱满,情节更富有生活气息。这时出现于小说中的吴春山、白鼎轩等人物,有的生长于本乡本土,有的则是被时代和命运裹挟到这里。古月作为转业而来的当地基层干部,其身份其实兼具双重意味,既是“京西之南”发展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又是一名因为军旅生涯而有了某种外部性视角的观察者、评价者,“(他)已不再是警卫员出身的一介莽夫,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时势的造就、土地的涵养、人民的哺育,使他成了一名有思想、有韬略、有政策水平,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基层领导者,他的生命有了质的变化”。坦率地说,通过古月这个虚构人物,可以更加灵活、更加从容、更加艺术化地展示出我对历史过程的思考。
“文革”中,古月被遣送回榆林水村劳动改造,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退缩,反而觉得“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草药,既可以治病又可以打牙祭”。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他为了多为农民干实事儿,虽已退居二线,却心甘情愿听从老首长的召唤,来到邻省的田间传授农村工作经验。
中华读书报:古月这一人物有原型吗?
凸凹:对古月这一人物的设置,自然有原型的依据,但是他是杂糅的产物,为的是让他的身份、职业、经历和普通农民相比,多了“特殊性”的存在。他在部队上、在县一级领导岗位上的种种经历,更是远在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之外的,这正如他对老领导刘秉彦所说的,“从榆林水村到县城,有近二百里的路程,如果不是跟着您在队伍上干过,做梦也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个地界”。但是,恰恰是因为他的经历的复杂性和身份的多元性,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冲击的承受者,我正是通过呈现他面对苦难时的姿态,集中体现了“京西之南”的人们的秉性和气质。
除了用古月的命运来结构全篇,他的作用,还在于通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出场,引发出对新一轮社会形态的变迁的描述,并引出更多人物的出场。例如,在抗战时期,他参军入伍,也带出了八路军旅长刘秉彦和卫生队护士乔祺燕。前者是他毕生的导师,后者则成了他的妻子。而乔祺燕作为医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她在京西建设医院、服务农民的过程,其实也是1949年后地方建设的缩影。
当然,古月在叙事功能上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就漠视了古月这一人物自身的生命力。实际上,他的个性是极具层次感的。如果说整部作品中上百个正式出场人物的性格,组合起来可以从不同侧面呈现京西人特有的性格特质,那么,古月的性格,就是京西人个性的集中体现。在他身上,北方山区农民、八路军战士、农村基层干部等多重身份实现了有机融合。而且,他的生命里,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倔强果敢的生命力。就像我借白鼎轩的视角所看到的,“这个古月,虽然已经是县政府的领导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有农民的粗俗和朴素”。小说中,古月对于战争年代中的枪伤和在批斗中的摔伤,始终是在“快活地承受”。
很多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往往被作家赋予阐释自己的历史观的功能。但我在《京西之南》中,对古月赋予了更多的创作意图,集中到一点,是要通过古月这一个人物撬动各种各样的人物、情节,通过蛛网般的辐射效果,刻画出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并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整个京西的历史面貌、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令我兴奋的是,我的这个用心,被著名青年作家邱振刚一眼识破,他说:“这样的叙事结构,无疑为今后的家族史题材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
我承认,《京西之南》绝对是一次难度写作,既要把历史文献变成“我的经验”,既要把人物的情感变成“我的情感”,还要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浑然融合,自然要呕心沥血。但是,因为把古月当成了“我”,让我按照人物的逻辑活了一次,得到了许多新鲜的的生命体验,我比以前“壮大”了,所以很快乐。
中华读书报:小说讲述近百年来发生在房山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对您来说,既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吧?为写这部作品,您做了怎样的准备?
凸凹:我曾做过十年的文史工作,对地方文献比较熟悉,同时我又一直生活在土地上,满脑子的乡村物事,满心怀的乡土情感,用宁肯的话说,我是一个“在场的乡村叙述者”,有及物和准确的优势,能不能写好像不成问题。但是,能不能写得好,就是第一等的现实难题。干巴巴的史料可以让你准确,但是不一定让你鲜活;熟悉乡情,容易让思维固化,在沾沾自喜中失于流滑,这就是挑战。为了写得好,我是下了大功夫的。首先是在史料中“沉浸”,一改用学者的眼光看史料,而是把自己当作亲历者,一边阅读史料一边还原现场,设想在那样的场域下,我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和动作,通过细节的勾勒,让自己在历史中“走”一趟。其二是让自己已有的乡土经验“陌生化”,贴着人物的身份,呈现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下,人物自己的生命感受。即:让人物自己去生活,而不是我主观规定他怎么生活。也就是说,每写作一章,甚至每写作一个小结,下笔之前,我都要做一番“想象在想象中”的准备,长时间地絮絮叨叨、嘟嘟囔囔,引家人瞠目,以为我被什么附体,疯了。
其实真正的挑战,还在于自我的突围,有独辟蹊径的作为。因为我已经写了近十部长篇小说,自然有“自我覆盖”之虞。为了有文本上的突破,必须处处留心。《京西之南》从写作之初,我就要求自己,既要写得酣畅淋漓、如行云流水,又要凝重蕴藉、涵盖深厚。要革命热土、儿女情长和乡风民俗交相生发,做到好看、耐看。叙事要别开生面,让其对人有强烈的吸引,把革命叙事、红色经典、英模传的路数,突破发展到“大家都是人”的新格局,但又要避开阴柔琐细的偏向,使文本气象生机勃勃,大气磅礴,撼人魂魄。这一点,好像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因为评论家李林荣对我说,《京西之南》很激越,很温暖,让京西之南以至整个京西的人,加上外来的移民,都会因这部作品,而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和人文历史背景,倍增自豪和骄傲。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很多细节部分,比如何家栋被饿狗扑食,以及柳绵桃见到此景竟用手生生把眼球抠出来……触目惊心,但也感觉未免过于惨烈。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吗?
凸凹:生活的真实往往比艺术的真实还要来得强烈。原型中的何家栋,是一个村政权的头人,日本人偷袭时,他先得到暗报,得以脱身。但敌人聚拢了村人,架起了机枪,支起了一个偌大的油锅,扬言,如果他不前来受死,就要屠村。他闻讯之后,从三十里外毅然决然地返回,着白衫青裤布鞋,面带微笑,从容地走向油锅,把大义烹给敌人看。他的爱人就在人群中,不忍目睹这活生生的惨烈,生生把自己的眼睛抠瞎了。这悲壮的故事,就写在京西南的正史里,反拨着人们的想象。
这样的情状,在战争年代,时时发生,所以京西南英烈辈出,是一块被鲜血浇灌了的土地。曹火星为什么能在这里写下那首经典歌曲,就是心灵被这里的悲壮所打动。京西南之外的人,很可能难以置信,但这正是京西人性格的自然体现,是山水之赐,他们因为乐生,所以重气节,因为自重,所以有不可思议的迂执。
中华读书报:《京西之南》中的几个女人刻画得非常饱满细腻,爱情描写也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冯景旺对柳绵桃的追求、古年对柳绵桃的爱、古月和乔祺燕的感情,都令人唏嘘。您对京西人的爱情、尤其是不同时代京西人的爱情是怎么把握的?您所理解的京西,是怎样的京西?
凸凹:京西人多情,容易被美丽、美好的女人所打动。这是他们的生活土壤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京西冬寒夏热,容易凝聚和蒸腾感情。感情缱绻,是京西人的胎记。一旦爱上了,就死不撒嘴,为了捍卫爱情,便会有激烈的举动,爱恨情仇,都会走向极端。总的来说,京西人重情重义,忠贞刻骨,既自我珍惜,又不容外人欺。就感情热烈,爱憎分明,人性丰沛,恪守本分,追求大善。几个人的感情状况,正昭示京西人爱情的种种,有“标本”意义。
许多人读了《京西之南》之后,对古月,除了看重他的革命身份之外,他的情感身份,整体地被忽略了。这让我气郁。其实在他身上,我有大的感情寄寓,他既是革命者,又是标准的“情圣”。他决绝地去替老婆挨批斗,不怕伤筋骨。他说:“我对得起党,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对得起首长,也要对得起老婆。”他把保卫自己的女人也作为他革命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人”的亮相,写的时候,我感动不已,流泪不止。
中华读书报:此前,您有多部长篇小说,并于2017年出版过文集八卷本,这次创作,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突破?
凸凹:说在创作上的突破,是他人的事,自己说起来,就显得不妥。不过,突破的意图始终就贯穿在写作过程中,那就是要写复调小说。总的来说,我写小说,不限于小说式的叙述,还要有思想的观照,情感的关怀,立体地呈现和阐释大地道德和乡土哲学。这样一来,散文家可以看到散文,诗人可以看到诗,戏剧家可以看到戏剧,学者可以看到文化。这部小说,我最得意之处,是大部分读者,都感到,我的语言极其讲究,每一个细部都一丝不苟,堪可当作美文来读。
中华读书报:写作36年,您的小说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从《慢慢呻吟》《正经人家》等作品看,您的创作受西方文学影响颇深,您自己觉得呢?评论家李敬泽评价您既“有根”,又“洋气”,您认同吗?
凸凹:李敬泽先生的评价是贴心之论,我自然认同。实际上,我的创作一直是左手小说,右手散文。
在小说写作上,因为我始终扎根于基层,是乡村生活的在场者,不仅熟悉乡土,而且对土地的感情很深,是大地之子,所以,写的都是乡土叙事,大量的中短篇之外,长篇也有了十部之多。
多年前我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应该避免观念先行、概念图解,更要摒弃书斋里的主观想象和凭空臆造,要进入土地内部,对乡土世界进行本真的、全息式的描绘,揭示出乡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者说,要按照土地的“逻辑”写作,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主观评判,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因而努力挖掘、探求和呈现土地上的种种“理由”,给读者提供一个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直逼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黑夜”一般的文本,即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即:土地道德,或大地伦理。这种写作,其核心点有二:一是人道主义的写作立场,二是悲悯万物的人文情怀。
为了获取这样的眼界和功力,仅仅靠扎根子泥土中,是不够的,还要眼界向外,向世界的乡土经典致敬。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他途,只有潜心阅读。
纵观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为什么品格上整体趋于低,就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感性泛滥,理性缺失。而鲁迅乡土文学,为什么有那么丰沛的理性和那么宏富的内涵,是因为他着眼于“立人”,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上“审视”乡土,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所以阅读是乡土写作的基本功。通过阅读,可以使写作者获取到世界眼光、现代襟怀和城市经验的关怀和观照,一如蚂蚁爬行得再努力、掘进得再深入,总是向下的,头顶上的风光它是看不见的。如果插上一双小小的翅膀,飞上一个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纬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传统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立体思维和现代思维,如此一来,写作的“准确性”,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到达。所以,我要求自己,即便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要取法乎上,跳出小我,写出普世的意义。
我的写作生态,就是在土洋之间,享受着读书人和写作者双重的幸福。
中华读书报:从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您在小说和散文创作方面著作颇丰,能否谈谈您的创作追求?
凸凹:我的创作追求,无非有二:一是终生做大地道德的呈现者、阐释者,为乡土立传,为生民塑魂。近期的目标,是向福克纳、诺里斯、怀特致敬,立足京西之南——我的“约克纳帕塔法”,完成“京西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写作。目前已完成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脉》,正在写《京西逸民》,并架构我的“世系”,让世界读懂了京西,就是读懂了乡土中国。二是继续我的“西典新读”工程,写我的书话散文,并做到智性、感性和理性浑然交合,尺牍之间,有大气象,做大读者、大文章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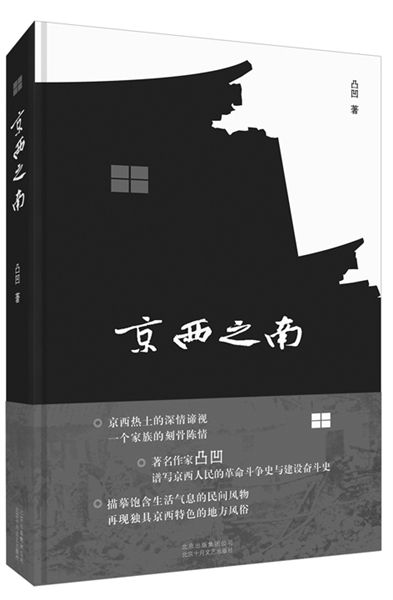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