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郞是日本电影史上三大导演之一,和沟口健二(1898—1956)及黑泽明(1910—1998)鼎足而三,也是世界电影史上风格鲜明、辨识度极高的大师级导演。中文世界将首次引进出版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收录了小津自1933年至1963年的共32册日记,正好是他六十年生命的后一半记录。
在看似淡淡的日常记录中,小津的生涯与作品重合,成为一幕独特的人生剧。在大历史的变迁下,一位真挚而有个性的艺术家,如何在艺术之路上越走越深,最终成就作为世界级电影艺术家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向所有读者揭示了其中秘密。
《小津安二郎全日记》即将出版之际,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举行小津作品研讨会。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格非在致辞时谈到,纵观小津一生的电影创作,其作品以一以贯之的美学趣味及风格、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和巨大的视觉魅力,即便普通影迷也不难辨认。但是如果我们想在总体上把握小津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以及世界图景的关系,如果我们试图捕捉小津在电影中必然有所反映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人生经验,其特殊的美学风格反而会成为一个理解的屏障。
《小津安二郎全日记》的出版为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更加深入地认识小津的电影提供了一个契机。1940—1950年代,日本有声电影迎来了它的高峰时期,小津安二郎作为这一时期日本电影的重要代表,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影迷,其电影艺术也对中国导演的电影实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导演贾樟柯接触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作品是在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他认为小津的电影世界有两方面非常吸引电影工作者,一是他所描述的时代。小津大量的电影一直在拍一个变革的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社会变革过程里人们所经历的情感上的困惑。二是他非常苛刻严谨的电影拍摄手法。
但是,当贾璋柯看完《小津安二郎全日记》,从他的美学世界进入了其私人的世俗世界、日常世界,开始思考小津的日常空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这是极其有趣的话题,也是值得我们对照阅读和观赏的新角度,就好像一体两面一样,电影作品呈现出来的小津和日记里所描写的小津之间有时候分裂,有时候一致,有很多电影创作上的蛛丝马迹,也可以透过日记了解到。
小津和战争的关系,一直是小津研究的一根硬骨,尤其在中国。那么,如何理解小津的战争态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关注的是小津日记和电影的空或白。
小津电影中,有大量空白大量悬置,比如《东京物语》,剧本提示有二儿子的“相片特写”,但电影中没有出现;电影结尾处,二儿媳的失声痛哭,原因也是空白。还比如,《晚春》《秋刀鱼之味》中,新郎都是空白。这些空白是什么?同时,小津中后期电影中,每部都有应该是角色互相对视说话但双方目光从不碰撞的场面,说话人或者朝着镜头,或者悬浮在空中,比如《独生子》《小早川家的秋天》等等。这种悬浮,就像小津电影中的风景,观看人是匿名的,常常既不是电影中的角色,也不是小津,也不是为观众准备的视角。
毛尖说,通过这些空白和悬置,小津成了影史上最语焉不详的一个导演,他用“无”总结了他的一生,消失的美学是不是一种最高级的呈现?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在小津看来,不出问题的家庭状态是,所有人都“匿名”,没有人需要扮演自己。用空白,小津彻底反击了蒙太奇语法,实现了影像的反独裁反侵略反扩大。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许多日本艺术家一样,小津安二郎也未能避免被“征召”入伍的命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以量注意到,关于战争时期的记述构成了小津独特的“战争叙事”。小津于1937年9月9日接到征集令,加入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直至1939年7月16日,小津的征集令才被解除,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小津度过了军人的生活。其本人的日记自接到征集令之前的8月6日戛然而止。然后是1939年,其日记完整地记录了直至其征集令被解除前的1939年6月5日的情况。此后一直到1951年的近12年间,其日记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小津日记中的“战争叙事”几乎仅保存在1939年的记述之中。从总体上来说,在这不到一年时间的“战争叙事”中,每一天的记述十分“冗长”,这是小津“战争叙事”的总体特征。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加以细分的话,小津“战争叙事”存在三个特点:一是非日常时期的日常生活,二是战争期间的战斗情景,三是作为“军人艺术家”的视角。
清华大学教授张芬注意到,小津的战时日记暴露的是小津对于“物”的迷恋。他对于“物”的感受异常敏锐:有的是审美对象、有的是食物、有些是词语、有的是印象深刻之物。总之,这些事物,在小津看来,都是可以被艺术转化的,他的电影,整体在哲学的意义上甚至具有一种把“物”当作本体的实在论色彩。
“对于小津来说,战争及身处战争之中的残酷和艰难,似乎并没有使他放弃自己顽固而保守,近乎早期浪漫主义者的‘艺术洁癖’。而几度试图尝试战争电影创作的未果,显示了他的这种‘洁癖’与电影这种大众媒体所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之间平衡的失败。”张芬说,战时小津仍执迷的这些物象在他的电影中反而变得更为“符号化”,而他连接着这些物象的故事,似乎也渐渐地不再是具体、单纯的剧情,而是作为一种形式要素,与画面、场景一起,成就了小津电影“意在言外”的稳定结构。因此,他的艺术也更加走向了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不厌其烦地“差异与重复”的境地。因此,战争经验对小津来说,更多地是艺术本身意义上的挑战。作为一个事实上对政治意识比较淡薄的人,他试图在这种历史的“例外”时刻用一种冷静、漠然而常态的眼光来构建他的“物”叙事。他在字面或形式上关心的,仍然是食物、风景、及其他可能被电影镜头吸纳的细节。以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越重要的事情说起来越困难”“越简单的事情越容易说”(《早安》,1959)的自我宽慰,小津用回环往复的家庭主题作为帷幕,模糊地遮掩了那些在日本战后精神史上更为重要而残酷的问题。所以,战争经验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能化解和处理的石头(这也以一种微妙的姿态切合了战后的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那种无法做简单化处理的纠结心态)。他的艺术之流,是在与他处理战争经验时那种犹疑、寻找制衡,企图创造,并最终绕过这枚“石头”的过程紧密贴合在一起。
虽然同处“东方”,都喜爱家庭叙事,但中日风格明显不同。中国的家庭剧具有强烈的道德或政治意味,直接呼应社会运动,“家国”的同构关系被高度彰显,家庭的私人性大大弱化衰减。中国式的特点是在家庭矛盾中寻找故事,铺陈冲突,阐述伦理,教化观众。而日本的情节剧较少用家庭叙事图解社会大势,更乐于白描普通人生活的细节,故事与画面中有大量“冗余”和“暧昧”。“小津自己说他要透过子女的成长窥探日本家族制度的瓦解过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表示,小津的作品数量很大,差别却很小,特别是他的晚期影片,全部情节都落脚于一个特定的结构单元,世界的尽头就近在家门之外。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小津的家庭剧是类型中的类型,它有一以贯之的主题,稳定不变的人物序列,自成格局的镜头调度,其细腻琐碎、冗长凝滞的庸常生活情景开始令人惊叹,继而让人会心气质单纯,景观限定。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舒晋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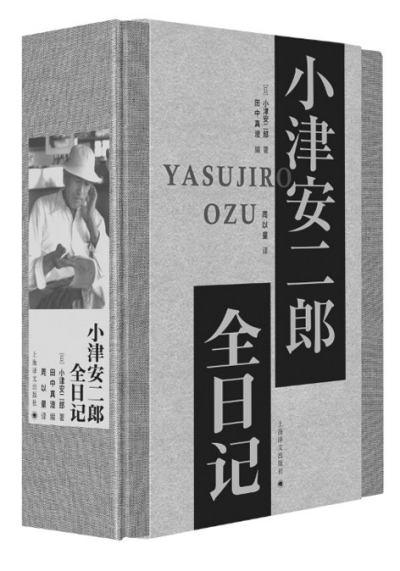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