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看王夫之的《宋论》,其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不乏精彩之见,但私心却并不很喜欢,以为其论“失”之于“刻”。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观感,作不得准。但史论却确实反映着读史者、治史者的心胸与见地。虞云国先生的新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即是他的史论,也即是他读史观世的深刻体悟。
本书是一系列“小文章”的集合,绝大部分是作者近年的新著,虽是因事命篇,主题却都集矢于南宋立国之初的“大问题”;又撷选了部分旧文,使所涉相关史事更加完整,全书也更加丰满立体。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本“小书”,却有作者的“大视野”“大观察”“大关怀”。
“绍兴体制”与“立国规模”
南宋虽然并非另建一个新朝代,但徽、钦二帝被俘,京城沦陷,宋高宗“自立”为帝,一番“纠结”之后将杭州定为临时都城(行在),也可以说是重新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便也可以有所谓“立国规模”。
从形势来说,宋高宗“立国”之初,面对的困难无疑比宋太祖更大,外有北方金人和刘齐的压迫,内有各地流寇四起,军事压力下还存在着财政危机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不稳定。与东晋南渡相比,宋高宗所依赖的,不是拥有雄厚实力的势家大族,而首先只能是起自行伍的武将。虽然宋朝家法“重文轻武”,但在战时状态下,提高武将之地位实是不得不然的无奈之举。但对宋高宗和文臣士大夫来说,“抑武”却是心底无时不在的念头。如何既削弱武将地位,保有中央集权,又可以解除金人的威胁,站稳脚跟,保住自己的小朝廷,便是宋高宗立国之初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在走马灯似地更换宰相之后,宋高宗最终确立的,用书中作者的话来说,即是融摄了绍兴十二年和议体制在内的“绍兴体制”。
所谓“绍兴体制”,简单地说,即是对外屈膝,与金人保持和平;对内强化君主及其代理人的专制乃至独裁。而这,即是南宋的“立国规模”。虞先生指出,它“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南宋时期“权相”接踵,对外又长期以求和为主,都由这一立国规模所“限定”和引发。这种集权体制,打破了恢复中原的可能性,彻底关闭了变革的大门,压抑了士大夫的刚直之气,导致了苟且萎靡的政风,乃至“中国转向内在”,也与这一体制息息相关。即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却无法扭转“立国规模”所带来的制度的惯性,也无解于南宋政治的死局。
宋高宗的这一选择,根本上出于“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即对于自身权力的渴望和对他人觊觎权力的防范。那么建立北宋王朝的宋太祖呢?虽然有柴世宗奠定了北方相对统一、武力比较强盛的基础,但在五代兵强马壮者即可轮番称帝,不足十数年即转瞬灭亡的混乱之下,宋太祖所面对的,就真的比宋高宗容易么?对比一下,宋太祖又是如何做的呢?《宋论》说:
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归结到最后,就是“惟其惧也”!但同样是惧,宋高宗念兹在兹的是收紧权力,而宋太祖所做的,却是宽和以待臣民,并逐渐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共识。北宋时期君主官僚政体构建起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形成比较完善的文官政治,便是宋太祖的“立国规模”所奠定的。可以说,“立国规模”是一个朝代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基础。作者抉发出“绍兴体制”这一南宋的“立国规模”,即给大家找出了解析南宋历史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当然,宋高宗的集权体制也不是凭空构建起来的,在北宋时,王安石变法即打破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共识,王安石与宋神宗形成专制权力;后王安石时代,沿着王安石的轨迹,由宫廷集权而专制而独裁,自有一条线索。本书集矢于南渡君臣,这一点暂且可以不论。
岳飞到底该不该杀?
自宋孝宗为岳飞平反之后,传统上,向来把岳飞视作忠臣,而以宋高宗不能任用岳飞北伐,痛失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的机会而惋惜。至20世纪面临西方尤其是日本侵略之后,岳飞的人格与功业,更是得到邓广铭等前辈史家的高度称颂。但在1920年代军阀割据的局面下,吕思勉、张荫麟等却也曾贬斥岳飞为“军阀”,以为岳飞的战功被夸大,又割据一方,其被杀是势所必至。近年来,也颇有论调指斥岳飞跋扈不臣,宋高宗及秦桧之杀岳飞,不仅是不得不杀,甚至是杀得好!对此,本书作者是颇不以为然的。
这里面恐怕牵涉两个层次:一是历史上的岳飞,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二是岳飞之被杀,是不是必需的?两个问题有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就前者来说,因为现有史料颇多局限,如《鄂国金佗粹编》为岳飞之孙岳珂所编,夸大战功,溢美先祖,自然不可尽信;反过来,出于“政治正确”迎合上意而大肆攻击岳飞,当然也无法全部视为事实。如何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实相,似乎仍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而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军阀”,不仅是岳飞“历史”形象的“呈现”,更是“观察者”历史观的折射。但无论哪一种评判或定位,可以确定的是,岳飞一没有威胁到宋高宗的皇位,二在晋升为枢密副使后没有威胁到朝廷的稳定。
那么,转换到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岳飞是不是必需要杀?或者换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即宋高宗与秦桧一定要置岳飞父子于死地,到底是出于“天下之公”,还是“一己之私”?虞先生在书中已指出,岳飞被杀之时,绍兴和议已经签署,大将的兵权也已顺利转移到三省、枢密院即朝廷之手,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与金议和,还是确保“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杀岳飞都不是必需之举。即使某种程度上,岳飞可能成为导致南宋朝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但以宋高宗和秦桧的政治手腕,已经轻松释去了岳飞的兵权,又何以必杀岳飞而后快?已无权而仍追究不止,可不杀而必杀,所反映的即是宋高宗的处理方式与出发点,不是为了人民安居和社稷稳定,而是要“借助恐怖性杀戮来震慑所有立朝的武将与文臣,为绍兴十二年体制正式确立的独裁模式大树特树君权的绝对权威”(第175页)。至此我们已可明了,独裁体制下“君为贵”,这才是岳飞之死的终极原因。那么,岳飞到底该不该杀,还需要争论吗?
史家的正大之论
作者提出“绍兴体制”对南宋的影响,解析岳飞之死的真相,不仅仅是对历史实相的一种追寻,同时也是作者历史观的反映。
弄清历史是什么,无疑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义。历史事实不清,一切议论即无从谈起。但这仍不过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已。我们研究历史,回望历史,虽不敢说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不敢奢望历史不要重演,但如虞先生在自序里面引用波里比阿的话:“学习历史是熟悉生活和政治的最好的途径;另一方面,了解别人不幸的遭遇是最好和唯一的办法使我们勇敢地接受命运的考验。”也就是说,历史并不是自外于我们当下的死去的过往,而与我们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的。
当前的很多历史学研究,深耕细作,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其深度是先辈大师也无法相比的。但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却也只局限于所研究的问题本身,忽视了对历史的宏观观察,无视历史研究的意义,而自诩为“无用之用”,实际上却是如清代所谓“饾饤小儒,破碎大道”。这样的研究,又如何与有宏观视野、有家国情怀的前辈相比,又哪称得上超越数十年前的学术水平呢?
近年来,史学界强调,不要以“后见之明”来论定“前代之史”,即不应将我们今天可见的既定的历史存在视作理所当然,而应重新回到历史场景,回到一切尚未尘埃落定之时,探讨历史何以至此。对此,作者并不反对,并且也有贯彻,比如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即充分体察了当时历史情境的复杂,以及各种因素交错之下削兵权的合理性。但他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读史或治史需求:
有必要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也是读史者或治史者以其“后见之明”对前代之史的一种复盘,以便揭示“前代之史”在推进过程中,包括在历史的分叉路口,哪些人为决策因素导致历史走向了岔路,从而深刻影响到其后历史的格局。(第132页)
当然,历史研究不能假设,比如我个人并不赞成假设岳飞没死的话,是否可以真的迎回徽钦二帝;而观察历史却可以不断追问:我们是否可以变得更合理、更好?而且,不要以“后见之明”去看历史,并不意味着治史者读史者应该主动放弃自我的立场。我们仍可以甚至应当有对历史的批判,这也是治史者良知的体现。比如作者对于秦桧专政时期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对高宗“中兴”语境塑造等的讨论,便不是大洋尽头隔岸观火的历史学家所谓回到“历史场景”、解构“话语建构”所能比拟的。还有我们私下谈起过美国学者对宋徽宗的重新勾勒,都以为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历史学家的责任,即不仅仅是告诉大家历史上发生了些什么,为什么发生了,同时,也有责任揭示历史上的善和恶,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看历史。在这方面,虞云国先生无疑是个中典范。从《南渡君臣》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正直,是我们应该了解和学习的史家的正大之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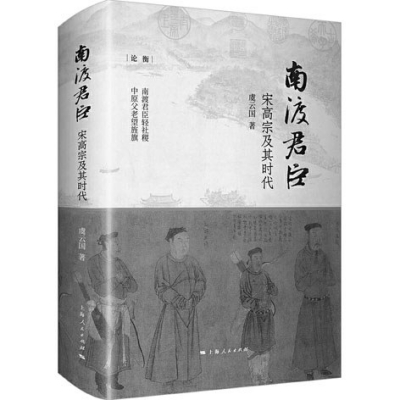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