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自我的提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若是此时看到一本名为《诗歌十八讲》的书,你大概会以为里面应该塞满有关意象、音韵、炼字等诗歌批评的论断,而在打开目录后,你会赫然发现自己错了。
这十八讲,并非一位知名大学的文学教授向一般读者普及一种文学类别的必备知识,而是集写作者、译者和读者这三重身份于一体的一对伉俪,在诗歌的世界进行漫长旅行后所写下的文学笔记。
诗的世界是如此广阔,从青蛙跃进的古池到星期四豪雨中的巴黎,从马祖匹祖高地到波罗的海,从爱尔兰的一把铁铲到克拉科夫的一份履历表……当你拥有足够的外语知识,当你能够搜索到相当的资料,你会选择了解哪片地域的诗歌,你会选择与哪位诗人交谈,这无疑会展现你对诗的好奇、对诗的趣味和对诗的困惑。
我们不妨顺着目录浏览一下作者陈黎、张芬龄在本书描述的一张旅行地图。从日韩诗歌出发,他们转向英国现代诗坛,在论述了几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后又来到了美国。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在那里久留,便迅速被拉美诗人吸引了。然后,他们又投向东欧和北欧的三位诺奖诗人,最后在短诗这一诗歌形式上结束,因其中对日本俳句的重点论述,让这次旅途似乎成为一个闭合的圆。
如此巨大的跨度令人生疑,这其中是否有某种关联性?是什么让这两位作者愿意翻译和理解这些地区和这些诗人的作品?无论他们有着何种初衷,我们在阅读时都应该主动寻找特定的主线将这些文章串联在一起。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萦绕以下问题:诗的资源来自何处?是人的情感和欲望吗?还是自身与他人、世界的关系?还是来自语言内部?诗人如何取舍和应对?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写诗?
为了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妨先从书中重点论述的拉美诗人身上探讨这些问题。在陈黎、张芬龄论述帕斯的《内在的树》一文中,他们有意识地将帕斯与巴列霍、聂鲁达做了对比:“在20世纪最重要的拉丁美洲诗人当中,帕斯是最抽象且富玄学意味的。帕斯不像巴列霍那样表达生活的诗的经验,他的诗往往是抽象、深沉的思维。”“帕斯相信诗是意念的泉源、空间的模式,他似乎不像聂鲁达那样相信诗就是一首‘歌’,是一种情感的直接表达。”
从这些描述中能看出,帕斯对诗的理解与常见的诗歌观念是不同的。在巴列霍和聂鲁达那里,诗的发源地是人的灵魂,内心的感受、身体的感觉是诗歌最核心的内容,所以无论是否真正“读懂”他们的诗作,我们几乎都能从那些诗句中感受到诗人在传达某些情绪和情感,比如“原谅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比如“如今我确已不再爱她。但也许我仍爱着她。爱是那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在这样的观念下,人的心灵更像一架乐器,不停变动的外部世界成为无形的演奏者,诗便是人的灵魂所发出的声响,无论它是一声呐喊——“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还是一阵叹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有那么多死者,有那么多被红阳割裂的堤防,有那么多碰撞船身的头颅,有那么多将吻围封住的手,以及那么多我想遗忘的事物。”
而帕斯的诗歌观念究竟是什么样的?陈黎、张芬龄对此总结道:“帕斯注重字与字、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投射’与‘回响’;对他而言,语言是一群流动且可以互换的象征组合而成,每一组成分子彼此牵连且互为暗示,每一个字都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帕斯想将社会现实和生活的意义从诗歌中驱逐,用语言这一形式来呈现人的感受与思想,而不是表达,更不是诠释。
面对纷争不断的政治环境,均担任过外交官的帕斯和聂鲁达,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态度,这种差异与他们的诗歌观念有莫大关联。聂鲁达投身其中,历经艰辛,而帕斯试图将诗与现实严格划清界限,这对他来说恰恰是对现实的某种抵抗,他用更纯粹的语言拒绝接受那已渗入到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控制。
聂鲁达式的诗歌观念在大众中依然盛行,但这对于当下想成为真正诗人的初学者来说却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障碍。或许是因为人的心灵本身所能发出的声音并不那么丰富,除非你也有一颗聂鲁达那般充盈着生命力的灵魂;帕斯的诗歌观念依然被具有良好知识背景的一部分诗人沿袭着。而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自身与他人、世界的关系之上。
无疑,这样的写作是异常开阔的。他人与世界,不再被简化为拨动心灵之弦的那只手,它本身就是丰富多变的,值得人们反复认真地观察,同时在这种互动中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融入其中,这带来的将不只是“歌声”和“语言结构”,而是无比多样的诗歌风貌。
在书中,陈黎、张芬龄同样重点论述了在英国现代诗歌中举足轻重的三位诗人:拉金、休斯和希尼。为了更快地切入,直接看一下他们在书中对三位诗人精到的评述:
拉金——“时间的流逝,年老,死亡,孤寂,每日生活的空洞,单调,都是文明中丧失个人特性的人类,被压抑而未能伸展的情感,这些都是他诗作中常见的主题。他略带嘲讽却又不失敦厚地记录这些人间的不快,以一种知性之外极动人的忧郁感性颂赞、美化这些原本被视为绝望、沮丧、负面的题材。”
休斯——“在过去,没有一位诗人能像休斯这样用客观且经济的手法把自然界之残酷或秩序内在化,并赋予新的诠释。休斯在写作时是如此具体且彻底地深入他所深思的动物,因此他的许多好诗都具有一种神奇咒语的效果,好像想从动物身上召回另一种可能的自我。”
希尼——“希尼则描绘出自然和人的互动关系,那是一种和土地密切相连的生活方式……他能够把眼睛捕捉到的场景描写得精确又细腻。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描写外在世界的同时,他还融入敏锐的心,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的意象,他赋予了外在事物内在的生命力。”
从这些点评中能看到,这三位诗人所重点关注的资源是完全不同的,那心灵之外的世界不再是被提炼为元素的金木水火土——“铁砧必定在中央的某个地方,独角兽般长着角,底盘四平八稳,动也不动地安放该处:一座祭坛,在那儿他将自己耗尽在形状与音乐中”,也不再只是被反复歌咏而干枯为标本的“雨”“玫瑰”“月亮”或“大海”——“我们再次减慢速度,而当拉紧的刹车急急刹住,一种掉落的感觉涌现,仿佛一阵箭自看不见处射来,在什么地方化作了雨”。
世界以前所未有更可触可感的方式与诗人发生着关联,这为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素材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都市生活与乡野风景并无阶级之分,天使与苍蝇同样可以扇动翅膀飞入诗中。
从这十八篇对众多诗人的译介文章中,我们能读到的不只是每位诗人的生平、写作特点,以及上面论述的不同诗歌观念,还有在彼此交织和呼应的章节中所隐藏的更多主题。因此,《诗歌十八讲》书中所包含的主题绝不仅是十八讲,它需要我们带着更多疑问去阅读,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发现更多的疑问,这也恰恰是阅读的乐趣之一。我猜想,这也是陈黎、张芬龄不断翻译和阅读其他诗人的重要动力之一。
保留疑惑,永远比抓住固定的答案更迷人。所以,一本讲述诗歌的好书,绝非是因它能够回答“诗歌究竟是什么”,而往往是它能让我们意识到“诗歌原来还能这样”,让我们了解到自己对诗歌的困惑原来如此之多,让我们愿意面对这些疑惑却依然想要抓紧它们,就像辛波斯卡在《有些人喜欢诗》中所的:
“然而诗究竟是怎么样的东西?/针对这个问题/人们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我不懂,不懂/又紧抓着它不放,/仿佛抓住了救命的栏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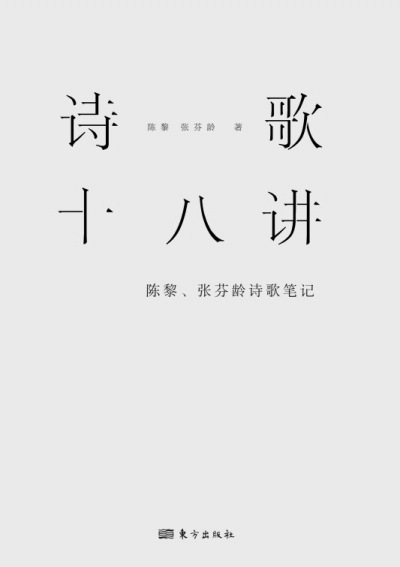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