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略讲传统的书,总免不了要写成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巨著,似乎非如此不能把我们的大传统讲清讲明。然而,结果是著者也辛苦,读者也辛苦。
郗文倩教授的这部《食色里的传统》,名为“传统”,却宕开一笔,单挑“食色”这类小物件下笔,避免了宏大叙事,却精巧绝伦、别开生面,照样把“传统”诠释得淋漓尽致。《食色里的传统》,其妙处就在于看到了传统的具体性。传统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今天我们所谓继承传统,言必称大历史大文化,虽也没错,但究其实质,还不是衣食住行、日用人伦。所以说,以小见大,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
《食色里的传统》由数十篇小品文辑合而成,严格来说,是一部小书,但小而精,每篇都如同一个“核舟”,被雕琢得极为细致;然而这又是一本大书,全书由六个主题构成,涉及衣食住行、娱乐节令,无不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
古人讲“吃饭皇帝大”,头等大事自然要放在最先,因此本书以“饮食”开篇。从道家的养生,到民间的习俗;从食货的历史,到文人的闲情;从宗教的戒律,到时令的小菜,竟把人看得渐觉口中生津。
古人又讲“人生如戏”,待人进入暮年,总不免生此感慨,故而本书以“百戏”收尾。真假难辨的幻术、瞠目结舌的虫戏、惊心动魄的跳剑、来路奇特的傀儡。读罢,真真让人感慨的竟不是戏本身,而是梦幻泡影四个字,且看那田猎场上的蹴鞠、皮开肉绽的斗鸡、忠心反受戮的走狗,到头来岂不是一场闹腾乎?直教人悟得“人生如戏”,好快去“游戏人生”。
这本书读来轻松,不知不觉就读完了。“大珠小珠落玉盘”,合上全书,不得不说,这66篇小品文,给人留下的就是满盘珠玉的美好感受。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百戏”,尤其《傀儡戏》一篇,令我反复玩味,啧啧称奇。
傀儡戏我们都熟悉,但对傀儡戏的历史却知之甚少。作者没有要写成考据性的文章,但用了破案的方法,一层层剥开了傀儡戏的源代码,却看得我紧张兮兮的。
傀儡就是偶人,但凡象人的东西,越往久远了追溯,就越与神秘文化相关。最早的线索可追溯到西周早期,周穆王西巡昆仑时得一舞者,其进退俯仰、曼声而歌、翩然起舞,甚至向宫人暗送秋波。周穆王岂能相信这活灵活现的竟是个偶人!为辩白冤屈,工匠当面拆解了偶人。只见他将心拆去,偶人便无法说话;将肝拆下,眼目尽盲;将肾拆除,无法行走,由此穆王心悦诚服。
类似的线索,在西汉的还有一例。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困于白登山时,为了脱困,陈平发明了一个木偶美女。他使该女在城头婀娜起舞,那翩若惊鸿的身子,把嫉妒心极强的冒顿之妻阏氏激得醋意大发,遂逼迫单于退兵。
以上两则故事,皆是关于木偶的起源,匪夷所思,难以当作史实。
于是作者告诉我们,其实在考古中,最常见到的木偶,乃是作为陪葬品的“人俑”。197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莱西县发现了一处西汉墓,其中发掘出一个身高一米九三的人偶,该人偶全身机动灵活,可坐、可立、可跪。“一米九三”“人偶”“陪葬品”,单就这几个词语组合在一起,亦不免让人有些头皮发麻,联想起《盗墓笔记》里的桥段,却也把个读者的探秘胃口吊起来了。
然而要说傀儡戏的源头,以上说的还只是傀儡,尚不是戏。东汉的《风俗通义》最早提到傀儡戏,并明确说明这是一种“丧家乐”,意即丧葬仪式上的表演。这种戏怎么表演?不妨参照儒经里提到的“傩戏”,那是一种带着恐怖面具进入墓室为死者驱鬼的仪式。《论语》里有“宋人傩”的记载,故宫藏有宋代《大傩图》的名画,今天的民间也有傩舞的传统。史料记载,傩戏的主角很多时候是制成肢体灵活的木偶,因此这一傀儡戏的起源说,或许可靠些。那么问题又来了,丧葬仪式上的表演,何以转变为后世欢快的娱乐节目?
其实这一转变真不好考证,因为这一转变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形成了。《风俗通义》说,当时社会对傀儡戏的接受达到了空前开放的局面,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宾礼、婚礼等宴会之中,形成了难以置信的风尚,当然也遭到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诟病。葬礼上的表演搬进了婚礼,我只能说,果然历史比小说更精彩。
此后,随着木偶技术的发展,古人又发明了手套木偶、提线木偶,还出现了特殊的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等等,这些名字听着都有些叫人不寒而栗。而在表演习惯上,至今在闽台地区,还特别讲究傀儡戏的表演场合与观众禁忌,比如宜在灾难现场表演,因为那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孕妇则不能观看傀儡戏,等等。这应该就是早先傀儡戏巫术性质的遗存吧。
读罢《傀儡戏》,脑中仍久久徘徊着盗墓电影的画风。从穆天子的仿真偶人,到西汉古墓的巨型人偶;从驱鬼的傩戏,到婚礼上的丧仪;从傀儡的变种,到闽台的禁忌。穿梭古今,往来阴阳,窃以为,佐酒之妙,亦不过如此吧,岂非小品文里有大乾坤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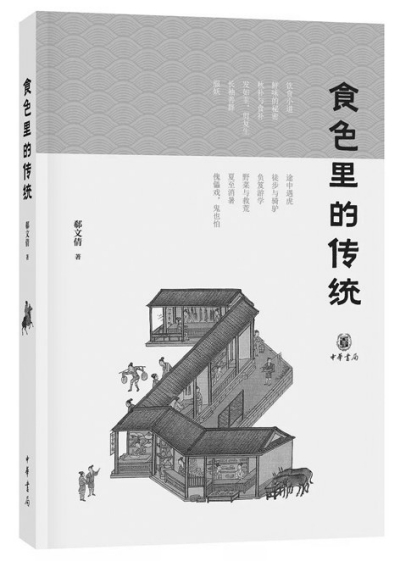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