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在《郭维森先生纪念文集》的序中说:“郭维森先生逝世以后,我们遵照其遗愿,丧事从简,也没有举行其他形式的悼念活动。郭先生为人淡泊谦逊,生前既视名利如浮云,身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然而正如古语所云:‘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尽管岁月流逝,郭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活在大家的心中。”转眼又过了六年,我惊讶地发现大家对郭先生的追思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相反,这种追思逐渐摆脱了死生相隔的震悼悲痛而转向对其生平业绩的理性思考,从而达到新的深度。郭维森先生是教师,也是一位学者,他的生命价值部分地体现在其学术论著。王安石在悼念王令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将郭先生的论文自选集《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一书公开出版,正是其“故人”——他的同道、弟子、亲友——的心愿。付梓之前,郭先生的夫人顾学梅老师让我为此书作序。郭先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业师之一,我为其遗著撰序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自忖学问浅薄,专攻方向也与郭先生有异,故不敢对全书内容作系统的分析,只能谈谈阅读书稿的点滴心得。
郭维森先生的学术成果包括专著与论文两种形式,前者如《屈原与楚辞》《屈原评传》《司马迁》《诗思与哲思》等独著,以及《中国辞赋发展史》《古代文化知识要览》《中国文学史话》等合著,都早已问世且多获好评。后者则散见于《文学遗产》《南京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多年未能结集。直到2010年,南京大学文学院准备为郭先生庆祝八十寿辰之际,缠绵病榻的郭先生才自选单篇论文30余篇,结成一集,题作《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印行后分赠友好,并未公开出版。不到一年,郭先生便与世长辞。此次顾学梅老师在郭先生的入室弟子管仁福教授等人的协助下为郭先生整理、出版《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在保持该书原貌的基础上增收论文10余篇。《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原是本书中一篇论文的题目,它虽然未能涵盖全书的内容,却能代表全书的精神。郭先生生前取此为论文集的书名,自有深意。早在1960年,年未而立的郭先生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古代文学的社会意义缩小了吗》一文,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日趋缩小”的议论,郭先生大声疾呼“要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指出“优秀的文学遗产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必将获得更大社会意义”。应该说,在“厚今薄古”成为时代思潮的上世纪60年代,郭先生的言论是不合时宜的石破天惊之论,他因此而受到批判,“文革”中还因此受到追究与整肃,当时中文系的一位老领导曾说郭先生“是想挽狂澜于既倒”,但是郭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到了2006年,他又撰写万字长文《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针锋相对地严辞批判“古代文化不适合现代化”“古代文学已经陈旧落后”等谬论,并从四个方面论证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增强爱国主义感情;浸溉平等的民主意识;唤起纯洁美好的感情;培养对大自然的热爱。重视本民族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当代美国的著名大学对西方文学经典就极为重视,例如哥伦比亚大学连续多年开设西方文学经典课程,描述该课程的著作《伟大的书》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又如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的著作《西方正典》,通过讲解西方文学经典来促使现代人更加重视西方文化传统,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拥有三千多年优秀文学遗产的中华民族当然更应该强调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更应该强调对中华文学经典的阅读和学习。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它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经典作品无不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聊斋志异》,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之双重身份。诸如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热爱自然、关心他人、提倡奉献、崇尚和谐、鄙视自私、追求高尚、拒绝庸俗等道德取向,都在中国文学经典中得到充分、生动的体现。毫无疑义,中国文学经典最生动、最直观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好桥梁。上述观念如今已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而成为常识,但是它曾经在激进思潮的冲击下被弃若敝屣,后来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历程才恢复正常。郭维森先生的学术贡献,应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得到充分的评价。郭先生在1960年发表《古代文学的社会意义缩小了吗》,不但体现了卓越的见识,而且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良知。他在2006年发表《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则说明他的认知已经升华为更加理性的思考。所以我认为,郭先生将论文自选集题作《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堪称画龙点睛。
郭维森先生逝世后,我曾撰文纪念,文中引《论语》载子夏之言:“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无论是亲聆郭先生生前的言谈,还是阅读其学术论著,我都曾联想到子夏之言。郭先生待人接物态度温和,但当他抨击时弊时,却变得慷慨激昂,声色俱厉。郭先生的学术论著文风朴实无华,论点实事求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绝无模棱两可或趋炎附势之时弊。以郭先生用力最勤的楚辞研究为例:上世纪80年代,海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屈原其人的思潮,主要是出于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之手,国内也有人随声附和。1984年,郭先生向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题作《从屈原创作的个性化论屈原之不容否定》的论文,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屈原的真实性及其伟大意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取了很大的反响。与此同时,某些爱唱高调的国内学者拘于时髦理论而否定屈原忠于楚国、反抗暴秦的行为是爱国主义,对于这种貌似新颖的谬论,郭先生于1990年撰写了《屈原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一文予以痛驳,指出在屈原的时代,爱国主义有着特定的内容,而屈原的爱国主义又有着独特的表现:对故国、故乡的热爱,对人民的关切,以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郭先生指出:如果说秦始皇用武力从政治上统一了中国,那么屈原则以他的诗篇从思想上促成了中国的统一。每当我读到这些掷地有声的论述,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听其言也厉”这句话。无独有偶,曾与郭先生合著《中国辞赋发展史》的许结教授评论郭先生的学术风格时,既称道其“平实”“中正”“真诚”,又赞扬其“奇崛”。用“奇崛”二字评价郭先生的学术,真乃探骊得珠。王安石有句云:“看似寻常最奇崛。”虽然这句诗的评说对象是诗歌创作,但移用来评说郭维森先生的学术研究,也恰如其分,故谨引此语作为这篇序言的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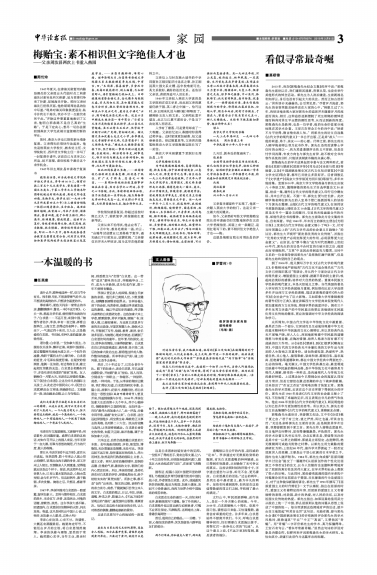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