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不合时宜的中国古代文学研治者,也是自封的魏晋六朝文学的痴迷者,因为我能够体验对嵇康、陶渊明、谢灵运辈那种发自内心的如醉如狂,以及对于两千多年前风流的评说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境。可惜这种醉、狂与渴念在现今“课题”“评奖”充斥的学坛是愈来愈难以激起了。
然而,我最近终于还是被激起了。激起我的是孙明君,他是如春阳之温时雨之润的谦谦君子,也是头角峥嵘的年轻学者。其新著《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与其先此出版的《两晋士族文学研究》适成双璧,很好地体现了明君的学术观点和学术造诣。
《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围绕主题,重点研究了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沈约与萧衍之交往、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阙当代不言”说辨析、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之转变、陈叔宝的雅篇与艳什释论、杨素与廊庙山林兼之的文学范式、杨素薛道衡赠答诗探析,等等。这些问题都别开生面,各恃胜场,但又因贵族文学串联,惨淡经营,历历如贯珠矣。下编则是颜延之、谢灵运等十九位南北朝作家生平事迹辑录,意在为本书上编的研究提供广泛而可信的文献支持和事实依据,是作者多年工作的积累,形式为辑录旧籍,而实则见取舍眼光。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士族、庶族、皇族在权力斗争中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南北方之间敌对而又相互影响,这些无不深刻影响着文学、艺术、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研治南北朝文学者不多,而卓然挺出者更为寥寥。以愚见所及,自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问世以来,此一领域惟曹道衡诸论著差强人意,明君兄此作后出转精,则承申叔遗绪,不让曹氏专美于前矣。
支持我拍案赞叹之理由,荦荦大者有三。
其一,撰论角度新颖。作者摆脱士族文学之窠臼,提出了贵族文学的概念。他认为南北朝贵族文学是指南北朝时代以皇族和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创作的、内容上具有鲜明贵族意识、在艺术上体现出贵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而且,他进一步认为,两晋的贵族文学主要是士族文学,宫廷文学并不兴盛,南北朝的贵族文学,则不仅有士族文学,同时还包括宫廷文学。所以说,两晋文学以士族文学为主体,南北朝文学以贵族文学为主体。明君兄以上的观点应该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卓荦之论,不仅使他的著作义立骨峻,新见迭出,而且亦适足为此一领域跋涉者之圭臬。如刘宋诗人鲍照,出身庶族,“家世贫贱”(虞炎《鲍照集序》),所谓“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鲍照《拜侍郎上疏》),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其列入士族文人或是寒门文人而论之。然而其受知于刘义庆,仕为参军,其《侍宴覆舟山二首》《从拜陵登京岘》《蒜山被始兴王命作》诸作,分明展示的是清跸羽盖的贵族生活;其《河清颂》一赋,更充溢着皇家气派。又如陈后主,其祖“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陈书·高祖记》)所谓“土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临时户口转正,据此可知陈家已住长城县二百年,家世寒微,不在士族之列。以后陈叔宝虽践大位,在作派上还是带有下层游民的遗传因子,故而有《玉树后庭花》《舞媚娘》《三妇艳词》等淫艳之作。明君兄将其列入贵族文学,引申为宫体乃宫廷文学之变异,从而畅论之深探之,是可谓“得其所哉”了。
其二,用朴学亦即乾嘉之学的方法来研治南北朝文学。此书从个案入手,通过对相关史实的分析和文学作品文本的细读,尽量深化对个体问题的探讨,从而上升到对贵族文学现象规律性的探讨。我们试读上编十章,每章都是有的放矢,不作泛泛空言。论述方法上则层层剖析,穷尽图相。如第六章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阙当代不言”说辨析,首先罗列了前修对刘勰“阙当代不言”的诸种意见,接着叙述了《文心雕龙》中对当代亦即萧梁文学既颂美又贬斥的矛盾态度,认为刘勰既已评骘萧梁,就不能说是“阙当代不言”。这当然是有力的辩驳。同时,他也承认了刘勰的确对具体作家没有点评。再接下来,作者考察了《明诗》《体性》《定势》《物色》《通变》诸篇文本,发现其中对当代文坛做出了与《时序》截然相反的评价。最后,作者探讨这种矛盾现象的历史必然性,找出了影响《文心雕龙》“阙当代不言”的两点因素。说实在话,明君兄这种义证兼赅、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的论述,让我想起了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著作。
窃以为,这就是学风。明君秉承的学风堪称当前学术界的一股清流。
其三,材料出新。记得曩时随表兄陈贻焮先生游雁荡山,陈先生说:“撰论总要求新。上者观点,次者方法,再次者材料也。”材料出新虽属撰论末事,但却最见腹笥,最要功力。如本书第四章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为叙述谢庄一生对刘宋朝廷忠贞不渝,竭诚尽智,作者先是引用唐许嵩《建康谨》卷十四,又引谢庄《密诣世祖启事》,再引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关于《搜才》《定刑》二表及《与索虏互市议》的评论,很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论点。而且这些材料都很新鲜,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我虽痴长,但有幸与明君同道,自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字资料俱已过目,但读此书,仍感心降。原因一是明君能用冷典,二是能准确找到异代资料。总之,材料问题上是明君出奇致胜处,亦是其见大功力处。
四十年前,我在武昌珞珈山随吴林伯先生攻读汉魏旧籍,其时“评奖”初萌,我请问本师,学术著作以何者最优?吴师不假思索曰:“以同行推重者最优。”我今白发江湖,醉眼微睇,无名无位,然忝列明君同行,秉本师开示,我以为《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是一部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谨负责任地向读者诸君推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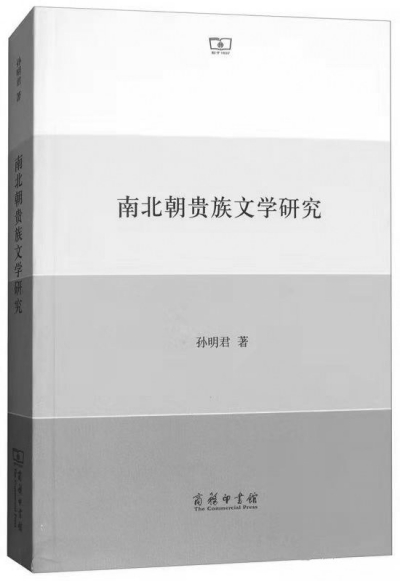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