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发先生年届八旬,身体棒,有时电话打来,胶东话那样洪亮,让人感到一股豪爽。没想到几个月不见,他就突然撒手离去了。本来最近也想约他喝茶聊天,却再也没有机会了。事情该做,就得加紧啊。
朱德发先生的过世,让我想到他和山东师大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团队,兢兢业业几十年,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这个团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最早可以追溯到田仲济先生,他写的《中国抗战文艺史》,1947年出版,后来是朱德发先生做了充实增订。文革以后,记得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文学史,就是山师的田仲济先生和山东大学的孙昌熙先生以及两个学校的老师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八十年代以后,这个团队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学史著作,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朱德发先生的《中国五四文学史》(关于“五四”他有三本书)、《中国现代小说史》、冯光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影响不小。最近这些年,朱德发先生、魏建先生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一百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著作。文学史写作,是这个团队的“重头戏”。朱德发先生在其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这个团队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比如薛绥之先生,他组织编写了《鲁迅生平资料》。当年鲁迅的资料很分散,有待发掘整理,他较早做了这个工作,影响也是很大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包括流派史的研究、文体史的研究、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当代文学评论,山师在全国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个团队是非常齐整的,与全国同一领域的各个大学,包括一些著名大学比较而言,也自有其特色。从田仲济先生开始,有薛绥之先生、冯光廉先生、蒋心焕先生、查国华先生、刘增人先生、宋遂良先生——他们都是跟朱德发先生大致同一辈,或者老一辈的。年轻的生力军也涌现出一大批,一个个都是响亮的名字,比如吴义勤、魏建、张清华、吕周聚、房福贤、姜振昌、李掖平、李宗刚,等等。他们一批一批地出来,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相当活跃。
不光是科研,在人才培养上,山师这个团队也有非常骄人的成果,培养出很多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像杨洪承、张光芒、周海波、王兆胜、温奉桥、贾振勇、耿传明、谭桂林、罗振亚、张丽军,等等,都是响亮的名字。
我能鲜明地感觉到朱先生和他的这个团队的气度、风格:在山师这里,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名士气”;比较少、或者说没有“才子气”;也很少学术的“玩票”或者自娱自乐的东西。这个团队多数的学者,都是比较脚踏实地的,就像农民开垦一块地,播下种子,勤勉地等待收获。几十年来,这个团队给人感觉有一股向上的力,有学术的激情,也比较团结。这是令人羡慕的。
朱德发先生可以说是山师这个现代文学团队的一个代表,或者说核心。朱先生的人格、作风,显然影响到这个团队。在庆贺朱先生八十诞辰时,有人撰写贺联用了“方正坦诚”和“开拓创新”八个字来赞赏先生——确实,朱先生为人坦率,为学虔诚,终生笔耕不辍,到八十多岁了,还不断写文章提出一些有创意的观点。朱先生对文学史的思考,他的文学史观是有实践的,不光是概念的提出。或许你不一定同意他的写法,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文学史写作的生态。我特别欣赏朱先生的一点就是,他认为文学史写作要用激情去拥抱研究对象,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理性。比如他提出了“标准”的问题,一个时代总要有大致的、比较能取得人们共识的标准。这都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现在我们确实很多元,但是缺少标准。他提出的“一个原则,三个亮点”等等,值得我们文学史写作加以参考。
朱先生还被教育部授予“高校教学名师”称号。据说他自己非常高兴,还专门请客吃饭。他不只是虔诚的学者,还是一个很尽职的老师。他知道一个学术团队光发表文章是不行的,培养人才、教书是本职。“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他不是形容,是事实。现在“朱家军”在学界已经形成气候。
青岛大学编写“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我写过一篇序言。朱先生也是第二代学者,他身上也有这一代学者的某些共同的特点。我在序言中说:“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有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说明。”
当然,他们这一代也有缺点,譬如说在大批判的年代里留下了极左的东西,但总的来看,这一代在学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朱先生身上体现了第二代学者的一些亮点。
从一个团队来看一个学科,从一个学科的带头人,看几十年研究的历程,会引发了我们一些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在八十年代曾经被称为“显学”。因为它满足了时代的需求,也从时代的变革中获取了巨大的动力。九十年代以后有些变化。这个学科逐步成型了,同时也越来越开放,接受了西方一些研究的理论、方法。年轻一点的学者非常兴奋,觉得学术进入了新的年代、新的境地。但人们很快发现,九十年代的研究,借用西方的方法、视点,也有问题,就是缺少历史感,对历史现象缺少同情之了解。所以这些年,对这样的理论方法又有所反思和淡化。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确实比较成熟了,学理化的建设也比较规范了。但现在的问题,正如朱德发先生所曾经指出过的:缺少“标准”,各行其是,没有交集,甚至有些碎片化,以至于这个学科失去了回应现实的能力。我也有同感。但是我相信,有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有像山师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那样努力和持续的工作,这个学科肯定有它光明的前景。我想,朱德发先生也会感到宽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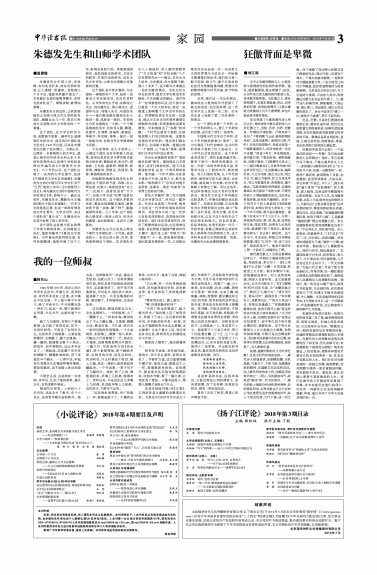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