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
最近的一篇文章《了不起的年轻人》中,作家周嘉宁回忆了她2001年第一次来北京的情形。那时她还在复旦大学读书,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而在写作上崭露头角。在北京她住地下室里的国营旅馆,乘公交车去颐和园,还赶上了北京申奥成功的晚上……“这种纯粹的集体性快乐带给我的震撼非常强烈,而当时的我身处其中或许并不会意识到,这样的快乐可能是没有办法复制下来的,而那个时刻终究会以某种方式给曾经身处其中的青年留下印记。”她在文章中这样叙述亲历那个狂欢之夜的感触。
十几年过去,周嘉宁继续走在写作这条路上,以不紧不慢的速度。她写得又从容又谨慎,这符合她对待文学的态度。她的作品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个性气质,细致、准确,有与笔下人物共命运的诚意,也提醒自己保持必要的疏离。这些特质,在她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基本美》中体现得很充分。她关于北京以及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记忆,在她的写作中,由这些作品人物所经历的平凡情感与日常聚散一点一点拼贴、清晰起来。世纪交替,时代变迁。京沪港,《基本美》中的年轻人身在那样的大时代,度过平淡的青春,连困境都难说有多么凶险。而庸常世俗的表象下面,是不动声色的力量和可资记录的片段。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那个下午,周嘉宁乘京沪高铁来到北京,第二天要在三里屯的Chao酒店和读者们分享她的感受,拉开之后一系列跨越若干城市的新书宣传活动。穿着白衬衫的她瘦瘦的,像个仍在校园中的大学生。做过记者的她,担心表达上的模糊和歧义,回答问题前总是几番斟酌才开口。这样的克制、得体与她在写作上的分寸感颇有默契,她不愿微言大义地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淡化写作在呈现群体记忆、记录时代上的作用。不过,她的写作正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些这样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读完《基本美》,发现书中的好几个短篇贯穿其间的主题就是“回忆”,人物之间往往若干年后再见面,展开回忆中的故事,这是有意设计的吗?
周嘉宁:其实我没有刻意地这么设计,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常常是无意识的,没有完全想好到底要干嘛,很多问题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慢慢解决。这本书里的年代背景是2000年到2010年,写作时我只能对这段时间进行思考,2010年到现在的这些年,外部世界和之前比起来变化很大,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各方面的生活状态区别都很大,这十几年对我来说还没有呈现出能够清晰捕捉的结果,身处时代漩涡是没办法看到时代的变化如何作用到个体上的。
中华读书报:来采访你之前,看到“理想国”公众号上你的一篇文章,写到几年前你和父母去海岛玩耍体会到“正是一些这样的时刻,基本美,随便走走,嬉戏漫游”,由此我想到你写的这些人物,无论生活状态还是精神状态,要么正身处这种嬉戏漫游的境地,要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你对“基本美”的一种理解?
周嘉宁:我觉得我笔下的这些人物活得都还不错,至少在我的评判标准里是好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一个点吧。我以前写小说会把一些想象中的命运甚至我不认可的观点强加到人物身上,一旦这样做了以后,我会忍不住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流露出嘲讽的态度。我现在挺讨厌小说中有对人物的嘲讽、轻蔑,这样对人物的态度是我想要避免的。我应该让人物生活在一个我希望能够创造的世界里,可以按照他们的个性生活和思考。
中华读书报:这篇文章中还有一句话触动了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分担起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这算是写作上的代入感?你会因人物命运的变化而内心起伏吗?
周嘉宁:我小说中的人物命运都没有很大的变化,我没有把人物命运写得特别跌宕,没有刻意去写那些带来强烈情感起伏的命运,我这个人身上也没有那些强烈的情绪变化。但是,情绪变化和感情共鸣是两回事,感情共鸣有时候可以很深沉,未必是激烈的。
中华读书报:《基本美》这篇小说里写到了世纪初的北京,写到各地前来的文艺青年,户外音乐节,还有那个香港乐队,这些是不是有原型?
周嘉宁:这是我想要特别说明的一个问题。我写小说,不是先有一个原型才有这个人物的。就《基本美》的写作,并不是我想要去写一个像mylittleairport(一支香港乐队)主唱那样的人物才有这部小说。而是我先虚构一个人物,当我要写他的外貌,就会想,如果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会长得像谁?所以我就会在写作时借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因素,有些人的外貌特征特别明显,符合我笔下人物的需要。不是说先有原型,然后我用小说去模仿原型,而是先有这个虚构人物,然后我才借用生活中很多人的元素去塑造人物,这些借用是为虚构的人物服务的。有人问我,你这部小说是在写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没有人能够纯粹虚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身上一定有现实的成分,有作家自己的日常经验。
中华读书报:但你所说的日常经验在作品中所投射出的比例,在不同作家应该是不一样的。很多作家最初写作时,作品的自传色彩会更重,随着阅历增加、技巧成熟,这个比例就减少。我看了你几部作品,并不觉得这些作品之间有泾渭分明的差别。对于《基本美》,出版方的推广语和网上的一些评价说这是你的“转型之作”。
周嘉宁:我的每一本书,自己都会觉得和上一本不一样。你刚刚说作家在写作上的代入感,如果要说《基本美》和之前我的写作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我现在的写作视角越来越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这本书里,最明显的是叙事视角的变化。其中我比较喜欢的两篇小说——《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都是以男性视角叙事,这么写其实很舒服。倒不是说我要去挑战男性叙事视角,而是我觉得男性视角的叙事更好写。小说中其实抛出了一些问题,我描述了一些当时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也有疑问。会不会有人看了这些小说思考以后得出更好的结果,那我也可以从这些思考中受益。
中华读书报:你所说对于一代人困境的呈现,侧重强调个体命运,同时这些小说也有时代背景的痕迹。记录时代,是作家不可回避的,你怎么看待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周嘉宁:你觉得从这些小说里看不到我的社会责任感吗(笑)?你不觉得这些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吗?我写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机会让命运和时代的重大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大部分普通人只能是被时代席卷,自己都没意识到怎么回事,时代就过去了。
现在大家都在说年轻作家不关心时代不关注社会,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人不关心时代?有的时候你就算想要避免对时代焦虑也未必能够避免得了。个人命运一定是和大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思考一定是和时代相关的。
中华读书报:实际上,你说的人群划分是从作家的角度。换个角度,读者或者评论界对于作家的划分也是有些标签式的,比如80后、青春文学作家、新概念,等等。时至今日,这些标签的存在感其实已经很弱了。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当年的写作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些年你一路写下来,也是必然的选择吧?
周嘉宁:我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我现在是新概念的评委,每年还是会看那些参赛作品。为什么这些年来大家反反复复还在提新概念,今天的记者还是会问起这个问题?这说明新概念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所有人,也影响了记者们,影响到媒体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影响到一代一代读者的阅读评判和选择。
新概念对于我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当时获奖,真的是命运给我的第一份巨大的礼物。我就是个很会珍惜东西的人啊,得到这么大的礼物当然会善意地、谨慎地珍惜。我能做什么?不就是写作吗。对于写作,我说不上什么坚持吧,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断地会得到世界给予的回应的,这些回应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我成长。
中华读书报:用“坚持”来形容你的状态确实有些牵强,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年顺理成章地就这么写过来了。同时你也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还参与《鲤》书系的编辑工作。这几重身份与文学都有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嘉宁:我觉得我只有一个身份——写作的人。对我来说,文学翻译不是写作的调剂,所要付出的精力其实比我写东西还要多。不过,翻译能够规范我的生活。一个职业写作者如果不能规范日常生活,就很容易塌陷。有翻译的工作在,至少让我的工作系统始终运转,每天都处于可以和语言打交道的状态,保持语言思考的惯性。如果停滞了一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不写作也不接触文字,再启动是有些痛苦的。我愿意让自己这个机器一直处在运转状态,等到需要时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调动起来。当然,做翻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年我越来越觉得中文很美,同时觉得中文在被滥用,很多中性词被滥用后就会变成贬义词,中文的美在被破坏。翻译过程中其实在不断帮助我调整和汉字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必须要选择最正确的词放在最适当的位置,让英文原义尽量损失得最少。这其实是对中文进行清洗的一个过程,让我更珍惜每个汉字在最开始、没有被污染过的那个状态。我也希望可以在写作中正确地使用汉字,如果它已经被污染,希望可以用我个人的方式让它回复到一个至少是中性的状态。
中华读书报: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你好像更倾向翻译女作家的作品?比如艾丽斯·门罗、珍妮特·温特森、弗兰纳里·奥康纳……
周嘉宁:我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标准挺简单,一个是尽量翻译还在世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另外尽量避免翻译一些语言特征明显的作家,因为很难做到把原来语言中最好的部分保留下来。我翻译的作家,语言都不是个人化印记特别强的,除了珍妮特·温特森。我也没有太多从个人喜好来选择翻译对象,除了米兰达·裘丽的作品确实是我翻译的作品中带有个人喜好的选择。至于我翻译的女作家作品多,那是找我翻译的出版社决定的,是不是他们觉得我是女性,翻译女作家的作品会更容易。其实不一定,毕竟每位翻译所擅长的是不同的。
中华读书报:你在翻译上是比较有计划性的,在写作上呢?是那种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要写多少字的作家吗?
周嘉宁:当我启动了一部小说的写作,是每天有规划的。但我写得很慢,小说可能每天只写五百字。但我花很多时间准备,像《基本美》这部小说也就三万字,我每天都在写,还写了差不多三个月才写完。从想要写《基本美》到完成,我花了半年时间。动笔之前要酝酿,有些情节要求证,有些香港部分的内容跟朋友通了很多信件。越写越慢,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中华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你对创作的自我把控应该是很强的吧,还会有很多不可预料的成分吗?
周嘉宁:肯定会有啊,不然的话就没有写作的乐趣了。写作当中一定有很多不可测的地方,对我来说,动笔之前必须做好详细的准备,这种不可测才不会从惊喜变成惊吓。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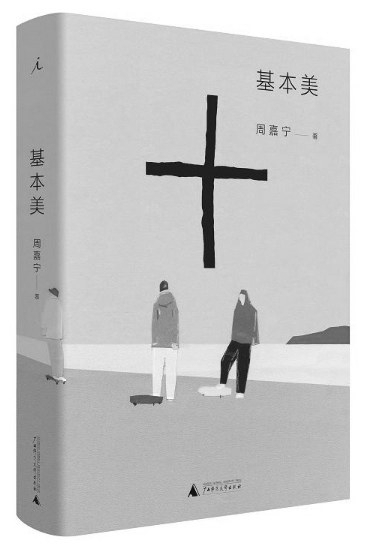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