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介入历史和现实都需要一种路径,那么夏坚勇无疑找到了一种两全的可能。在新著《唐朝的驿站》里,夏坚勇依旧保持着他的儒雅与风趣,他再次在自己辨识度极高的写作风格中挖掘散文深处的另一种可能——时空的对位与超越。他不断地立足于过往或当下的某一个平凡的点,搭建起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并神奇地将之推演成一种普适的情感价值,解读着“士”这个极具古典主义气质的意象,或者说呼唤这个概念的“乘愿再来”。
骨鲠,在夏坚勇笔下标识着“士”精神的归去来。
在整部书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对骨鲠这一品质的高度赞誉。藐视皇权秉笔直书的司马迁、佯病抗暴的九品县尉白居易、集礼乐侠义于一身的季札、大义凛然又深具情怀的周顺昌......作者信手拈来的名士故事无不彰显着一个没有璀璨光华却无比温润厚重的关键词——骨鲠。他书写那些攸关生死的历史片刻,重述那些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郑重抉择,作者将它们深挖成一个个意义的深渊,供我们凝视古人,反躬自问。当然,文章中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对另外一个文人群体的审视与挞写。无论是对以文字换取千斛米的陈寿,还是对执着于名利双收的司马相如,作者都是毫不犹豫地加以冷眼与斥责,尽管他们在文学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和显赫的声名,骨鲠的缺失让他们在作者的笔下面目模糊。
正是因为身为文人,他更能体察骨鲠对于塑造文人精神生命的绝对意义。在这部散文集中,无处不在的就是他对骨鲠的呼告,他敢于代言古往今来全部文人进行精神的自反,这是可贵的勇气,更是一种难得的执着,他渴望着“士”的精神归去来兮。
当然,我们在《唐朝的驿站》中亦时常与温暖这个关键词不期然相遇。
保持内心的绝对赤诚才能够在笔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那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而这种温暖,恰与对骨鲠近乎执念的守持构成了“士”精神的一体两面,溪流与火焰共同锻造着这种来源于传统的高贵品质。
对《温暖而感伤的记忆》这一辑的阅读,可以视为与作者共同温故了一个远去又时时午夜梦回的时代。作者在回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精神故里的重新搭建与修葺,我们的阅读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没有目的却常有收获的旅程,而读者微妙的心理变化也被作者巧妙地调适成了一种对我们生活着的世界颇有质地的思考和卓有意味的审视。
对好友的回忆、过往生活的回忆、书信时代的回忆......在种种回忆的情景中,夏坚勇已经凭借手中的笔勾勒出了一方古朴的的印信,钤记了一个温柔的时代。在物质相对贫瘠,经济尚未如此发达的年月,素朴的生活里满载人性的温存。《书笺小祭》中为了不让妻子苦等寒夜而一路“站火车”归来的脉脉情愫,《大暑天为什么呼喊“小寒”》中与儿子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的沉浸与低诉,《石板街的回声》中烈士张大烈妻子一生品味蘑菇炒肉丝的“深情也大”,《村景三题》中那份对乡土最饱满的依恋和精神上的归属,无不透露着往日的温情,和蓦然回首时的淡淡感伤。这些情感被牵系到白纸黑字的方寸之地,像一首拨动心弦的老歌,让我们在追逐快速发展和物质丰盈的生活中找寻到了慢下来的方式与重新感受“初心”的可能。这种甘于守贫的精神和对人内心深处情感世界的体察,亦是作者呼唤和找寻的“士”的风度,这种风度在一篇篇散文中是如此的牵人心神。
作者对英雄和战争的深刻分析,实质上是完成了对“士”精神的进一步指认,“士”绝不是只纠缠于个人际遇上的慷慨讲演者,而是与家国、生民、苦难站在一处的践行者。在这个层面上,作者夏坚勇借助力透纸背文字对展卷的我们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扣问,而我们受到震动的程度,则构成了“士”精神能否彻底回归的有效参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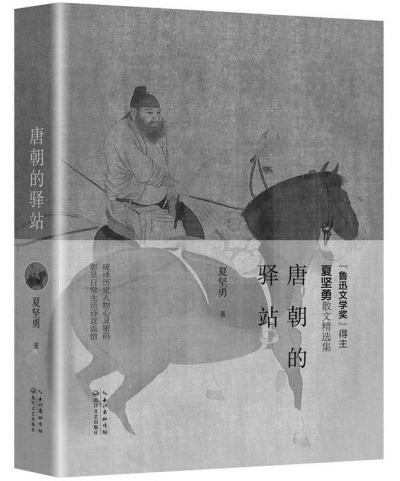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