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近代日本学者西周以汉语“哲学”翻译“philosophy(爱智)”时,不得不说他独具法眼,因为《尚书》有“智人则哲”之说法,《说文》《尔雅》皆以“智”训“哲”,可见“智”与“哲”可以互训,因此以“哲学”翻译“philosophy”可谓原来有自。这意味着,不管中国学者承认不承认,近代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必然会走上一条追寻智慧之路,至少,自觉地寻觅经子中所隐含的智慧是不该忽略的一条中国哲学研究之路。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从奠基之时就有一种“反智”倾向,然而“反智”又何尝不是一种“智”呢?如果承认“智”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之对真理的追求,而且包含着一切对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之探寻,那么“中华的智慧”作为一种迥异于西方传统的“哲学”便实至名归。这种“中华的智慧”便是我们古圣先贤所不断寻觅、探问、践行的“道”,换言之,中国哲学是关于“道”的学问,读书学习是“问道”,学有所获是“闻道”,身体力行是“志道”。
正是带着这种探究“中华之道”中所蕴含的“中华智慧”之学术自觉,张岱年先生(主编)与方立天先生(副主编)统领诸高弟(程宜山、刘笑敢、陈来)编撰成《中华的智慧》一书。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2月初版,近来又由中华书局于2017年11月再版。此次新版补充入部分出土文献之材料和思想。另外,新版附录加有参与撰写的陈来与刘笑敢两位先生所列两种“中国哲学书单”,陈先生所列书目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劳思光等“中国哲学通史”类著作外,以传统经典为主;刘先生所列书目则还包含不少时贤之学术专著。这些书目可备读者参阅。
智人其哲,哲人其智。哲人是智慧的主体,是智慧的承载着、阐发者。智慧是哲人对世道人生、天地宇宙的独见独闻或先知先觉,它注定不是人云亦云的市井常识,也不是循规蹈矩的老生常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哲学的进步实则是哲人学术与智慧品格的不断推陈出新。既然此书旨在探寻古老中华的智慧,故其目次划分便不再突出时代学风和学派意识,因为时代特色或学派意识可能会淡化作为智慧担当者的哲人之个性,这样哲人智慧就可能隐而不彰,也就没办法与一般的哲学史著作区别开来。相反,本书以哲人或哲学家为目次纲领(仅《易传》以书名为章目,因作者不可考),以春秋末期之孔子、老子启篇,以清代之颜元、戴震收笔,涉及两千三百余年含括九流三教共三十七位中华哲人。如果说宇宙人生之真理是那座“不识真面目”的庐山,那么哲人则是从四面八方排闼而来的观者,他们所见所思并非一致,但他们却各有独出机杼的智慧,一如观光者会从不同角度去欣赏庐山的远近高低,哲人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宇宙人生的然否是非。这部书正是以一种平实的态度展现两千多年的中华哲人智慧,少了几分先入为主的判教意识和褒贬揶揄,多了几分公允情怀和恕古之道。
就具体内容来说,此书也体现出作为一种中华智慧的中国哲学。作者们没有如一般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叙事一样,将中国哲学史视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观念辩证运动,也不是以所谓“基源问题”(劳思光)为导向而构建每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而是从历代哲人著作中萃取集中体现其哲学智慧的关键思想进行阐发。这样,枝叶被芟荑,茅塞被扒开,“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孟子·尽心下》),哲人之智慧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朗现出来,可谓是水落石出,云敛日开。比如,关于孔子之智慧,作者拈出“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过犹不及”“多学而识”等四个核心理念去展现孔子的人生智慧,这里既有被今人称为交往黄金律的“忠恕之道”,也有被视作康德哲学之“自由意志”的先声,还有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和知识论等等。关于老子之智慧,作者拈出“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祸福相倚”“柔弱胜刚强”等几个关键理念,既涉及哲人对终极存在的追问,也有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和对人生存在祸福无常的反思等等。这种对“智慧”之突出的哲学叙事方式不再是宏大的经典哲学史撰写,其展现的是要言不烦、直蹈堂奥的人生哲理,如孔子所谓“为仁由己”,实则是说道不远人,但看此心如何想;老子所言“道法自然”,是说素朴从简原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天地如此,人何以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书旨在突出对中华智慧的探赜,一些被通常哲学史论著所忽略的哲人如墨辩后学、惠施、公孙龙、范镇、方以智、戴震等也被颇为重视地论及。如作者专章论述墨家学说之“好学而博”的特征,大力表彰墨家学派的“科学学风”;作者将惠施哲学的“历物十事”(保存于《庄子·天下篇》)进行一一详阐;作者将公孙龙子的《名实论》《白马论》《坚白论》《指物论》(《公孙龙子》传世七篇,此书论及四篇)等都详细论及。重视理论思辨和名相分析的名家学派虽然昙花一现,但中华智慧谱系实在少不了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论及墨辩思想时,作者遗憾地写道:“墨家科学传统的中绝,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巨大的损失。”在论及方以智哲学的科学精神时,作者写道:“他的那种对于知识的热爱和追求,那种对摒弃知识的学说的憎恶和鄙夷,那种追求知识而不顾一切的勇气,那种博采万方的宏大胸怀,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几乎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还原中华传统学术中的科学精神是阐发“中华的智慧”的题中之义,但这部书突出对这种“科学学风”的彰显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重视玄思和体悟的中国哲学虽然可以避免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异化,但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着在所难免的未尽之处。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忽视细密的分析,缺乏严谨的论证,表现了很大的不足。”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实证主义在中国传统主流哲学中的消失。
张岱年先生是一个真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流风所及,其弟子也大都受其影响,反映在这部书里,就是特别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智慧。事实上,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富于辩证思维,这是一个显著的优点。”也就是说,重视辩证智慧本身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职是之故,注重钩沉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论及孔子时,专门强调其“过犹不及”之思想,论及老子时,专门强调其“福祸依伏”“柔弱胜刚强”等思想,论及《易传》时强调其“阴阳转化”之思想,论及庄子时强调其“彼是方生”之思想,论及程颐时强调其“物极必反”“理必有对待”等思想,论及朱熹时则专列其“两端相对”“阴阳交变”“体用对待”等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辩证智慧落实于人生实践,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遭逢际遇和忧患得失;用以观照自然天道,就是以天道的阴阳、昼夜、四时等交推轮回来参悟人生的生死流变;用以哲学思考,就是在天人、义利、有无、空有、体用、道器、正反、理气、理事、理欲等对待辩证中用思想去逼近宇宙人生的真源。
张岱年先生将中华“深湛智慧”分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等三类,如其所言:“中国古代哲人所讲的‘人生之道’是关于如何做人的智慧;其所讲的‘自然之道’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智慧;其所讲的‘致知之道’是关于认识方法的智慧。深入了解这些智慧,对于如何做人,如何认识世界还是有益的。”这三种智慧大体来说可分别对应人生观、宇宙观和认识论等,中华的智慧皆含摄于这三种哲学之中。罗素先生在完成《西方哲学史》后又撰写《西方的智慧》一书,正是受其启发,张岱年先生在完成《中国哲学大纲》之后又组织编撰《中华的智慧》一书。如前文所言,偏重理论思辨和体系重构的哲学史专著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中华智慧”的一种“所知障”,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慧”进行萃取并彰显出来,可以说有“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效。以此书来沾溉士林启迪后进,或是张先生晚年孜孜以求之苦心孤诣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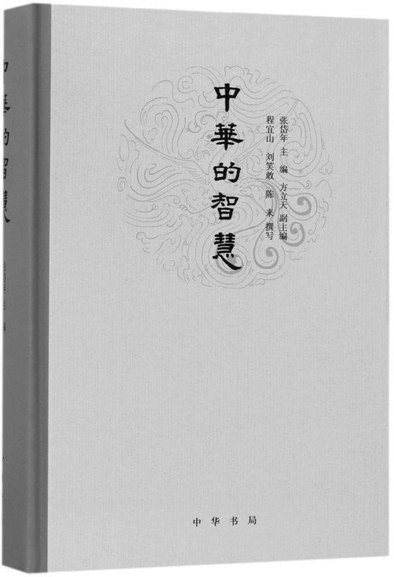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