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焕龙的诗歌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鄂东地域文化的窗户。
《潘焕龙文集》的编辑出版,让这位清代的文学与文化大师重见天日,而不是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无疑填补了一项中国清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空白。
潘焕龙于乾隆59年(公元1794年)诞生于湖北罗田,22岁考进紫禁城,于武英殿当教录,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受道光皇帝召见,外派河南洧川县当县令。由于长期在京城工作,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仅被当时的一些硕学鸿儒引为知己,还被一代名臣曾国藩夸赞为“一笔能抵万人之敌”,是有名的“诗人县令”。他曾任职于河南洧川、商丘和山东邹平,为官清正、为民造福一方。同样,他的诗歌诗品高雅,诗格清奇,是他官品和人品的最佳注释。他是被埋没的清代文学与文化大师,这一次,被春生教授和余尘博士从故纸堆里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无疑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的文化大事。
潘焕龙诗品高洁。其高洁诗品同样是他高洁官品的具体呈现。他的诗歌虚实结合,沉雄有序,超以像外、得其环中,写梅有梅的高雅,写雪有雪的纯洁,乃绿山观野屋,落日见气清的上乘之作。看他的《梅雪十咏》中的诗句:“路隔江南千里远,魂牵东阁一支春。”“雪碗冰瓯闲涤笔,风流水部旧关情。”“寒气仅教凌傲骨,前程毕竟识芳心。”“瑞兆年丰蝗入地,要看盈尺慰农夫。”可以说,《梅雪十咏》是潘焕龙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代贤令的虚谷高怀。他面对“寒气”和“蝗入地”展示着诗人之“傲骨”和“芳心”,即使“路隔千里”也“魂牵一春”,因此,他的心里“关情”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关心百性疾苦,用“盈尺”来“慰农夫”,一个“盈”字展示了他为官清正的高尚情操和诗人情怀。就像他在洧川兴学堂,析冤狱一样,他的诗高品而气清,积健而沉雄,既有“雪碗冰瓯”的纯净“涤笔”,更有“风流水部”的温暖“关情”。
鄂东文化具有儒道结合的特点,体现在诗人的人格里就是既慷慨激昂又性灵闲散。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山川秀丽,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平原千里,民风淳朴,既有薄刀锋的险峻,也有天堂湖的柔美,所以,造就了潘焕龙诗歌格调清奇的特征。他的诗灵动如风游,飘逸如水流。我们常说诗格即人格,潘焕龙之清奇格调正是他清正人格的具体体现。看他的《春日杂诗》中的几首:
树色苍茫欲夕晖,金炉香烬篆烟微。抛书别有关心事,亲卷珠帘放燕归。
紫陌寻春借玉骢,摇鞭缓缓踏春风。多情最是斜阳好,照得桃花影亦红。
小立闲庭落照中,辞枝花片各西东。春风不忍残红落,婉转相吹其半空。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的诗人,潘焕龙一面怀揣着一颗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真心,一面承袭着与身俱来的安贫乐道的家风,因此,他以清奇的笔调写出了他恬淡自由的心灵。看第一首诗,在“树色苍茫”和“金炉香烬”的“夕晖”中,一切归于平静,本来是适合读书的,然而他一反常态,他“抛书别有关心事”,而是把“珠帘”轻轻卷起,让燕子归来。这一个生动细节与其说是诗人一种悯怀之心,倒不如说是潘焕龙的一种自然和谐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可以平静地在“夕晖”下读书,而“归燕”也应该此时回巢了。人和动物,屋里的世界和外面的游子共享这一片刻的安宁。而在另一首诗里,他“借玉骢”去“寻春”,而“春风”就在缓缓的“摇鞭”里,“踏踏”的马蹄下,在“多情”的“斜阳”下,“桃花”开放,春影摇动,一片红红的春天。而第三首体现了潘焕龙自由而悲悯的情怀,他看到“花片”各飞“西东”,而“春风不忍”“残红”飘落,那么就让它们依旧飘扬在“半空”中。诗人潘焕龙从田间劳作、秉烛读书、兴来作诗中获得了无限乐趣。作为一名官员,在民心不稳,贫困不足的社会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才是诗人心中的向往。
这几首小诗正是诗人诗格清奇的写照。他的诗歌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情状。无论是苍茫的夕晖、回归的燕子,还是踏踏的马蹄、或者飘零的花片都能激荡诗人的感受神经,成为诗人情感的负载体。这些不仅表明了潘焕龙对自然的爱恋、对个体生命的体恤、对生活的热爱,也证实了他“诗格清奇、性灵温润”的诗学观点。清奇格调的诗歌与美文应出自清奇格调的美的心灵,这些都给予了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潘焕龙充足的营养,练就了他于宦海沉浮中坚强生活的意志力,培养了他独有的文化鉴赏力。
潘焕龙的诗歌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鄂东地域文化的窗户。从外在形象看,鄂东尤其是罗田山川秀美、奇峰异景、清流泻注、茶香栗美,给人一种清丽爽约、心胸畅快的感觉。从内在精神讲,这片土地由于山川林立,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反而犹如一口幽深静谧的古井,充满了神秘色彩。在我看来,罗田一直都是一个历尽沧桑、沉静温婉、气质淡雅的女子,她自然山水条件的得天独厚、人文历史的浩淼深重成就了潘焕龙诗歌的与众不同和独特风姿。在他恬淡与自由的表达里,孕育着浓郁的深情。他的诗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百姓的关切之情,一是对家乡山水的怀念之情。
看他的五绝《避难》:
避难仓皇际,攀岩挈小溪。相依如共命,奇冷不胜凄。
似鹤偎松睡,如乌少屋栖。万山深壑处,兀坐数鸣鸡。
潘焕龙之所以称为一代“诗人县令”,正是他在诗歌里寄予了他对百姓的深刻悲悯和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在这首诗中,他描写了避难灾民的流离失所和悲凉命运。在“仓皇”逃难之际,没有和平的生活环境,只有“攀岩”到山中的“小溪”边,“相依共命”,山中“奇冷”,生命凄凉。然而,任何生命都会找到自己的温暖,山上有“松”,那么就像“鹤”一样伴随“松睡”,山中有鸟,就像鸟一样栖息在树上或者水边。在“万山深壑”之中,数着“鸣鸡”,坐到天明了。这首诗仿佛在写避难,但难道不是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缩影吗?人们无家可归,颠沛流离,只有在山中的松和小溪旁艰难度日,等待着没有目标的凄清的命运。这种家国情怀对潘焕龙坚毅的文化人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赋予他诗歌中浓郁的关切之情、爱民之心,体现了他为官或为诗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如果说潘焕龙的悲悯诗歌表达了他对百姓的关切之心和人道主义之情的话,那么在他诗歌中家乡文化的体现就是诗人的心中精神性的符号,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幅幅鄂东山水或者罗田山水的写意画。这些诗歌写得生动形象、细腻真切,有的深入浅出,有的借物抒怀,无一不体现出他对故园山水的浓郁之情。看他的《晚游光州湖上亭》:
烟波万顷夕阳沉,雨后登临思不禁。飒飒风帆频过眼,寥寥人海几同心。
野凫浴水知春暖,画舫围桥待客寻。俯仰乾坤无限阔,新诗掉首自长吟。
在这里,诗人的视线从“烟波”和“雨”中看到了“夕阳”的西沉,由近及远,从“过眼“的“飒飒风帆”看到了“几同心”的“人海”茫茫,由高及低,人间虽然有“野凫知春”和“画舫围桥”,但他的眼光却在“俯仰”“无限乾坤”,他在追寻“几同心”,只有自吟新诗,也许从诗歌中才能找到生命的归宿。这里,我们似乎看到,潘焕龙置身于风雨后的夕阳里,水天相接、烟波弥漫,似幻似真、渐行渐远。只有知春的水鸟和过眼的风帆与之陪伴,他已经分不清自己在湖中还是在天空了。此时,除了俯仰天地,吟诗抒情还能干些什么呢。作为诗人的潘焕龙只有在清澈的湖水中才能看清自己的真容,才能在俯仰乾坤之际体会到生命的灵动。大别山的山水是潘焕龙的灵魂牵挂、精神皈依,潘焕龙的诗歌也为家乡的山水夯筑了思乡的基石、披挂了人文的彩衣。
总之,诗人县令潘焕龙是明清时代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历史研究所绕不开一座桥梁。是鄂东文化、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链接的一条精神纽带。他的诗歌里渗透的诸多文化信息既具有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有作为一代“县令”的悲悯情怀;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慷慨激扬的语言和闲散性灵的诗情始终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他思想上的矛盾使他在仕途上几经波折,但他一生的家园情怀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他的诗歌,呈现出一幅幅气象万千、飘逸神韵的大别山山水画,全面勾勒鄂东地区传承久远、淳朴自然的民俗画卷,也彰显鄂东民众朴实谦和、豪爽干练、坚忍不拔也轻灵飘逸的精神气质,从而成为了一张宣传鄂东文化的靓丽名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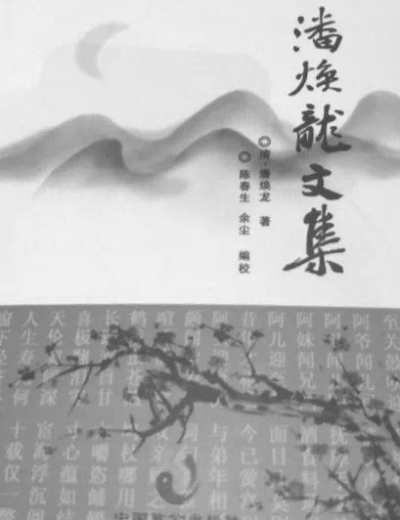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