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焦同仁先生认识,拜托我母亲在延安时期的战友温济泽。20世纪50年代,温济泽担任中国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焦同仁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1957年,温济泽被打成右派,行政级别由九级降为十四级,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教书。焦同仁也被打成右派,他的结果更惨──开除公职,送去劳教。右派问题改正后,他伤心了,不想回原单位,就跟着已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的温济泽去了该院研究生院,在公共外语日语教研组当组长。当时,母亲问我想学什么语种,我说,日语汉字多,感到亲切,就学它了。于是,老温把焦同仁引入我家。
大约从1980年底到1981年夏天,焦老师冬天披着棉猴儿、踹着大雪,夏天撑着一把油伞、冒着大雨,每星期晚上来我家两次,雷打不动地教我日语。我用新买的录音机录他的日语发音,鹦鹉学舌。他说,用我给你的教本速成你。这个教本只有1500个单词,但在半年内我把基本语法和惯用型都告诉你,今后你就可以自学了。1981年冬天,我参加了一个日语三级程度的考试,得了53分。1982年秋天,我在同一个考试中考了75分。这个分数是当时的大学本科公共外语毕业的程度。
焦同仁总爱戴一顶鸭舌帽。他个子高高的,身材瘦,皮肤老粗,颜色偏黑,皱纹很多,恐怕与他吃过苦有关。他在授课中经常批评我,说,你怎么不爱张嘴呀,不张嘴能学好外语吗?还说,我挺喜欢你,邋遢,散宕,没什么心眼儿,但对做学问的事还蛮执着。若干年后,我和他的联系不很紧密了,一旦相见,他便说:“你整天闷着头想什么呢?也不来看看我。”
焦先生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传授加漫无边际的神聊。他会背孟子、陶渊明、杜韩、欧苏等许多人的文章或诗歌,穿插在讲学中。有一位与我一块听课的经常骑一辆摩托车的学生,被焦老师起外号“摩托”。这个“摩托”说,老焦太能神聊了,我要测试一下他的日语功夫。后来,“摩托”对我讲:“确有两下子。对焦老师你得套他,能套出好多你不懂的日语知识。”但是,有些话焦同仁是不会跟“摩托”说的。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他一边教日语一边对我讲了他的人生遭际:1957年,焦同仁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到北京的大专院校采访鸣放情况。他听了“六教授”的发言,觉得不错,回到单位逢人便宣传。反右开始后,有人把他的言论反映给领导,领导找他谈话,叫他交代思想,他就一五一十地向领导汇报,如何如何地赞许“六教授”的发言……焦老师对我说,我就吃亏在嘴上,竹筒倒豆子,自己把自己说成了极右。是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黄埔一期”的学生讲,焦老师很幽默,在课堂上常说笑话,别人大笑,他只呈现收敛的微笑,眼光中露出看透世情的意味。于是有人猜测,吾师莫非隐有“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历史包袱”?然而仅仅是一掠而过的想法,毕竟不便细问。
劳教回来后,他没了饭碗,自己报名考上商务印书馆招聘的社外日文校对,一个月还有一点儿微薄的收入。“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五类分子被遣送回吉林长春原籍劳动。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多数人都姓焦,他的辈分大、人缘好,村民还算尊重他,看他不会干活,照样给记不错的工分。我问,那你能干什么?他说:“会撸老玉米豆呗。”我想起廖沫沙在“文化大革命”中游街“坐飞机”时还吟诗:“满城争看斗风骚”。焦同仁在逆境中大抵也会是这样,不悲愤、不绝望,始终悠然乐观的样子。
当时,焦同仁的家和我家只隔一条东长安街,都离天安门很近。他授课的地点不一定在西八间房(社科院研究生院所在地),而是经常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或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他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在校研究生,一种是他纠集来的像我这样野路子的学生。稀稀落落七八个人、十来个人聚拢在教室,与焦老师凑趣。大家一块上课,一块参加闭卷测验。我遇到不会做的题,就抓耳挠腮、左顾右盼。他溜达到我的课桌旁,倾头看看,然后回到讲台,一边神聊,一边写板书。学生在考试的过程中还能听听课,这也是一种享受。我突然明白了,题已经会做了。
焦先生授课不喜欢照本宣科,而是喜欢讲一些日本历史上文学或语言的故事,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历史上文学或语言的故事。有一次,他提到一个日语单词“一夜妻”,问我什么意思。我回答:“妓女。”他说:“引申义包括妓女这个义项,本义则指织女星。”于是便背诵秦观咏七夕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情况,焦师母在他被遣返后,并没有跟去。焦老师非常自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喜欢这首词结拍两句脱略临别总是黯然的传统写法,而陡作拗转之笔,既是离别时的深情相慰,更是坚贞不移的爱情誓言。焦先生还富于哲学意味的人类意识。譬如,对学生进行汉译中造句训练时,把“这些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写在黑板上端。我对过去听他授课的具体内容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但这句话的日语表达,却始终牢记心头。
乐于助人也是焦同仁的特点。他的日语是在伪满洲国学的,我的另一位日语老师爱新觉罗·连湘先生的日语是在东京学的。连老师是清朝末代肃亲王的孙子,川岛芳子的侄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出身不好,不受重用,后来不知怎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黑龙江省北安监狱服刑。平反之后,没有工作,焦同仁以特长取人,把他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焦和连的日语发音有些细微差异。焦老师的耳朵很灵,有一次我母亲给他介绍了一位也懂日语的朋友,两个人一对话,焦同仁便说:“你的日语是在华北或华中学的,比在华南学的日语稍好一点。”说的一点儿都不错。
焦同仁翻译出版过不多的日本文学作品,偶尔写几首旧体诗词在报刊上发表,自娱自乐,但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学术成果,是一位教而不著的日语先生。他擅长教学,在没有电脑的时代,经常没日没夜地自刻蜡板油印出自编的教材分发给学生使用。他去世后,我每次翻箱倒柜整理书籍和材料,都能看到他当年的字迹──我没有筛汰这些东西,仿佛还能嗅出油墨的馨香。他最终刚刚迈过坎儿,在74岁那年,死于监考——话还要慢慢说。
焦同仁退休之前职称为副教授,他找温济泽希望解决职称问题,但没有办成。他曾跟我叹气道:“老温这个犊子……”抱怨温济泽在外面敢于直言,不怕老虎,但在家里却天真地不会呵护自己的属下。然而,研究生院返聘他为教授继续执教,使他从65岁直到去世,一直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他认为自己耽误了20余年,工作做得太少,还要拼一把老命。1997年春天,他在课堂给学生监考,心脏病突发,被送进西八间房附近的医院抢救,很快就没事了。他不听劝告,又返回学校处理考务,在奔学校的路上第二次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
凡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念书的学生,无论第一外语是日语,还是第二外语选修日语,都是焦同仁的弟子。教授我中国古代文学的董乃斌先生,与我同出一师。这是我在焦同仁追悼会上知道的。我想,那个年月没有心脏搭桥技术,倘有的话,焦老师还会有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吗?也许我与焦先生、董先生还能在一个饭桌上碰杯呢!
董乃斌曾给我发过电子邮件:当年既可学日语,也可学英语,我选了日语,有幸跟焦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去世,我还参加了追悼,见过师母。焦老师,东北人,自幼通日语,精通古日语,所谓文语,但我们水平太低,不大懂。他教书认真,改作业仔细,待人客气,非常友善,又非常谨慎小心。我内心非常尊重他。你如跟他有交往,希望能写出……
是的,焦同仁的学生们早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对春催桃李的师辈,应该在记忆中把他们点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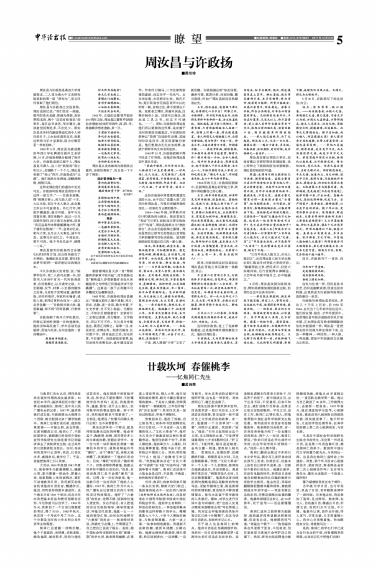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