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同窗契友,二人同为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仅仅录取了他们两位。
周汝昌与许政扬之交谊甚笃,周汝昌回忆说:“我们住在一间屋,窗外即是未名湖,那湖光塔影,是世界闻名的,两个‘自觉有些抱负’的青年,每日品书谈艺,考字徵文,愈谈愈觉投契处多,不合处少。那实在是求学时代最值得追忆的令人神往的日子,人生如有清欢至乐,我想这种欢与乐才是真的,因为它像苦茗一样有回味。”
1952年5月,周汝昌先被成都的华西大学电聘前往做外文系讲师,10月,许政扬则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许政扬是浙江海宁人,周汝昌是天津人,这二位“典型的”南士和北人,却调换了一个个儿,周汝昌来到了“南土”四川,许政扬成为“北漂”。他们虽然分处两地,却鳞鸿频数,相契日深。
这种友情在他们的通信中处处可见。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往读东坡集,得‘相携石桥上,夜与故人语’十字,大以为佳,而古今无人称之,此全集之所以不可废读也。书已付丙,两纸字劃遒劲,极为可惜。昔年与兄同窗乐事,常往来胸中,犹记一日兄自图书馆归,时方读玉台新咏,语及‘吴迈远每作诗得意辄擲地大呼,曹子建何足数哉!’一节,会弟亦忆此,相与大笑,以为古人天真处,诚不可及。此事兄亦必忆之。今玆此乐,更不可再。唯于书札往返中,稍得一二耳。”
周汝昌曾和许政扬约订合撰《水浒》详简计划,而且很快做完了头两回。他俩还发过宏愿,要为《东京梦华录》作一部详密切实的笺注本。
不久许政扬又发奇想,说:“除梦华注外,我二人尚可合撰一书,即取宋人诗词中有关一代风俗典故者,合而笺释之,以为读宋之助。大至朝制、仪节、时事,小至器用服饰之沿革,凡有助于发明诗意,通贯辞指,词书所难详,专家所未喻者,咸收入焉,则考订赏析合而为一,读之必多佳趣……”许政扬兴致大发,遐思联翩,却不料“肝疼甚劇,只索停笔”。
许政扬到了南开大学任教后,肝病以及神经衰弱一齐向他袭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学术活动无法延续,苦恼与无奈,全写在他的一首自嘲诗中:
数卷破书饱蠹虫,药瓯常满箪瓢空。
材无所用其能寿?诗久已穷未便工。著帽应门遮鬢乱,舍筇步砌博颜红。心如枯卉春难绿,只把东风当北风。
1963年,正值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际,周汝昌以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诗所用的吟、深、阴、寻、林韵脚步雪老遗韵,其一曰:于君谁可接讴吟,异代非关怅望深。劔匣不留奇恨远,鼓摊长玷墨花阴。数家弱笔争腾笑,一往高风之梦寻。犹有此心殊未死,为传神采託书林。
周汝昌以此诗韵向许政扬发出邀约,诗很快寄来了,而且是一下子步了两首:
读步雪诗勉和一章摩诃残拍费沉吟,匣剑囊琴怨自深。鹦燕唤回堂下梦
淳于棼寝,堂东廡下
笙歌催送隙中阴。沾泥墜穗尚堪拾,印雪飞鸿何处寻。束子补亡浑好事,要传遗韵照诗林。
再步稗中贤圣足悲吟,一息韶华累恨深。大觉后方知大梦,分崩时乃惜分阴。狩麟绝笔元无续,论马解人或可寻。会有玄珠沉赤水,凭君钧取入笺林。
庄子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此语或可以赠稗圣后四句意属解味兄
紧接着周汝昌又步一首“得照蕴再步新章不觉兴起”,而许政扬也是“解味道人步雪新篇有圣处从来题恶语之句吟唱三叹强起学步不觉蹣跚”。这真是一段千古奇题不可多觏的文坛趣事佳话。
1965年初,许政扬向周汝昌建议:“弟曩议取宋人集中典制、风习、语言、名物,逐一论说,勒为专著,于文史学者,当不无小助益。兄颇许之,不知尔后曾留意否?史家有卄二史劄记诸書,功力精深。文字独无,所以不可不作。兄与其为专集选注,莫若汇而释之。每事一目,有说有论,有辨由考。短者百餘言,长可数千字。则有选注之功,而无其累,不亦善乎。如陆游临安春霁,起句世味年来尊似沙,谁令骑马客京华。作客何曰骑马,二字注家殆皆视同虚辞,而实关乎一代风气。且全诗旨意,亦自两字生发。钱氏不知,竟引简斋杏花消息雨声中以比听雨一联,皮相之论,真不啻谬以千里。虽夏老之博识,其唐宋词选,注释亦间有小误。自馀可以無论,故此虽工具之书,而实不可缺也。……”。须知,许政扬和周汝昌他们所以要做的这件事,是有感于当时的某些空疏宽泛、不切真际的那种以“简明”自诩的作注释,其间时时似是而非,甚至讹谬触目皆是。他们想做点扎扎实实的事,妄欲于那种学风文风有所匡济。
1965年10月,许政扬因病不得不住进了疗养院。而他在给周汝昌信中再次申述:
“弟病中静思,今代学林文苑、人物语言(以至里巷琐闻、一时风尚),乏人记述。兄交游既广,见闻復富,若有馀晷,不妨随时疏录。积久渐富,略加删辑,即成专著。此亦一代文献,于后世学者,谅非小补。”
这份许政扬非常看重和冀望完成的大业,由于自己“连遭大故”,即托付给周汝昌。可惜后来随形势的变化,一切皆化为云烟而荡尽。
1965—1966年间,学界展开对《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发文“考证”《兰亭》,说帖连文带字统统出于“伪造”,周汝昌视郭文为“绝世妙文”,并由此引起驳辩之激情。周汝昌把自己欲写文的想法以及背临兰亭的趣事写信告诉政扬。谁知那政扬回信却道出自己的一番心意:
味兄:奉书展读,病室生春。禊贴而能背临,可知寝饋极熟。想見掷笔四顾,踌躇满志,当时意气,逈非寻常。如此佳笔,漫弃可惜,莫若付弟,时刻对翫,聊当指授,何如?……兰亭弟向所觏,如落水本等,皆石本,且贾人索价,类非措大能办。至勾填本,则绝未经眼。乍睹眼为之明,神为之清,不啻金篦刮目,灵醐灌顶。张好好诗,忆是伯驹先生物,曩在燕京展出,幸一寓目。初不知曾有翻印也。见示新印诸本,为之垂涎三尺,病榻与世隔绝,寡闻至於此极,失之交臂,良堪叹息。……弟不能字划,每观兄书,不胜临渊之羡。候病躯小平,拟发愤三年。右军书兄宜撰为专论,未可但作随笔。夫曹氏说部,既已专擅矣,今復有此著,艺苑好事,将被一人占断,令人羡殺妒殺。……书成必先借读。弟思今代世说之作,其人不特须闻见广博,必善于行文。微兄,其谁能任?……
于是,两人围绕“兰亭”又有了新话题。许政扬提出的“如此佳笔,漫弃可惜,莫若付弟,时刻对翫,聊当指授,何如?”周汝昌回信自然颔首应允。
玉言:得札喜甚,笔意极飞舞之致,安得谓之心手不应?所摹兰亭,亦候掷寄。昨日院中病友出外,託购得米芾拜中岳命诗一卷,为之欣喜欲狂。满纸逸氣,类不食人间烟火。萧斋长物,只有郑振铎编宋人画册一部,清明上河图一卷,得此便覚暴富。昔人所谓乞儿啗猪脂三升,自谓穷奢极欲,竟与何异?可发一笑。神龙兰亭,上海天津皆不可得。即精装亦罄。……弟近岁卧病,颇恨寡闻。不知数年来新印名迹墨寳,都有几许?暇日希逐一示知,当令人物色之。院中好书法者甚众,有持宋高宗、赵子昂诸人千字文求解者,且不止一人,不悟疗养院乃成三家村,打针吃药之余,“都之平丈我”,作訓蒙老冬烘,真六十年代新奇事也。
1966年的元旦,许政扬回到家中,见到周汝昌寄去的背临兰亭,欢喜中再袒露自己的心愿:
玉言:新年疗养院放假,回家即见兄所书禊贴,惊喜欲狂。墨韵欲流,笔致飞动,虽起山阴于地下,亦必称善。乃来书尚以未能尽合为言,弟固以为微妙之处,正在微有不肖,苟笔笔如脱印板,则褚摹具在,何必更有周摹哉。跋文备见风流蕴藉之致(及吾儕意趣、情谊),而谓可以截而去之,真以老斧为古董商矣。当适付装褫。纸端留俟吾兄再跋,弟岂宜便为狗尾。首本既尤勝此,则何妨并以见赐,盖本庵主人不计纸质,而得隴望蜀,贪求无厌,亦禀性如是,毋庸诧怪也。且弟有二女,若止有一本,将来当授何人?……
原来,许政扬的这封信是回应周汝昌在背临兰亭后缀的一条跋语,其云:
平生第二次背写兰亭文,行款结体多不能确记,信笔所之,唯冀用筆情神之间或能有一二合处耶。斧兄知我曾写一次,欲索观未敢即付,恐见笑。今偶重书亦未胜初写,互有得失而已。时一九六五年之十二月,天大寒,呵凍草草,非敢以此言翰墨,聊用寄情于老友而已。解味弟顿首兰亭以二十八行著称,今写落况脩短随化终期於尽等句,致成卄七行,咲枋也。又记。
这时的许政扬,迷上了名家碑帖墨迹,这是他养病休憩的最佳方式。他告诉周汝昌:
日前病友,又为买得柳公权书兰亭诗及苏东坡书黄几道祭文,苏书笔法,似多出魏碑,视此,则包慎翁辈真土苴耳。柳之墨迹,逈与常见诸碑不类,且多用侧锋,特为奇妙,使弟爱不能释。所费不能数金,而高兴者累日,何其廉也。唐摹兰亭叙,即当去函购求,计书店必有善策封寄也。兄但择其佳者开示,不论真行藳草,凡宋元以上,价不甚贵者,若上海人美所印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张旭古诗四贴之类,动需百数十金,则非酸儒辈所得染指矣。……弟入院已逾两月,而了无起色,则冰冻三尺,元非一日之寒。据医生谓……嘱令少看书,多自娱。今备画册、法帖数帙,时时对翫,或亦养病之一善法乎。……
周汝昌自寄出背临兰亭后,却没有像以往那样很快收到回复,忧心忡忡之下政扬的回信来到案前。周汝昌即刻回信写道:
照蕴:未得书日稍久疑前纸已付洪喬,微有惜念意。盖假古董虽不真而作伪老味亦未嘗为他人作,是以有惜念意。况再作不知何日復有兴致,且作亦未保胜前纸故耳。展诵来笺,不觉大笑。造假古董之惯家必得一爱收假古董之“古董商”,始为相得益彰。云付装池,若果实行,务嘱稍接幅后纸,以俻好事者下笔。原纸馀尾必须请兄题记,兄若但存一“续貂”之谦念而不之加墨,试思此一纸尚有何意味可言乎?岂不真应作假古董而烧却乎?至恳至恳。其第二本〖即误为廿七行者〗偶令一行家寓目有“三百年来无人能为之,亦无人能识之”之语,其“三”字是塗去后改,亦不悉原作“几百年”?见此赞语未免洋洋得意,颇自了不起……
“三百年来无人能为之,亦无人能识之”,出自周汝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仁陈迩冬对背临兰亭的评语:“敏庵背临兰亭,把玩多日,幻觉大似褚河南,后乃发现得永禅師法。三百年来书家不能为之,亦不能識之。”
5月份,周汝昌收到许政扬来信,得知其病情加剧而提前出院,但其仍念念不忘谈书论学:
……弟在院失眠愈剧,漸至终夜不能交睫,同室三人,皆有此苦,往往彼此干扰,故商得医师同意,提前出院。……回家后,医生仍不令观书。借得故宫周刊数函,以伴晨夕。其中所载宋人书简,无不妙绝。蔡襄一帖极可爱。蔡京墨迹,曩于故宫见其楷字,今復覩所作行书,甚佳乃若此。元度书与京笔法全同,妩媚略逊而挺秀则过之。又元鲜于伯幾草书一帖,亦极神韵飞动之致。凡此殆皆兄所寝馈,弟则乍觏,遂瞠然叹为观止矣。兄闻之,得无为之喷饭乎。
5月30日,许政扬写下的这封信,内云:
味兄:前书草草,秪以报喜。——向来报喜者,必报人之喜,弟则报己之喜,固已荒唐,乃老兄不以为恠,亦因之大喜特喜,方賢郎抱恙,嫂夫人觅医生,灶突无烟,箪瓢猶空之际,提腹据案,而谈敝帖。此事之尤滑稽者也。顾不自知痴,尚以嘲人,何其蔽溺之深!昔人谓穷秀才冻死通衢,衣带上有喜雪诗,正堪为吾辈写照。……寄帖只是捲封,稍有折痕,是为美中不足,而无剉筋伤骨之痛,尚是不幸中之大幸。弟思苟能中间实以木轴,無则代以废纸卷,必可保持完好。惜去信过迟,竟已无及。然弟已喜出望外,当时无暇计此。拆封眼花缭乱,手足无措,把卷而立,为之四顾,值室中孑然,莫得与语,乃亟抽纸作书报兄,冀能分喜,抑亦饮水思源之意也。又取唐摹兰亭与周摹对看。风神韵致,竟是逼肖〖不在逐字逐笔〗,使弟目瞪口呆,汗出如浆。急掩而藏之,恐似延津神物,化龙飞去。当严闭窗户,焚香独坐,凝神揣摩,以求是中金针妙诀。觊十年以后,更有许摹本出世云。陈陈鑑本、薛道祖本、天曆本等新印者称何名称?三希堂本甚难得否?又兰亭墨迹彙编,价如不甚昂者,谓在十元亦思罗致之。所举北魏碑以下刻,极感兴趣。盖弟全以卖浆求益,多多益善。饥不择食,言之可哂。不富饱人能知饿人之腹否?所得圣教序乃文物简装本,弟元有大雅集王书,而此本尤觉可爱。惜体力不任,否则,定当临他十遍八遍耳。
信末,许政扬写下一首诗,诗云:
行年四十学塗鸦,走笔殭龍復死蛇。縂为欧孙两本帖,垂涎三滴乱如麻。
信札与往常一样,仍旧是谈书论艺,仍旧是幽默诙谐,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成为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最后一封信。
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信札,多达几十乃至上百封,自1952至1966,在长达十几年的书信往还中,他们的友情、抱负、才华尽显其中。虽然周汝昌写给许政扬的信札片纸未留,正如周汝昌写给老师顾随的信札未能留痕一样,周汝昌一直把师友的书信视为珍宝保存下来,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品德,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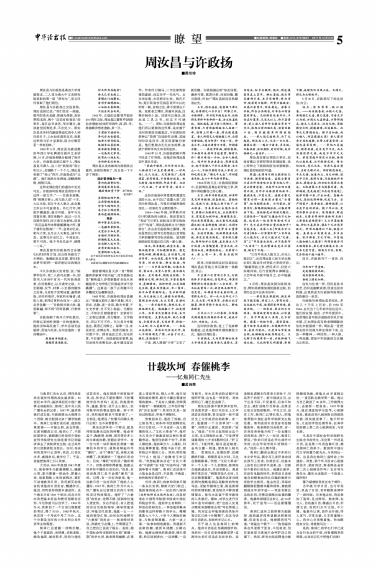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