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的作家当中是有幸的,参与战争对于培养我的文学理想和战争理想、人生理想至关重要。战争经历是我宝贵的资源。
他一直在创作领域中寻求值得自己攀登的制高点。无论是写《历史的天空》,还是新作《对阵》,总结起来,徐贵祥觉得自己的创作得益于曾经在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生涯。他研究了很多革命战争史料,读了很多军史、战史、人物传记、回忆录,积累、沉淀、发酵,形成了对抗日战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面旗帜下,出现了国共合作、全民皆兵的现象。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胜利,既有国际力量的支持,也有国民党军队的牺牲,更有全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牺牲和奉献。”徐贵祥很早就关注抗日战争,他总觉得很多抗战题材的作品,对人性的开掘不够深刻,不仅没有把我们自己写好,也没有把敌人写好。“人类在进步,文明在进步,文学也在进步。只要我们向前一步,回过头来就会发现,刚刚走过的道路长度不够,高度也不够。”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品过去没有写好,现在仍然没有写好。
“我应该在这个领域中有所建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徐贵祥说,他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有太多的情感要表达。作为军队作家,不仅为文学负责,也为社会负责;不仅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不仅对今天负责,也要对未来负责。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家叫国家,有一个姓叫百姓,有一扇门叫国门,有一个神叫精神。”小说中章慧创作的歌词,也是作品的主旨。
徐贵祥:文学担负着启蒙滋养的作用,所以我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家国天下、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很多关于抗日战争的信息储存在我的记忆深处,不用刻意温习,遇到恰当的气温,听到一段音乐或者看到一片色彩,会条件反射进入到某一个情境中,记忆迅速生长,人物、线条、色彩全都往外冒。我经常会感到有神来之笔,有时会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候也会气得暴跳如雷。写作时笔下的人物浮现在面前,我看着他们言谈举止,看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唇枪舌剑,活灵活现。
中华读书报:听说《对阵》最初叫《第一身份》?
徐贵祥: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中国人,我希望大家增强国家意识。先有国,后有家。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国家利益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后来改为“对阵”,这里有多重意义,指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对阵,也是指统一抗战时期的两个阵营合合分分,也象征思想的对阵。
中华读书报:两次上前线,一定有特殊的感受?
徐贵祥:1979年我还是新兵,就上了前线,立了三等功,亲人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1984年,听说部队要组建侦察大队到云南,我马上找到师政治部打报告要求到前线去。我的决定把父母吓得够呛。父亲是农村的公社书记,就我一个儿子,听说我要到前线,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备受煎熬。父母是共产党员,从不迷信,但是我去了前线后,他们在屋里供了一尊菩萨像。
我回家后,父亲高兴地放了鞭,母亲端了热水给我洗脚。我说为什么洗脚?母亲说是家里的风俗,亲人从外面回来一定要洗脚。我心里纳闷,也由了母亲,而且她一定要坚持给我洗脚,用手捏我的脚趾。后来姐姐告诉我,母亲是借故搞清楚我的脚是真是假。因为村里传说我的腿被打断了。捏我脚趾,是想看看是否通着电线。我听了后大笑,笑着笑着,泪水滚滚而下。
中华读书报:那段时间,您的写作状态如何?
徐贵祥:那时写了《大路朝天》《走出密林》《小河远去》《潇洒行军》《请跟我来》。关于那一时期的写作,有评论说我像“战场上的行者”。我的作品集中在当代的战争小说。我在中国的作家当中是有幸的,一是新兵的体验,参与战争对于培养我的文学理想和战争理想、人生理想至关重要。这一阶段对我的文学成长之路来说,主要是增加了我的感性认识,培养了我的形象思维;二是作为基层干部去云南,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培养了我的理性思考,关于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个体生命与整体命运等等思考。这段时期的经历,给我的作品带来的底色基本上是阴郁的、黑暗的、低沉的。因为是在密林里,作品中只要我写到阳光,就会有大量的文字铺排、渲染、烘托。多年后再回头看,从我的作品中发现关于描写阳光的段落时,我会像局外人一样,似乎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惊喜甚至是狂喜。因为看到了阳光就看到了生命。
中华读书报:您所经历的战争,和我们常见的文学作品中的战争,有什么区别?
徐贵祥:真实的战争和想象的战争,当然有很大差距。第一,想象中的战争,是理想化的也是理性化的。文学作品只是用日常生活经验想象战争,真实的战争永远丰富得多,不管是客观的遭遇还是心理的感受,远远复杂得多。一个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作家和参加过战争的作家,笔下的战争永远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战争经历是我宝贵的资源。我可以在战争的记忆库里无限地开发。
没有战争经历的作家,笔下的战争会多一些审美的诗意。参加过战争的作家,笔下的战争带有刻骨铭心的痛楚和难言之隐。文学的人文关怀有四个层次:说事,言情,见性,显灵。比较好的作品,应该在这几方面都有所体现。你在战争上见到的人和事,不需要过多地修饰,原生态写出来就有现代感,战争中人性的荒诞、变态、扭曲、疯狂……我们所看到的战争文学,远远是冰山一角。
中华读书报:就读解放军艺术学院前后,作品风格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徐贵祥:战争对人的性格会发生影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他的行为方式,表达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我也有很多变化,从战场下来回到和平生活状态,尤其是到军艺上学,有一段时间很不习惯。因为在前线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基本处于不受约束的野生状态,不出操、不用学习,就干一件事,潜伏。那段时间人和土地基本融为一体,我甚至感觉自己的双脚,已经开始在土地上长根了,也可以随时在大石头上睡觉,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吃饭没有规律,也没有规矩,有可能用大盆子,就地蹲着吃。说话要大声,我在军艺是班长,经常想把同学们集合起来讲一通话。情感方式也不同,往往表达比较直接。
很多年之后我才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直到现在还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这么多年取得一些成就,创作上也些荣誉。经过“包装”,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但还有一些没改变,就是身上还有粗野和率性。尽管我假装很理性,很老谋深算,还是难免会露出尾巴。
中华读书报:但是这些似乎不影响您的文学观。
徐贵祥:我曾经语出惊人地表达我的文学观。我的文学观可以借两个故事比喻:一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作家就是小女孩,火柴就是文学,火光就是文学作品,火光中出现的烤鹅和奶奶,就是文学的理想;二是《皇帝的新衣》,文学就是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我有时候很理性,理性到狡诈的程度。有时候很不理性,不理性到傻的程度。
文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探索真相。作为个体是探索人的情感真相,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从社会层面讲,要探求社会真相和自然真相。文学还应该照亮、温暖、净化、美化我们的人生。一部好的小说,还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取决于作家的认识、认知和境界。写什么怎么写固然重要,作家在关注什么问题,对其价值的判断更为重要。作家是在精神领域里把脉。
中华读书报:“理性”或是“狡诈”?您觉得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徐贵祥:我很复杂。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比如我写《历史的天空》的时候,我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人;但是在写有些作品的时候,我是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我经常把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混淆。我进入创作状态时很“可怕”,有时会做出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不太明智的事情;我也有时候会感觉到委屈。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军艺的学习让我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思考战争观,文学观,有意识地提高了文学修养。真正的好小说是离心最近的小说,是真正从你的心里面流淌出来,不是外在挤压出来的、时代或社会需要的作品。我觉得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作品,有《高地》《特务连》等。《高地》写得非常快,因为有写作《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香》的经验和思考基础,作品中那些粗野率性的人物,和我在精神上有某种相通的地方。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这些从心里流淌的好作品,是否得到了社会和读者的公认?
徐贵祥:这里就涉及到文学生态。每个人对一部好作品判断的尺度不同,不同的时代判断标准也不一样。有些评论家不是将评论作为事业而是作为饭碗,有些评论家的文章让人看不懂,评价文学作品隔靴搔痒。他们更多地是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思想高度评价,其实作品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有时候作家本人也搞不清楚。
我对作品的内心期待和读者对作品的评价是否吻合,不好量化,也没办法量化。作家不能看社会的眼神,不能看读者的眼神,应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判断。否则,总想着去迎合时代和观众,就会丧失自我,永远会疲于奔命。冷水泡茶慢慢浓。
中华读书报:您近来创作状态如何?
徐贵祥:我最近在挖掘中国革命战争不为人知的资料,我以一双魔鬼般的眼睛发现。我相信这些资料比我们经历的以及从官方话语了解的战争真实得多。我感觉自己有神奇的力量,我相信我会写出很好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对语言有怎样的追求?
徐贵祥:我认为最好的语言是精准地、生动地、形象地表达。我判断语言的品质,第一要准确,第二是简洁,第三是生动。小说最好的形式是看不出形式,没有刻意结构,呈现在你面前的故事却很清晰;真正好的作品,是没有结构的结构,成竹在胸,内化于心。我追求人物个性鲜明,不鬼化也不神话,同样的解放军,《高地》里的兰光泽,《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都属于他自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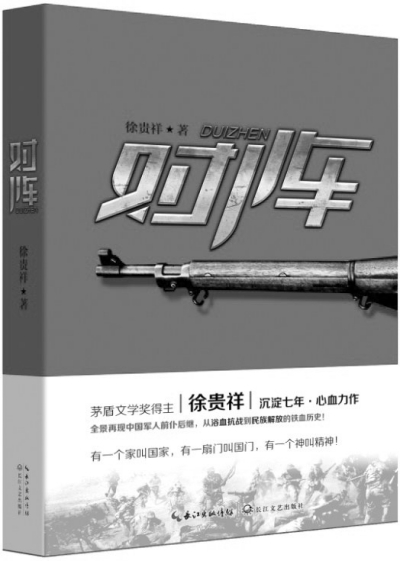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