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一本随笔集,看出作者对民国遗风的呼应。这大概也可窥见他的文学与学术之梦,在远去的韶光里,有爱意于斯,以此抵抗日益粗鄙的文风,也有生命中不能缺少的快慰。
《书林清欢》为唐元明先生的精心之作,除了读书偶得,还有诸多记人记事之文。出版之前,得以先睹为快,对于其精神底色有了诸多了解。全书语言自然、素朴,又多逸趣,陶情笔墨间,见出作者明达的见识。
我认识唐先生是在《胡适全集》的学术讨论会上,地点是在北大,那一次来了许多人,谈话间溢出相近的趣味。此后很快有了一些交往。现在算起来,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吧。印象里唐先生有一点旧文人气,书法和文章都有功夫,自然也喜谈文史,钟情旧迹。但他的恋旧,却无儒生陈腐之气,“五四”的忧患感也深藏其间,所以说是往来于新旧之间的文人。
那些年他策划了许多书,最用心的大概是学术文化类的。《胡适全集》《台静农论文集》《黄裳作品集》《钱穆学术思想史》《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等名家名作,都有他的心血。我猜想那些著作的编辑,也与自己的写作兴趣相近的。
安徽是个出学者的地方,近代以来,桐城派的遗风且不说,仅陈独秀、胡适、台静农、朱光潜等人,就给了我们不了的话题。唐元明先生的精神衔接在这个故土的深处,且又上溯晚明,在空阔的领域辗转自己的思想。晚清文化后来分化出不同路径,新旧之间,惟京派保留了士大夫遗风,又兼有西学韵致。这个路径的一切,后来受到重创,文风不得流转甚久。八十年代后,京派文化得以延续,深深吸引唐元明,读这一本随笔集,看出他对民国遗风的呼应。这大概也可窥见他的文学与学术之梦,在远去的韶光里,有爱意于斯,以此抵抗日益粗鄙的文风,也有生命中不能缺少的快慰。
现代以来,因为战乱之故,文化饱受创伤,淹没了本有的个人意识和精神独思,这在唐元明看来都是不小的损失。他沉浸在那些曾被遮蔽的风景里,既有补课的意味,也是追梦的选择。文人者也,倘不能广泛摄取人间思想,在学识与趣味间自塑己身,便也可能沦为思想的传声筒。我觉得在审美方面,京派的许多遗存都回响在他的世界里。苦雨斋间性灵之音,暗藏其间。唐元明对于学识与诗意兼得者垂爱有加,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冰心这些知堂弟子唤起了某种幽思,这一切,乃今天文坛不易见到的所在,他心里喜爱这些,由此进入历史的深处。那些远离时风的文字,也成了他信仰里的一部分。
我们的作者是个追踪学术根脉的人。自幼便染有儒风,“家族中尚有崇文敬儒的传统”。“文革”厄运使其深感读书的重要,后来的职业选择看出自己的喜好。我从其文章里感到,不喜时髦之书,厌恶浅薄之作,于前人的厚重之文中得不小的自在。这和京派的许多学人有些心灵的相通,趣味与爱好间散出知人论世的文气。
唐元明的文章属于书话体,不都是宏阔之论,长的不显张扬,短的也恰到好处。文行于旷达之处,止于平静之所,多少有点无拘无束、怡然不倦的古风。这既来自书本的暗示,亦有读人的收获。他造访过的前辈学者张中行、黄裳、舒芜、吴小如、袁行霈诸人,都是好的文章家。沿着这些文人的语体,找到了明代与晚清的文学体例,诗趣、学识、掌故连为一体的时候,文章便有了诸多意思。以知堂的观点看,唐先生属于喜欢言志的文人,对于载道的文字,有诸多隔膜。每每读到古人性灵小品,见其笔墨间的飘渺之思,便有欣然相识的冲动。他阅读张岱、废名、汪曾祺,都有亲昵之感,好似进入清新疏朗之地。这些都不是文化的主流,但却可以校正文明里的旧病,那些远离道统的诗性,才是自己内心神往的所在。
随笔之体,千百年来进化缓慢。吕叔湘先生说:“从先秦以后到白话文学兴起以前,中间这一千年多年里,散文文学是远远落后于韵文文学的。”中国的好文章,六朝是一个阶段,宋明也是发达的时候。“五四”有了新的变化,成就最高者,乃周氏兄弟。周氏兄弟风格不同,又形成两派,用汪曾祺的话说,诞生了峻急与闲适两条路径。作家懂得文章学之道的不多,惟学者用心于此,可惜实践者寥寥,遂显得有些空谷足音,甚为孤独。唐元明写这类的文章,内心有静的一面,寂寞也是有的。但其间所得,岂是寻常者可以明白?耕耘其间,才知道汉语的写作,有无限可能,以学理为衣,灵思为体,智性为根,便可往来古今之间,游走东西之界。这是“五四”好的传统,唐先生得之而又乐之,我们于此也可以分享一二。
章太炎先生以为,文化之事,其兴起多从民间开始,自下而上,才有可能繁荣起来。唐元明深味于此,想来他在自己的路上,总能唤来更多的同道。私以为会有更多的人会回到自己的园地,深耕精作,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由此也可以相信,周氏兄弟的文章之道,总能延伸下来,智者之音,有民间的传递,终究是不会衰亡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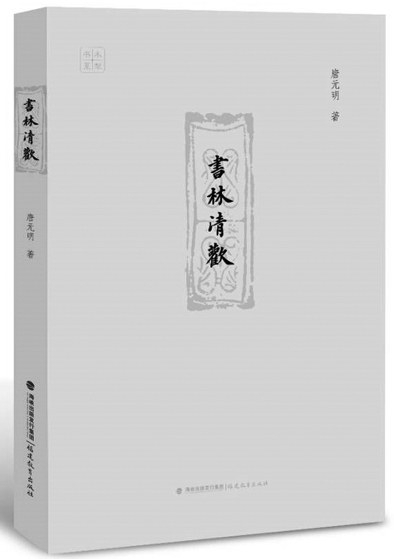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