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是一部与萨义德《东方学》齐名的文化研究经典。笔者拿到这本书的中译本时,心中怀着敬重,又掺杂着忧虑:之前阅读此书的英文本时,笔者苦于其表达晦涩和思维跳跃,一度试图放弃。对于缺乏文论训练且稀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阅读经验的笔者而言,阅读《帝国之眼》的过程犹如眼科手术:痛苦之后别有洞天。
读罢全书,笔者对《帝国之眼》的两个观点颇有感触。第一,以分类和归纳为己任的博物学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总结,而是构建存在巨链和制造新知识的框架。根据《帝国之眼》的分析,18世纪博物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关系密切。后者不仅提供物质支持和商业动机,更重要的在于提供动机:系统化整个世界。正如普拉特所言,“自然的系统化,不仅表征一种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欧洲话语,而且表征一种关于非城市世界的城市话语,以及一种关于无文化修养农民世界的有文化修养资产阶级话语。自然系统被投射在欧洲边界之内及其之外”(第45页)。换言之,欧洲的地方性的知识由此转化为世界性的常识。从今日看,这项事业极为成功。离开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术语体系,我们甚至无法定义我们身边的一株小草。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制造一个可控和有序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纳入原料、产品和市场的循环而甘受奴役。非欧洲地区沦为了一片波澜壮阔的自然,一群等待英雄的人民,一个等待拯救的大陆。这种描述在凸显了“欧洲-英雄”这样一组概念的同时,也将“自然”和“土著”打入了客体的深渊。自然只是生产英雄气概和原料的场所,而不像拉图尔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主体性。至于被征服者,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没有历史,只是在等待着发现者的到来;他们的历史也只是在不自觉地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服务,负责提供劳力和市场。“美洲必须被改造成一个工业和效率的景象;其殖民地人必须从没有嗜好、等级、品味、现金,而且懒惰、无差别、不洁的民众,被改造成雇佣劳动力和宗主国消费品的市场。”(第196页)他们的“史前史”和“历史”全然断裂,其原生的历史意识和身份认同被全然抹杀并被烙印上刻板印象。正如普拉特所言,“在西班牙语美洲,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对懒惰的判断与旅行者具体见证的劳动密集型的奴役完全兼容”(第196页)。懒惰和主观能动性的丧失如同滤镜一般,只保留特定的负面印象并深嵌入旅行书写之中。伴随着西欧的经济扩展和文化霸权,这认识也随之扩散,并最终成为了常识。
第二,帝国主义的修辞术塑造了知识生产。在《帝国之眼》中,普拉特辨认出了旅行书写常用的三种修辞:风景的审美化、意义的稠密化、观者和对象间的控制关系。这三种修辞策略,不仅是文学性的,更是认知性的。重叠的修饰在遮蔽了描述对象的同时,也混淆了现实和写作者内心投射的区别。可怕的是,正是这些充溢偏见的游记描述,构成了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认知的底色和基本知识的来源。简单说,当我们谈论“非洲”或“拉美”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景象是一颗洋葱:由各种欧洲人的俯视印象层层包裹且令人伤心。如同欧洲的探险家自诩发现了美洲,他们的旅行书写也自以为发现了美洲风景的审美意义。
笔者非常欣赏中译本中的一个用词——“看客”。对于几代中国读者而言,“看客”一词的第一解释必然指向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国人。类似鲁迅笔下的“看客”,普拉特笔下的欧洲游记作者也对殖民地发生的事情毫无切肤之痛,而仅仅是满足其读者对于异域的好奇和支配的想象。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殖民主义所做到的并不是跳出窠臼,而是从一个坑跳入另一个。引用普拉特的原话,帝国主义的话语“在20世纪晚期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成分,构成西方关于其努力征服的人民和地方的观念。它是第三世界的官方宗主国代码,其修辞讲述的是单调、灭绝人性、否定,与殖民统治在亚洲和非洲大部的终结、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在世界许多地方加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发展进程不谋而合”(第286页)。换言之,关于第三世界描述的主旋律从征服转化为了赎罪,但是支配关系并没有动摇。全球化并没有改变支配关系,只不过将原本发生在域外的悲喜剧搬到了眼前而已。由此而言,当下欧洲所面对的难民潮及其所带来宗教、社会和安全等问题,无疑强化了“宗主国”居民对于异域的罪恶和恐怖想象。当“看客”不再能够置身事外的时候,他们或是沦为维持“政治正确”胜利法的阿Q,或是成为特朗普式强力人物的拥趸。
至于本书之于中国当下的意义,或许有人会认为仅限于学术而无关乎现实。毕竟历史的际遇决定了我们无从体会欧洲殖民者的傲慢和偏见。但是,网站和论坛上对于“非洲”和“拉美”的描述中,不难发现普拉特所揭露的修辞工具的不自觉使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民众已经不自觉交替使用“资源丰富”“政治腐败”“景色迷人”之类的词汇描述我们曾经的兄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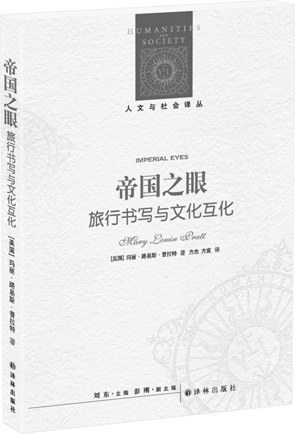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