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没有想到,她的写作会和近两年极为热闹的“返乡书写”产生关联,她更没有想到,随着话题的发酵,“返乡体”写作者的知识者身份、写作动机和写作姿态,会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甚至作为攻击的靶子。相对于自己作品的一时热闹,这些质疑让她在媒体的喧嚣中保持了一份清醒。对于她,这样的写作虽然介入了现实,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但作为一名学院知识分子,这种书写的抉择,更是一件个人的精神事件,是经历着深刻的精神剥离之后的精神“还乡”。
对一个农村孩子而言,在近几十年来的社会转型中,要想改变命运,突围人生,逃离作为故乡的乡村,进入城市,几乎成为唯一选择,只有城市,才是他们获得价值实现和自我完成之所,不论离开是多么难以割舍,不论这条路是否正确,这已经成为无以改变的宿命和固有逻辑。黄灯也依循这一固定成长逻辑,通过读书、考试,一步步离开湖南汨罗农村,到岳阳,到武汉,到广州,并最后在一线城市安家,以致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在这40年来的漫长历程中,她不但一次次迁徙居留之处,也一次次实现社会身份的蜕变,从一名乡村女孩、大学生、工厂女工变成了博士,学院知识分子。黄灯脱农、离乡、奔向现代化都市的每一次进阶,都会给她带来暂时的欣喜,特别是在她1999年因为下岗,被迫考研,接到武汉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将要彻底改变命运,彻底离开工厂、并摆脱让她惶恐的下岗工人身份时,她人生的雀跃和幸福,在此后多次的书写中显露无疑。
她从来没有想到,步入学院,经过十多年来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浸染后,在目睹知识界的真相,亲身感受到社会裂变式的发展与学院知识群体的疏离后,她内心会陷入另一重更为真实而无解的困境。“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在意识到纯粹的知识生活无法解除她内心的困惑,个体经验的激活和复苏,成为她有意无意的选择,这也许是她写作学术论文的主业之外,依然坚持思想随笔写作的原因,而现实困境倒逼下的精神重建,成为摆在她面前的首要问题。
黄灯精神的重建从“反求诸己”的自我省察开始。在侧身于学界之后,她对知识分子在诸多诱惑中,心安理得投入到各类投机钻营活动中的风气大为诧异,也正是这种不认同,使她意识到80年代播下的理想主义种子,其实一直深埋内心,并未随着处境的改变而消泯。此时,她内心的犹豫和犹疑,成为最大的纠结,恰好在此时,韩少功2000年4月,重回知青地汨罗,而汨罗是黄灯的出生地,韩少功的居处和她故乡只相隔几公里,对黄灯而言,韩少功的重返,意味着她在知识和现实的观照中,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入口,韩少功作为一名知识者落地乡村的举动,帮助黄灯确立了精神方向,同时也意味着她内心某种确定性的锚定。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种古老的知识者传统,因为韩少功的到来,在黄灯身上获得了唤醒。在她精神成长的过程中,韩少功对她精神的滋养不容忽视。落实到书写上,重新审视个体经验,审视个人在时代转型中的遭遇,成为黄灯精神重建的开始。
2003年暑假,陷入博士论文虚空营构的黄灯,开始了思想随笔的写作,她在自己从未出版的长篇思想随笔《细节》中,彻底在文字中,将自己过去有意无意回避的人生经历召唤出来,回返到她曾经生活过的故乡和工厂,在这次自由的书写中,她发现最牵动其情感和心灵的,不是程式化的学问和教条化的概念,而是那些生为农民的亲人、那些曾经的工厂同事。他们要么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流离失所,要么在改革洪流中,因为体制的抛弃而命运多舛,这些身边的人和事,在被考研突围短暂的幸福遮蔽后,再一次回到她内心,令她久久无法释怀。一旦发现自我与农民、工人之间深沉的情感和精神联系,黄灯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学术、写作,不能再拘泥于书本知识、概念、理论,而应该向那更为鲜活、广大、原初的生命体验开放,并从精神深处接纳自己出身底层的人生履历,在接通个体和身后群体的关联中,裹挟着各类粗粝的遭遇上路,并由此开始了底层视角的“精神还乡”历程。
在黄灯成名前的长达十几年时间里,她一直给《天涯》供稿,也仅仅向《天涯》供稿,她不少重要的思想随笔,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从2003年《今夜我回到工厂》开始,她逐渐将自我回返的精神奔突,转化为一篇篇文章。在此文中,她记下了那些暗夜深处,时常浮现在脑海中的工人同事,她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纺织厂工人怎样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又如何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被决绝抛弃的疲惫和无奈。在《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中,黄灯不仅再一次回想起工人遭遇房改的焦虑和切肤之痛,而且把目光转向那些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被卷入他乡的农民亲人,她书写他们在流光溢彩都市中的艰辛、辗转,暗处的卑微,还有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孤独,在黄灯眼中,他们尽管被称为“盲流”“农民工”,但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他们的存在、痛苦和不知所终的命运,不应在城市的光鲜中失踪,而应该用文字记下。这样的书写让黄灯痛苦,也让她坦然接纳,“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他们是我的亲人”。
2006年,黄灯第一次将故乡视为“问题的载体”,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书写,并接通了她此后“返乡书写”的通道。在《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文中,黄灯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直击乡村生活现场,描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环境的恶化、人口的离散、固有传统文化的沦陷和教育的危机,反思单一发展主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何侵蚀、肢解着乡村。与此同时,为了更好通过写作去贴近乡村与底层现实,自2006年起,她开始走访在广州和珠三角地区打工的亲戚、老乡,并做了大量采访笔记和录音,寒暑假回家,她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走访留守农村的亲人和乡民,尤其是亲人团聚的过年期间,更成为她灵活田野调查的绝佳时机。
值得一提的是,黄灯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离不开她对近20年蓬勃发展的乡建实践的介入和学习。也是从2006年开始,黄灯参与到中国乡村建设的队伍中,与温铁军、邱建生等中国乡建的核心人物和不少乡建志愿者有密切接触,并参与他们的研讨会和实地调研。为了更好地了解乡村和乡建,黄灯还阅读了不少相关学术著作,做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些踏踏实实的实践和理论活动,无疑会加深黄灯对中国乡村和乡村建设的了解和介入程度。联系其漫长的写作历程和思想脉络,2016年春节期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爆红,并非一次偶然的出场。
2016年,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通过微信广泛传播。这篇文章讲述了婆家一家三代如何与残酷的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深层原因,触及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因戳中了众多打工者心底“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无奈,引起了广泛共鸣。尽管黄灯在后来的采访中说到,这并不是她写得最为出彩的文章,但这毫无疑问是她意义最大的文章。在文中,她不回避婆家的难堪,敢于正视个人家庭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大胆敞开家族的隐秘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真诚和勇敢接纳的勇气。
在以前写作的基础上,2017年3月,黄灯出版了《大地上的亲人》。在“自序”中,黄灯坦言,“本书是我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和致意”。在书中,她更深地进入农村,进一步扩展了她对农村既有的观察和思考,更全面地记录了身为农民的亲人在城市化浪潮中的命运,表达了对农村、农民不可知未来的忧虑。这部兼具文学感染力和社会学理性的非虚构作品,主要由三方面的文字构成:事实叙述、口述实录、议论分析。事实叙述是黄灯对亲人生活的概要性陈述,口述实录则是根据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黄灯用这两部分文字,通过触碰到“一个家庭不能碰的秘密”,将这个无声的群体带到亮处,敞开了他们血肉之躯在大时代变动中不知所终的卑微人生,将农民的“家族秘史”放置于宏大历史的结构中,通过揭开隐匿的真相,获得了一个被遮蔽群体的历史建构。黄灯说,“一个人只有外出了,才会站在高处,俯览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才会在乎家乡河流的来路和去向”。《大地上的亲人》尽管涉及到两省三地几十个亲人的生活,笔涉教育、环境、养老、文化等诸多问题,但这部书并不松散,有相对集中的内容,也有统一的问题指向和意义旨归。
黄灯无意“唱衰”乡村,也无意把乡村刻画得破败萧瑟,她不过因为情感的羁绊,通过书写,展现了对一个群体命运的担忧,对农村困局的思虑。只是面对困局,她依然无法给出答案,但书中对乡村盘根错节困境的呈示,暗示我们,农村的问题不能仅在农村和农民自身寻找答案,它隐含在庞大而复杂的城市中心化发展模式中。在后记中,黄灯强调,“城市的光鲜,不应该以农村的颓败、荒芜为底色”。她把城市的光鲜与农村的颓败对举,不能不让人质疑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给广大乡村带来的伤害和掠夺,这是一种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
这本书的成功没有其他,只是动用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情感和真实。而这部作品能做到深情和真实,与黄灯回归自我初心、回归更广大群体的生存现实、主动建立起与现实的深刻关联密切相关。黄灯的“精神还乡”是一批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寻求自我突破、希图让自我的生命和写作扎根现实的典型个案,《大地上的亲人》亦不失为知识者精神转向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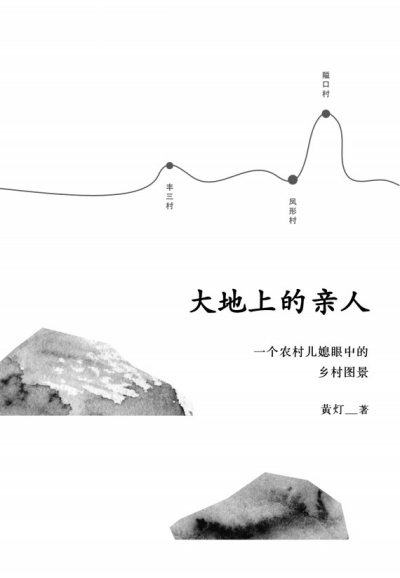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