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冬参加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制作的纪录片《东京审判》的审片会,当荧幕出现科林·F.布赖恩(ColinF.Brien)在东京法庭解开上衣,袒露脖颈,讲述自己幸而未死的被斩首经历时,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本书日文版(日文版名稍稍简化,为『東京裁判——もう一つのニュルンベルク』)中也曾看到过的这一幕。作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C.Brackman)在叙述了一组这类事件时说的一句话,至今在我脑际中仍留有深刻的印象:“当这类证词呈堂时,一些被告会摘下耳机。有的低下头,有的闭上眼,他们不愿或不能听到这些最恶劣的事情。展现在东京法庭上的场景就像希罗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Bosch)在《堕入地狱》(TheDescentintoHell)中描绘的恐怖画面。”布拉克曼之所以坚持要写出此书,根本的动机就是痛感不能遗忘的“罪孽”正在被遗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西方著述在谈到为什么要写作或讨论东京审判时,异口同声,都说东京审判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遗忘。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几乎被人完全淡忘不同,布拉克曼等认为的“遗忘”,既是指与纽伦堡审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鲜明反差,更是指东京审判的正面意义受到了质疑。因为从早期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RadhabinodPal)的“异议书”,到稍后理查德·H.迈尼尔(RichardH.Minear)的《胜者的正义》(Victor’sJustice:TheTokyoWarCrimesTrial),都是有影响的著作。有“影响”而仍不免被认为“遗忘”,是因为它们虽然在讨论东京审判,但结论、甚至目的却是否定东京审判。所以就“罪孽”而言,它们是比一般遗忘走得更远的遗忘。
本书从构想到成书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在东京审判的相关书籍中,大概没有哪一本像本书下过那么大的功夫。布拉克曼23岁被合众国际社派往东京报道东京审判,从那时起,他即有“写一本书”的“朦胧的念头”。所以他不仅尽可能多的出席了庭审,还开始收集包括隔日印发的前一日的庭审记录在内的各种文献。以后布拉克曼转任东南亚等地,各种新任务纷至沓来,但为东京审判写书的想法始终没有放弃。
五十年代回到美国后,布拉克曼遍访档案馆、图书馆、高校等公私收藏机构,查阅了用“巨大”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的大量文献,在当今世界,在东京审判这一领域,大概没有哪位的阅读量超得过布拉克曼。为撰写本书,三十余年中,他还采访了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与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学教授有过交流和讨论。作为一个记者,跟踪一个主题如此之久,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采访东京审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最早的工作,本书是他的绝笔,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东京审判是名副其实的贯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为了东京审判而生的。
与西方、中国不同,日本数十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从未间断,本书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日暮为本书日译本写了长篇解读。日暮认为:一、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进而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二、“实证”为本书的显著特色。除了庭审记录与证据文献,本书还博采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相关文献,就从对于庭审内外活动描画的细致而言,不仅在美国,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本书中述及的外界从来不明的法官团内部的情况。由于亲身参与审判采访的特殊经历,审判的逸闻也是本书别具的一个特色。三、对当事人做了相当多的访谈。那些重要当事人,如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托·A.勒林(B.V.A.Röling),在本书杀青时都已离世,作者抢救下的这些可补文献记载不足的访谈,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四、对审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场。此外,日暮认为本书也有两点不足,一是基本照搬检方与法庭判决的主张,一是未理会相关的争议与研究。所谓“不足”,与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的主流看法有关,在此不能详论。
日暮概括的本书四个正面特点,十分恰当,我完全赞成。在此只想补充一点。以上所说长处,着眼点都是“学术”,这是本书特别重要的价值。同时,本书不是学院型著作。布拉克曼撰写此书,自始就是为了更广泛的读者。它与东京审判林林总总的学术著作不同,与日本特别多见的政治性强烈的“文宣”作品也不同,它是一个非常好读的“读物”。当然,它与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同,法国艾迪安·若代尔(EtienneJaudel)《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LeprocèsdeTo⁃kyo:unNurembergoublié)也是一本易读的好书,但论厚重深入,满足读者更多期待,若代尔所著毕竟无法望本书之项背。
再说一句。没有精准的传递,域外佳作成不了本国佳作。本书译者梅小侃女士曾在北大与美国求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无论在专业上,还是语言上,对本书的翻译应付裕如自然不在话下。但我相信这本西文世界的东京审判名著在中文世界定将同获好评还有其他理由,这个理由是:译者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后人,与原著者布拉克曼会有普通译手难有的神会,使原著的情感与精神得以流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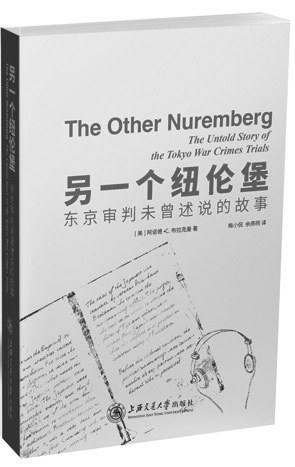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