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研”,即鲁迅研究。鲁迅始终有说不完的话,鲁研也永远有讨论不完的课题。福康兄这部《鲁研存渖》(以下简称《存渖》)是他三十余年鲁研成果的汇集,集中了他鲁研的大部分作品,我有些读过,有些是第一次获见。不论是已读还是初读,都有新鲜感,因为我也曾是一个“鲁迷”,鲁迅研究第一次把我引入文史殿堂,成为一名弄文字的人,直到如今。
福康兄取这样高雅的书名,颇有深意。《前言》中他解释道:“在古文中,研又通砚;渖就是墨汁”。“存渖”是作者自己留存的辛苦文字,寓含了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谦和自珍之意。全书四卷,分别为专论、杂考、商榷与批驳。专论篇幅最长,约占一半以上。其中开卷首篇《永铭在心的一段人生经历》,即他参加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参与纪事,读来令人感动。2006年他撰写这篇长文之时,正逢老母亲因脑出血昏迷不醒,他奔走陪伴并护理一个多月后,终于未能挽回老母的生命。在如此严重打击下,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将人生中这段重要历程写下来。我们可以从中知晓《鲁迅全集》修订工作之艰辛与复杂。
文史研究是科学,科学讲究创新,提出新问题,发掘新史料。《全集》修订原有注释,就是个创新过程。福康兄很多意见均被采纳,有简单的,也有较复杂的。如第五卷旧版“礼拜五派”,注释写:“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新版则补充为:“1933年3月9日,鲁迅、茅盾、郁达夫、洪深等人聚会,茅盾提到‘一批所谓文人,有礼拜六派的无耻,文章却还是礼拜六派的好,无以名其派,暂名为礼拜五’,大家大笑一致通过。(见1933年3月11日《艺术新闻》周刊)”鲁迅的文章发表于这年4月,可知他是及时用了这一新的“文坛掌故”。如“哥伦布”旧版仅注“美洲大陆的发现者”。陈福康提出应加上“被称为”三字,因国内外学者都有人认为,哥伦布并非第一个到达美洲。又如鲁迅《为翻译辩护》一文提到达尔文《物种由来》的两种日文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旧版没有注明日文翻译的究竟哪两种,事关鲁迅进化论思想来源,有关系到达尔文著译在中国的传播,福康兄心细如发,一一查明版本,加入新注。鲁迅文内用字从来研究者并不注意,陈福康发现《全集》第五卷《诗和豫言》,“豫”字颇为奇怪,为什么不用通常的“预”呢?他查了该文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时和收入《准风月谈》,这个题目及文章内的“豫”字均作“预”。可能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校对者误以为鲁迅只用或习用“豫”,故而硬改称“预”,因此应当改过来。
当然,修订中常有分歧,争论是免不了的。据作者自己说,讨论中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虽然有时火气大了点。如《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该不该收入《全集》,争论相当激烈。原件至今没有发现,但有当年苏区报纸及中共领导人等文章为证,陈福康能列出一连串的“证据链”。因此他坚持主张将此信列入“附录”。可有不少朋友当面或撰文与其争辩,提出“种种疑问”。最后在他与其他参与修订工作的专家们一致同意下,该文终于当做“附录”被收入《全集》。又譬如,鲁迅《冲》一文用到“年方花信”一语,旧版注释云:“指女子正当成年时期。花信,花开的消息。”福康兄认为,古有“二十四番花信”之说,“花信”指女性二十四岁,注释应该明确说明。编委会讨论时,有人翻阅《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均无这一解释,意见被否定。他不气馁,继续寻找“书证”,终于在清人戴赓保的诗词等古书中找到“花信”专指二十四岁女性的根据。然而,材料寄到出版社,却仍未被编辑采纳,这就有点令人遗憾了!
陈福康有些意见未被采纳,只要他觉得有没道理的,他就表示“不服”。如《汉文学史纲要》,原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课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曾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鲁迅生前并未正式出版,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现名。其实“古代”二字不能少,因为此书明明从上古开始写到西汉为止,“汉文学”可以理解为“汉朝的文学”,也可以理解为“汉民族的文学”。陈建议仍采用鲁迅用过的题目,是有道理的。再如鲁迅一些诗作,原先没有题目,后人加上去的,不一定贴切。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学术争鸣么,先入为主要不得。
福康兄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下参加《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的点滴,我丝毫没有看出他为参与过这项重要工作的得意,只看到他的认真和勤勉。曾听《存渖》的责任编辑说起,或谓该文涉吹捧自己之微词,我仔细翻阅,仍未读出诸公之感。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实属研究《鲁迅全集》编纂史的有用文献。
《存渖》中的文章不同于某些应景文章,过眼烟云,经不起咀嚼。我对于几篇有关鲁迅翻译成就的作品,很感兴趣,很受启发。《周氏兄弟的译论》与《鲁迅对译学的重大贡献》二文,较系统地阐述了五四前与五四后鲁迅翻译主张的发展历程。我不敢说是否发他人之未发,至少我看到这方面有分量的文章不多,此为突出的两篇。
周氏兄弟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鲁迅1902年3月去日本留学,1903年开始翻译活动。最初是从日文转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和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等。周氏兄弟当时积极从事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提出了一些译学见解,成为清末文学理论拓荒的重要组成部分。《摩罗诗力说》是鲁迅1907年、26岁时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1908年3月以“令飞”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2、3期,后收于《坟》。该文内容复杂深广,鲁迅后来自己也承认因受章太炎影响,用了许多古怪句子与古字,比较难懂。所谓“摩罗诗派”,即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积极或革命的浪漫主义流派。“摩罗”一词,借于佛教用语。陈福康把鲁迅文章中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概括出来,让人容易读懂理解。还有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里“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观点,主张直译,等等,经过提炼说明,一目了然。1927年后,鲁迅的翻译论述更为丰富,《存渖》作者总结出“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关于‘直译’与‘硬译’”“关于翻译的语言、语句问题”“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关于翻译批评问题”,洋洋洒洒数千言,至今读来仍有新意。譬如鲁迅把翻译比作普罗米修斯“窃火”,同时还为了“煮自己的肉”,这些话虽然很多人引用过,现在有人又从鲁迅的译学贡献角度加以阐述,值得点赞!
《存渖》卷二杂考类,读来更为有趣,一些过去人们极少注意的事情,陈福康注意了。《鲁海偶拾六则》第一则《鲁迅在民国第一天》,1912年1月1日民国第一天,鲁迅在干什么?几种《鲁迅年谱》都为空白。陈在1936年元旦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孙伏园散文《第一个阳历元旦》中,欣喜地发现一条材料。当时孙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读书,校长周豫才即鲁迅。文章写道,民国元年的新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午饭以后,校长周豫才先生召集全校学生谈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表庆祝……”孙伏园这段回忆虽然简略,但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确实以极大的兴奋喜悦心情迎接中华民国的成立。陈福康的新发现,不知是否已经补入新版《鲁迅年谱》?
再如“马郎妇”用典、“《太白》刊名”辨证,“幽闭”小考,令人信服。鲁迅在杂文《病后杂谈》中提到中国古代一种对妇女的酷刑“幽闭”,究竟是一种什么酷刑呢?古书记载比较简单,现代刑法史专著说法也不同,一般人都以为是将女子关起来。陈福康从明万历年间刊行的王同轨的《耳谈类增》等书中找到根据,指出是一种极其惨无人道的的刑罚,正如鲁迅所说“凶恶,妥当,又合乎解剖学”,鲁迅学过医,懂得解剖学原理,也读过《识小录》,所以在他的杂文中顺笔对封建统治者加以无情揭露,一针见血。
卷四批驳栏中数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对所谓“新史料”失实问题详加考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笔者以为这些文字至今具有很强生命力,值得研究者重视。
《存渖》作者读书广博,记忆强健,思考慎密,令人佩服。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认为,既然是旧作新集,那么每篇原刊何处,篇后应该标明,这也可以省去篇中某些夹注说明,新的材料补充作为“附记”处理则很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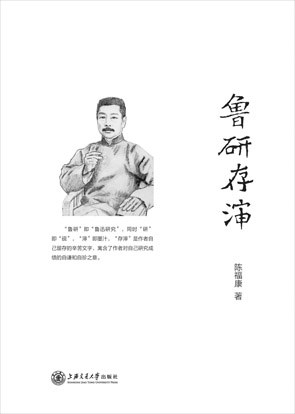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