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书斋中,将一摞誊抄得工工整整的稿件打包封起,题上“请交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王兼士先生收存弟寅恪敬托”字样,随后寄往上海,希望借银行家的保险柜,将自己的心血妥善保存。不料随着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上海沦陷,香港沦陷,陈先生虽受尽磨难终于回到大陆,却与王兼士先生彻底失去了联系。1943年,商务印书馆来谈出版事宜,陈先生只能找出“不完整之最初草稿”,由一位叫邵循正的年轻人帮助整理,“拼凑成书”,即著名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终其一生,陈寅恪先生都没有再看到自己早年遗失的那份稿件,更不可能想到,1980年,这份稿件竟重见天日,他亲手题写的“唐代政治史略稿”七字,终于出现在世人眼前。
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唐代政治史略稿外一种》线装本,引起一波小小的轰动。其之所以得到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关注,原因大致有二:一为是书主体部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之影印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二为“外一种”所录陈寅恪先生于1958年至1965年间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十余封书信,系首次全面影印披露(并附高克勤所作辑注)。
一、《唐代政治史略稿》手稿本
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略稿》,即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和本社亦均曾出版)。但凡研究唐史及对陈先生有所关注的读者学人,大约都读过后书,但见过前者的无疑要少得多。是稿为手写本,抄写工整,字迹清晰,而时不时仍有黑笔和红笔的修改痕迹。据书前蒋天枢先生序言,乃陈先生在香港时的手写清稿,因避战乱,寄到上海托人保存,不幸遗失,后来为给商务出版,只能“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蒋天枢是陈先生嫡传弟子,陈氏晚年许多出版相关事宜乃至著作文稿均交托之,至赠以“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之诗,可见所受信重,是言得自陈先生亲口,自当属实。而意外的惊喜是,1980年,大约是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关系,当年受托保存此稿的王兼士委托陶菊隐先生找到本社,交付了这份珍贵的稿件,封面上还清楚地写着“请交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王兼士先生收存弟寅恪敬托”字样。是时陈先生已去世,本社即与蒋先生取得联系,将手稿交还,并在获得家属授权后,影印出版。
作为难得一见的手稿,保留陈先生手迹之价值自毋庸多言。而更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在于其与排印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内容不完全一致,且如上所言,可能此本为更接近陈先生原意者。而对于更广泛的学人来说,稿中保存的大量修改痕迹,则可使人得睹一代大师对于自身著作的修改过程。
1.手稿本与排印本的区别。
最一目了然的区别,无疑是手稿上一丝不苟地添加了专名线、书名线(不过是按照老传统加在相应字词右侧),而排印本于此则付阙如。在二者对校方面,张旭东兄早在2011年便曾于《上海书评》发表一简短札记,列举三条例证。第一条言“开篇第一句……通行本作‘朱子语类壹壹陆历代类叁’,手写本作‘壹叁陆’,检《语类》,手写本是。三联书店最新版(2010)已改”;第二条言第二页“李唐世系之纪述”处,通行本将作为类书的《册府元龟》置于正史之前,又缺《元和姓纂》一种,亦认为显然不如手写本。但第三条则举一反例,言手写本第三十五页“元和二年己卯”,通行本作“十二月己卯”,更明晰。他还指出:“通行本又有大段多出者,是多者善抑或少而精,真难判断。”虽然旭东兄事务繁忙,后来未暇再做详校,但仅此三条已可窥豹一斑,提出的问题亦值得思考。
笔者在此基础上稍事增华,继续做了些校勘工作,发现二稿细节上差异极大,每页校改少则二三处,多则近十处。其中如“门”与“类”、“又”与“即”、“即”与“兹”、“别取”与“复取”等具体字句差别,虽或涉文采,无伤大雅;第一叶a“李唐史事”排为“李唐一代史事”,虽有简繁之别,难定高下;部分标点以及虚词增减亦置不论。第十七叶a第一句“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统治之中心也”,排印本作“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前者显然漏一“年”字,而后者少了一个逗号,亦不应当。
除了这些难分高下的差异,应该承认,有一些区别之处是排印本较优的。如手稿本第1叶b第四行有“(李唐疑是李初古拔之后裔)”一句,单独占一行,前后均空一行,似是小标题形式,下文论述亦与之相符;但其后未见有类似小标题形式。排印本中即无此一行,或为排印时,为统一格式而删除了,从统一体例的角度来说似较恰当。又第2叶a第五行至第六行,“次曰乞头;次曰太祖”,排印本改为“次曰太祖;次曰乞豆”,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同面倒数第二行“(四)父为恒农太守”,排印本补充为“后魏恒农太守”;末行“(五)父为宋将薛安都所陷”,排印本于句末补充“即所擒”:显然均更完善。陈先生云排印本系“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据鲲西先生《陈寅恪先生手稿存放之谜》一文,“邵循正当时为历史系学生,师从蒋廷黼教授治中法外交史,后经清华资助赴法国留学,为闽之世家”(转引自高克勤《拙斋书话》p34,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则邵氏之学术素养可见一斑,其“拼凑成书”,或亦有不少整理之功。
不过,既然陈先生自言手稿本为抄定之清样,且特地交人保存,则手稿本之优势自亦不待言。第43叶a第一句,手稿本作“唐代政治革命有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之别”十八字,十分简明扼要,排印本作“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三十六字,篇幅整整多出一倍,且颇有叠床架屋之感。下第五行,“党派若牛李等”,排印本作“党派若牛李等党”,显然累赘;此段末“此皆前人所未尝显言,今此篇所欲讨论者也”,排印本句中逗号作一“而”字,虽只一字之差,语句之简明节奏显然已受影响。同页下段“创启霸业”,排印本作“创建霸业”;“空前之盛世”,排印本作“极盛之世”:均觉手稿本更佳。而此页末行引《陆宣公奏议》云“分隶禁卫”,排印本作“分置禁卫”;下“承平渐久”,排印本作“承平既久”:查《奏议原文》,均手稿本是。此类例子尚多,想来不应为邵氏改错,或当年“不完整之最初草稿”即如此,陈先生后来已自行修改于手稿本,排印本中未能体现耳。
2.手稿本的修改痕迹
蒋天枢先生为手稿影印本所作序言云:“清写稿系定稿,其中仍有改笔,有红色校笔,即双行注与括号之增减,亦细密斟酌;其他,一字之去留,一笔画之差错,一语之补充,及行款形式之改正,无不精心酌度,悉予订正。由此具见先生思细如发之精神与忠诚负责之生活态度。”翻开书页,黑笔、红笔勾画修改确实处处可见。因已是定稿,观点论证上的修改比较少了,而具体字句的修改仍几乎无一页无之,而均描画清晰,一丝不苟。非独可见先生对待著作之严谨,亦可示后学以撰述之法云。姑举数例如下。
第7叶b第三行,“则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下句号描改为逗号,增加“而唐代皇室自称其祖考李熙留家武川之说可不攻自破矣”。当是感觉原先论述尚未说彻,故加一句定论以足之。第19叶a第四行,“士大夫以文章科举进身者”,“章”字为“词”字圈改而来(排印本仍作“文词”未改)。第72叶b倒二行至末行,“词采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射策决科之新工具”,“词采”后加小字“即词章”,“射策决科”四字亦涂抹原稿后添加上的,对照排印本两处均未改(且“词采”作“词彩”),前者倒也罢了,后者径作“阶级之新工具”,显然修改后之意蕴更完足。
如上所述,手稿本上的修改,有些于排印本中没有体现,有些虽有体现,但往往有若干字词区别,不完全一致。或是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先生自己亦根据记忆,将大致内容在早先之草稿上再修改了一遍吧。此不再赘举,其用心之处,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翻阅体会。
除了内容、修辞上的改动,陈寅恪先生在形式上亦精益求精,丝毫不肯放过。如第1叶a“若以女系母统”上批:“提行顶格。”盖上一段末刚好写到一行最后,若不加批注,排版时会误以为仍在一段之中接排。稿中凡遇此类情况,均不厌其烦,一一注明。第9叶a“(事见梁书、南史侯景传)”,红笔圈去括号,并拉出旁批云“此九字小注。括弧不要”。下十余叶此类批注甚多,大约初时引文出处写法未定,后决定统一为小字,不加括号,故一一批改。又如第1叶b第六行“晋书卷八十七”,改为“晋书捌柒”,盖全稿卷数标注统一为此格式,故稿内凡不一致者均一一手改。
陈先生在给中华上编的信中曾写到“拙稿不愿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虽似桀骜,但从手稿本的修改情况来看,这般从内容到格式都细致审定,需要编辑做的工作也确实不多了吧,难怪如此自信。不过,从上引漏一“年”字之类的例子来看,即便认真严谨如陈先生,仍难免有疏忽处,这也就是编辑存在的意义了。
二、致出版社的信件
从1958年到1965年,陈寅恪先生给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共写来十四封信。此前高克勤先生曾撰文披露过其中部分信件内容,但全部影印公开尚属首次。所有信件按时间排序,以彩色印刷最大程度保留信件原貌,包括信笺花样均历历可见,部分横版来信还采用了展页的形式特别制作。
和手稿本中体现的严肃认真精神一致,陈先生的信件亦是毫不苟且。所有十四封信,都是围绕著作出版事(当然,偶亦有涉及病足等日常事),其中讨论合同写法者三通,讨论校样、封面等事者五通,回应本社约稿计划者七通(第九函于后两项均有涉及)。其中如第三函回复编辑询问《元白诗笺证稿》封面上作者署名究竟当在左或在右事,陈先生表示一般自当在右,但若是作者自己题签,则当在左,且举了陈垣《史讳举例》、郭沫若《青铜时代》、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三书为例证,犹恐不足,还特意以毛笔大字,在信末将“史讳举例陈垣撰”特地按准确方位写了一遍。又如第二函与第九函均讨论封面颜色:前者为《元白诗笺证稿》之出版,提出“要用浅黄或浅蓝,最好用浅蓝”;后者为该书再版,提出“可否用深色有花纹者”,本社均回信应允。至于再三关照校样须作者过目、不能用简体字等等,都不用说了。
回复本社约稿事,是信件中占比最高的。盖本社出版《元白诗笺证稿》之后,便向陈先生提出稿约,希望出版其旧著,并承诺“校字当力求精确,版式装帧等亦当尊重先生意见,以求善美”,事实上,从来往信件和最终出版的书都可以看出,本社也确实实现了这些承诺。陈先生对于约稿事,首先是表示非常愿意,并很快提出拟定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并拟于1959年初即交稿,但因身体状况欠佳,无力整理稿件,不得不拖延下来,于信中十分仔细地做了多次说明。后来陈先生信中又提及拟先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一气呵成后再整理旧稿,本社顺势约请此稿,亦获允可,后即以《柳如是别传》之名出版。
还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信件格式相当规范。回函开头一定写明,收到贵社第xxx号函,以使事件明晰。行文中自称“鄙人”或“寅恪”,用小字以表谦逊;提到“尊处”“惠赐”等字眼,则前空一格以示尊重:这些都是传统文人尺牍写法。笔者当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为章培恒先生处理邮件,哪怕是回复电子邮件或用电脑打印者,章先生仍特别关照“弟”要用小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与年辈较高的学者们往来,曾有幸收到若干封以毛笔写于笺纸上之信件,往往还保留古风;同辈友人之间交流,则不复留意于此矣。
从1956年本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正式成立至今,已经过去60个春秋。自1958年获陈寅恪先生授权出版《元白诗笺证稿》,到多年间往复联系约稿,前辈编辑们始终对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表示最大的敬意与关注。《金明馆丛稿初编》后来终于交稿,但尚未及出版,“文革”便开始了。举国尽墨,万马齐喑,来往信件的双方自然亦莫能外。上海大多数出版社被并入人民出版社,陈先生亦受到政治冲击并去世,10月7日正是他的忌日。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出版界开始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工作。1978年1月1日,以原中华上编人马为主的古籍编辑室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恢复独立建制并正式更名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毫无疑问地被列入第一批出版计划,除此前已有单行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外,还有《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附陈寅恪诗存》四种,均于1980年便完成出版。1981年,本社又刊行了蒋天枢先生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陈寅恪文集》的附录。1988年,影印出版了《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精装版。1989年,出版了《陈寅恪读书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以上出版过程参见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收录于《拙斋书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8月版)无论是1958年开始的交流,还是在拨乱反正后敢为天下先,立刻为陈先生正名并出版其著作,均充分体现了本社前辈们的学术眼光与担当。
正是这种学术坚持,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最宝贵的财富。60年来,在一代又一代编辑的坚持与努力下,本社出版了许多杰出学者撰写的对中国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陈寅恪文集》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值此社庆之际,我们重印《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并附以书信,俾读者可感受学者之用心,及当年出版之不易。谨以此文,向陈寅恪先生,以及为我社专注学术之风格奠定基础的前辈们致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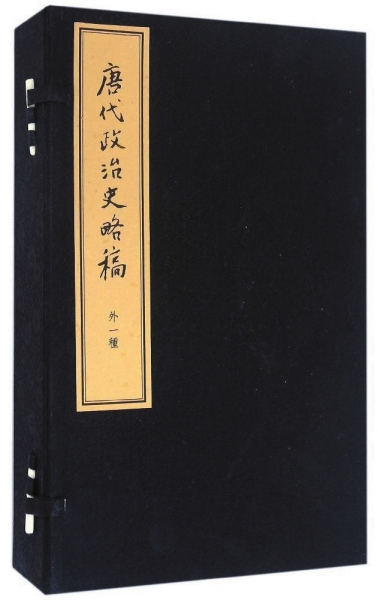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