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政治哲学……既是概念范畴,也是学科方向,它们既彼此交叠,又不乏差异。从研究对象和学科外延来看,“政治思想史”统摄最广,既包括成体系的政治学说,还涉及特定时代人们围绕政治问题形成的观念、主张、意见甚至偏见,这就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者和撰述者提出如下挑战:即如何在思想文本(text)与历史语境(context)、历史视野与哲学方法、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商务印书馆近期陆续推出的“剑桥政治思想史”中译系列,为汉语学界重新总结和反省相关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在进入新世纪的门槛上,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这个思想史系列,其历史意识和当代关怀可谓显而易见。商务印书馆原计划与英文版问世的同时推出中译版,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中译版与汉语读者见面的时间延宕至今,虽然不无遗憾,但也许这样更好,因为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学习积累,汉语学术界对西学的研究已有大幅提升,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分辨力和判断力。再加上参与这个翻译项目的中译者们全身心的投入,确保了这个系列相当高的翻译水准,其中《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中译者晏绍祥教授,长期致力于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和译介,译笔准确洗练,实乃广大汉语读者之大幸。
作为致力于学术出版的“老字号”,与一般的出版机构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出版销售端不同,剑桥大学出版社经常介入学术产出的全过程,尤其是类似“剑桥政治思想史”这样规模较大的系列丛书,出版社参与选题设计、团队组建、平台提供、资金支持、印刷出版等各个环节。对于这样的宏篇巨制,必须借助众多领域学者之间的通力合作。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照顾各位作者的关注点和学术个性的同时,使最终呈现给读者的作品是一个有着内在线索的整体,而不是多个主题论文的汇编?无论是在统筹能力还是学术视野方面,都对主编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正如作为《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主编之一的克里斯托弗·罗(ChristopherRows)在“导言”中指出的:“在本项目的早期阶段,许多作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章的初稿和一般的编写原则。这种讨论的一个益处是:它启动了作者之间的对话,并使对话一直延续到提交各章的定稿,而这一过程也保证本卷作为一个整体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页12)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覆盖历史时段上自发端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古风时代,下至公元350年。全书分两编,它们的标题直接体现的正是主编的历史分期:古风和古典希腊、希腊化与罗马世界。这一分期背后隐含的政治史框架便是从城邦到帝国的嬗变。显然,这一分期法和措辞策略意在突出历史本身的连续性,强调历史脉络里思想家之间的相互对话、反思、辩难,这样的努力实属难能可贵。
但读者若仔细阅读便不难发现,整卷书突出的是古典希腊,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从第八至十八章,汇集了相关领域众多学术“大腕儿”,对两人的主要著作做了精深的梳理和分析。其中柏拉图部分涵盖了柏氏包括“伪篇”在内的几乎所有对话,以柏拉图三大篇政治理论著作即《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为主线,其它对话与之参照。作者在写法上完全克服了传统通论著作要么泛泛而论要么将原著大意概括了之的毛病,而是综合了相关领域晚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诸如苏格拉底与“成熟的柏拉图”之间的一致与分歧、《第七封信》在整个柏拉图作品中的地位以及通过文体风格特征统计以尝试确定柏拉图对话集的年代顺序,都有很强的启发性。第十五至十八章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论旨的分析延展及其与柏拉图之间的一致与分歧的揭示,都能够使那些细心的读者获益良多。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固然不容置疑,但主编在凸显这一重心的同时,却未能避免因此导致的弊病:即之前和之后著述家的贡献和努力,要么是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做思想准备和理论铺垫,要么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演绎发挥。例如第二至第七章对荷马、赫西俄德、梭伦、悲喜剧、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智术师、色诺芬、演说家等的处理,显然不能完全代表相关领域目前的研究水平;再例如第三章对希腊戏剧的处理,作者只集中讨论了两部悲剧: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三联剧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无疑是一大缺憾;再比如,在柏拉图心目中,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有着同等的地位,可惜作者只用三页篇幅就将这位对城邦以及民主政治有着系统思考的伟大的喜剧诗人一笔带过;另外,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著述并不能作为单纯的历史著述对待,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即便无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肩,但主编和作者对他们这样的处理显然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和学术上的公允,而且远未能反映相关领域晚近的研究成果。对于上述问题,比较可信的解释只能是:主编的总体构思和对相关章节撰写者的选择上有自己的主张,两位主编都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方面的专门研究家,或许在他们看来,希罗多德等人的著述只能被归属于历史著作,是历史系学者的“自留地”,他们在政治理论、政治哲学上的贡献即便有,也非常有限,现代学科建制的隔阂和偏见对他们的编写视野构成了相当的局限。
与此相关,主编和作者对罗马时代的处理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罗马政治理论的核心载体是罗马史学家们的著述:诸如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等。然而遗憾的是,整卷书只用一章进行介绍,即第二十五章“拉丁语历史作品对罗马政治思想的思考”。相较而言,第二十四章对西塞罗却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这样的安排更强化了如下印象:因为西塞罗与柏拉图有着更为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而整卷著作都是围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安排布局的。
因此,从主编和作者对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所谓“史学家”的处理可以看出,现代学科建制带来的人为区隔甚至知识偏见可谓根深蒂固。这可不仅仅是当代西方学术界所面临的难题!
笔者之所以写这个短评,目的绝非是要否定西方同行可敬的学术努力和积极的学术贡献。而是意在提醒:不妨将这部宏篇巨制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其“得”需要我们积极学习,其“失”更需要我们努力避免。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正如西方学者在他们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编写“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一样,中国学者同样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完成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它的长处或许并不在于提供所谓“中国视角”“中国立场”,而是在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前辈贡献的基础上,拿出内容更加完备、结构更加均衡、视野更加公允的通史著作。毕竟,在学术上,从来就只有更好的与次好的分野,根本无所谓中国的与西方的不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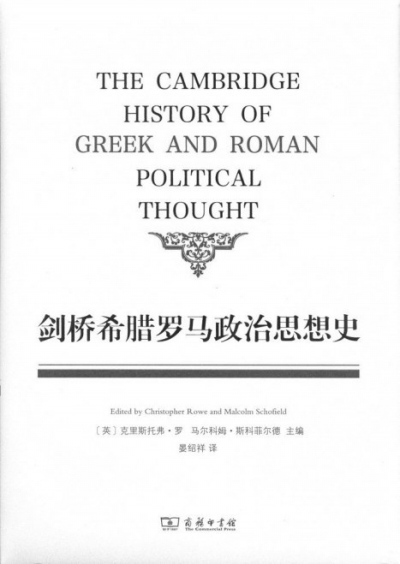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