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是一个导火索。我写小说也是冒很大的险。一个批评家写小说了,如果写得很可笑,会把你从前得来的荣耀全部抹掉。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是有的。
吴亮写小说了。
这件事似乎比他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更引人关注。那个超级自信甚至有些狂妄的评论家,当代文学似乎都不在他的话下,早早地为自己设置了无形的门坎;如今突发奇想自己要动手写作,他的起点将有多高?
当然是写上海。又不止于写上海。上海的魅力绝不在它可以看得到的风景与满街表情各异的人流,而是在“那些根本无法直观的内部世界,它的欲望,它的隐秘,它的幻象,它的错觉,它的疯狂,它的计算”。吴亮在小说里说,上海不善交谈,上海没有话要说。
但是作为上海人,吴亮喜欢对话。吴亮喜欢论战。
中华读书报:《朝霞》的出版,使你从一个评论家变身为被评论者,什么感受?
吴亮:很意外。我尽量用不同的语言不断地谈自己的作品,说字面上的东西还不够,还要说字面外的东西,就需要不断地问自己。同时接受很多人的解读。写作的半年时间,每天和小说连在一起。这种情况以前没有。以前很多话题的观点是变化的,谈别人,这次是谈自己。
中华读书报:这种不断的“问”,是否也能发现您本人在写作中未曾发现的一些问题?
吴亮:非常复杂。我讲“问自己”有很多内容。有些想法是被“问”激发出来的。比如有人问我写长篇小说和写批评有什么差别?差别太大了——以前写文学批评,是有话要说,通常一个小时就解决了;但小说是生成过程,是不断在膨胀、不断在拉长。我也有提纲,但是很模糊。当小说随着时间推移时,我要不断地回头看,必须注意前后是否照应,要有逻辑的关联,直到你写的人物立起来了——这是很刺激的感觉。
写《朝霞》就是意外的触动。外部原因是金宇澄不断鼓励我;内部原因是随笔集《我的罗陀斯》写完后,感觉还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现在看《朝霞》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而且还有突破,带来很多我想不到的东西。这是我惊讶的。
另外,小说里的那些人还没有栩栩如生出现在我脑子里时,有一段时间很混乱;当他们生成时,我的日常生活智力明显下降。但小说里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这是生物钟的一个自然调整。每天我去办公室写作,感觉一群人在背后跟着我,我必须马上记下来。这感觉也是全新的,只是来得太晚了。
中华读书报:今天所引起的反响,是小说家吴亮的原因,还是评论家吴亮的原因?
吴亮:“吴亮”是一个导火索。我写小说也是冒很大的险。一个批评家写小说了,如果写得很可笑,会把你从前得来的荣耀全部抹掉。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是有的。小说还没在《收获》发表时,就有电视台来拍我的节目。我说是否有点太早,他们说,只要是你的,我们就敢做。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评论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吴亮:最重要是发现。我说的“发现”,不是否定编辑的重要性,编辑是非常了不起的,编辑的发现很多是靠经验和直觉,靠他的文学修养;当然有的编辑本身就是批评家。我说的是批评家的发现,我能够发现作品中以前没有被发现的、或别人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不仅是小说,而是小说方法、小说观念。
所以,对人的发现,我有“发现”。在某种方面,文学和艺术有点相通,就是发现人。我的敏感点和嗅点在这里。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下决心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标高?
吴亮:写作不是面对一座山,想爬就可以爬上去。我不知道山有多高。不知道自己走的路,哪一天能停下来。写到两三万字,第二叙事人阿诺出现了,李兆熹、邦斯舅舅、马立克也出现了,这些都是边缘人,都很奇异——我的基本结构形成了,是块面式的,蒙太奇式的,每一个作品的单元是两百字、顶多八九百字,还有三四种形式,一个场景一两个人或三四个人,假如用电影来看,每一个自然段里有三个机位,或者是长镜头,推拉摇移跟甩,视线会跟着讲话的人转移;有的是对话,有的是剧本,有的是日记、书信——尽管那个年代写信很危险,还是有很多人在写。五种形式分开了,镜头滑动自如。我的小说布局像是围旗,开局时白子黑子非常遥远,慢慢走近,将进入实地的时候打入,争先抢占棋盘上的“大场”;又好像是一个园丁。我拿到一块空地做花园,没有计划,没有图纸。第一天种进来一棵树,第二天拉个篱笆,第三天挖个井,慢慢把花园布满。我没有办法按原来的路径返回,但是你可以从每一个路径进入。我本来想写一个特殊的小说,写两万字的时候,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小说,因为触及了文革,文革很多人写,但是没有人写得好。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写得好吗?评论家程德培说您这是“风险写作的取胜之道”,您觉得自己胜了吗?
吴亮:我写完最后一段,松了一口气,我知道结尾很重要。从92到99节,我是最满意的,非常饱满,没有一段是不好的。最起码是杰作——假如还不能说它是伟大的话。
中华读书报:给小说人物取名字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马立克这个名字就是受马克思的影响。那么马馘伦呢?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生僻字命名?这几个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有无特别的用意?
吴亮:取名字非常重要。有时候读小说一看名字就觉得很假。我取名字一定要看到这个名字就感觉人物是活的。
小说开始要有一个叙事人出现,“他”是一个代言人,就是当年的“我”,当然不是真实的我。要写我,就需要心理活动,这很麻烦。所以一定要拉开距离。直到需要相互称呼名字时,才把“他”的面纱拉下来,这时阿诺出现了。
我当时有几个朋友,说起我在写的小说,说“阿诺是你。假如你只有少年视角,还不够丰富。还要有一个成熟男人的视角。”她向我推荐了黑塞的《荒原狼》。这部作品讲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分裂,讲都市里的孤独,我都感受到了。但是文革中没有空间给你孤独。我需要一个闯入者,这个人非常有学问,有眼光,行踪诡异。那个时候我已经想好要写马立克,他从新疆农场逃回来,他的知识储备,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非常有教养,肯定出生在不一样的家庭,马立克出现拖出了他的父母,这就是马馘伦。马馘伦难道没有同事吗?他们在文革后期怎样?这样就出现了三个知识分子。我把我比较熟悉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比如对拉伯雷的体会。
中华读书报:《朝霞》写上海的地域风情,但是没有一条弄堂是真实的。写马馘伦,反而出现了中央编译局这样真实的单位名称。
吴亮:写上海的马路是真的,弄堂只有一条是真的,淮海坊。写小说一定要真真假假。
中华读书报:一般意义上讲,小说家首先是讲故事的人。《朝霞》中的故事总是不断的中止,这样有可能给读者造成的阅读障碍是有意“反其道而为”吗?
吴亮: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想到读者是什么人。比方说雨果,普鲁斯特,假如他写小说时有读者的概念,肯定不是我;即使是本国人,鲁迅是为我写的吗?但是我被打动了,这是文学的力量。
读者是一个动态的群体,是生成的,不要用固定的概念界定说这是作家,这是读者。你读我的时候,就是我的读者。这是一种相遇,这种相遇也可能是一百年之后。我相信所有的书都不是为吴亮写的,但我可能是很好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那么用一种图志的方法书写烟草的生长过程,这些看上去刻板枯燥的知识穿插,也是必须的?
吴亮:比方说有99朵花。这朵花拿掉可以吗?可以。按这个逻辑,所有花都可以拿掉。森林之所以成为森林,是因为每片叶子都重要。邦斯舅舅一肚子学问,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学问没有用处,他又喜欢听众,他要说话,只能对侄子讲烟草的事情,讲鸡零狗碎的事情。这边翁史曼丽在埋葬大黑猫,那边读报栏里出现一排照片,是刚刚被处决的死刑犯……写到这里时我在发抖。看似一些无聊的东西,其实很重要,都有隐喻在里面。包括结尾,写“阿诺睡着了,他梦见了马思聪。”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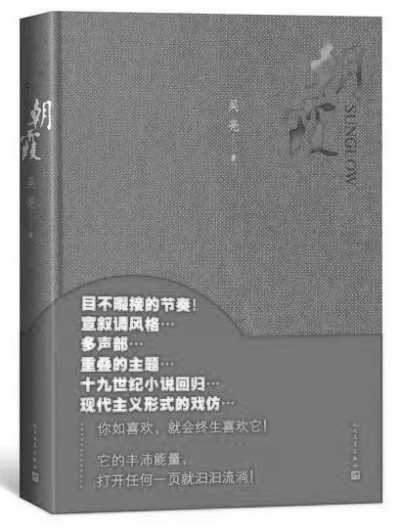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