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究竟是应该侧重于“汉皇重色思倾国”,归结为政治讽喻,还是应该着眼于“此恨绵绵无绝期”,归结为真爱咏叹,历来颇有争议。可无论专家们如何评价定位,其广为流传的事实无疑证明了这首诗的“爱情”题材更贴近大众的向美本能与情感取向。赵翼在《瓯北诗话》里就白乐天及其作品曾有如下评介:“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
赵翼之评这一席话堪为《长恨歌》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精当注解。李杨故事因男女主人公身份、地位的极端特殊,加上背景的富丽、氛围的旖旎、情节的跌宕、结局的凄凉,“其事本易传”。白居易写《长恨歌》又打破了他所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原则,用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贯穿始终,其情景交叠的完美结构,音韵和谐的语言风格,大大强化了故事本身的艺术感染力。
李杨故事很早便有英文译介。1874年,外交官出身的英国汉学家乔治·斯坦特(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汉名司登德)在伦敦出版了《玉链二十四珠:歌词民谣选集》(TheJade Chaplet,in Twen⁃ty-fourBeads:ACollectionofSongs,Ballads,etc.)一书。此书从第16章到第21章依次题为:“杨贵妃”(Yang-Kuei-Fei)、“皇家情人”(AnImperialLover)、“丝网”(Silk⁃enMeshes)、“梦乐”(DreamMu⁃sic)、“杨贵妃之死”(TheDeathofYang-Kuei-Fei)、“杨贵妃之坟”(The GraveofYang-Kuei-Fei),都是李杨故事的片段,由司登德笔录民间唱词并翻译成英文。这六篇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使之成为颇引人注目的内容,以致被后人误认为是白居易《长恨歌》的翻译,尽管整本书与唐诗并无关联。
笔者见到《长恨歌》最早的完整英译,出自于英国汉学大家哈伯特·翟尔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1901年问世的鸿篇巨著《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翟尔斯翻译这首诗之前,用整整一页的篇幅介绍了唐明皇的政治成就与贞观之治的辉煌,然后将《长恨歌》以“The EverlastingWrong”为题译出,分为八大段,每一段各添加了一个小标题:
开篇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为“倦怠”(Ennui)。
从“杨家有女初长成”到“始是新承恩泽时”为“美人”(Beauty)。
从“云鬓花颜金步摇”到“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狂欢”(Revelry)。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为“逃亡”(Flight)。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夜雨闻铃肠断声”为“放逐”(Exile)。
从“天旋地转回龙驭”到“东望都门信马归”为“归来”(Return)。
从“归来池苑皆依旧”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家园”(Home)。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结尾为“灵界”(Spirit-Land)。
品读《长恨歌》原文,开卷第一句总领全篇,故事从这里展开。杨妃因美色而得“承恩泽”,玄宗因她而从此“不早朝”;马嵬坡杨妃之死是故事的转折点,李杨的爱情遂成“长恨”悲剧;玄宗在蜀中黯然神伤,还都路上追怀忆旧,回宫后睹物思人,终于将故事的结局推向海上仙境中的重申前誓,归结到“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题旨。翟尔斯的段落划分很清晰,也很准确地把握住了故事的脉络。
翟尔斯是英美汉学界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家,以风格典雅的韵体直译知名,“在保存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尽管中国诗歌在形式上既可以作为诗歌,也可以作为散文来翻译,但他个人倾向于用诗歌的形式,因为对原作形式上的重现也同样重要。为此,他强调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必须押韵,否则便不足以体现中国诗歌的特点,因为中国诗歌原本是为歌咏而作的”(江岚:《唐诗西传史论》,第44页)。到《中国文学史》问世之时,翟尔斯按照自己这个原则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技法已经相当圆熟了,对译诗“必须押韵”的坚持几近于执拗,甚至于不惜因韵而害意。
可他翻译《长恨歌》却是一个例外,译文通篇虽形式工整,辞藻考究,却不押韵。究其原因,大约是他更看重《长恨歌》的叙事功能,需要用其内容来补充说明他前面述及的唐玄宗及其时代,相对而言,作为诗歌的审美特性便被忽略了。且来看看被他题为“美人”的这一部分:
杨家有女初长成,
From the Yang family cameamaiden,
just grown up to woman-hood,
养在深闺人未识。
Reared in the inner apart-
ments,
altogetherunknowntofame.天生丽质难自弃,
But nature had amply en-dowedher
withabeauty hardto con-ceal,
一朝选在君王侧。
And one day she was sum-moned
toaplaceatthe monarch’sside.
回眸一笑百媚生,
Her sparkling eye and merrylaughter
fascinatedeverybeholder,六宫粉黛无颜色。
And among the powder andpaintoftheharem
herlovelinessreignedsupreme.春寒赐浴华清池,
In the chills of spring, byImperialmandate,
shebathedintheHua-chingPool,
温泉水滑洗凝脂。
Laving her body in theglassywavelets
of the fountain perennially
warm.
侍儿扶起娇无力,
Then, when she came forth,helpedbyattendants,
her delicate and graceful
movements
始是新承恩泽时。
Finally gained for her gra-ciousfavour,
captivatinghisMajesty’sheart.
原诗中的“粉黛”是“女人”,指代后宫三千佳丽,翟尔斯译为实指物质的“粉”与“黛”,明显是误译;将“始是新承恩泽时”译为“终于增添了她的魅力,掳获圣心”也不准确。当然正如翟尔斯自己曾说过的,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永远是月光之于太阳,水之于美酒,是难以并列作横向比较的。当他把《长恨歌》当成李扬故事的文本来译介的时候,错漏之处更难避免。同时翟尔斯翻译文学作品的态度总是很学者派,将自己置身于原文之外,运笔客观、严谨而冷静。所以一旦遇上《长恨歌》这一类抒情成分很重的作品,他的译文便难免平淡,缺乏了声情摇曳的感染力。
相比之下,受他的影响而终身致力于译介东方古典诗歌的英国诗人克莱默–班(LauncelotA.Cranmer–Byng,1872—1945),在这个问题上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克莱默–班并不精通汉语,他所有的译文都是在他人文本基础上的改写。1902年,他的诗集《长恨歌及其他》(TheNev⁃er-endingWrongandOtherRen⁃derings)在伦敦出版,内容大部分是翟尔斯英译中国古典诗歌文本的重译,其中便包括《长恨歌》。
克莱默–班首先将诗题改为“TheNever-endingWrong”,与翟尔斯的诗题词意相仿佛,音韵更琳琅,意蕴也更痛切。他沿用了翟尔斯的分段并保留了小标题,“美人”这一段的译文如下:
杨家有女初长成,
From the Yang family amaidencame
Glowing to womanhood aroseaflame,
养在深闺人未识。
Rearedinthe inner sanctu-
aryapart,
Lost to the world, resistlesstotheheart,
天生丽质难自弃,
Forbeauty suchashers washardtohide:
一朝选在君王侧。
And so when summoned tothemonarch’sside.
回眸一笑百媚生,
Her flashing eye and merrylaughhadpower
Tocharmintopuregoldtheleadenhour;
六宫粉黛无颜色。
And through the paint andpowderofthecourt
All gathered to the sunshinethatshebrought.
春寒赐浴华清池,
In spring by the Imperialcommand
ThepoolofHua-ch’ingbe-heldherstand
温泉水滑洗凝脂。
Lavingherbodyinthecrys-talwave
Whose dimpled fount awarmthperennialgave.
侍儿扶起娇无力,
Thenwhenhergirls attend-ing,forthshecame
Areedinmotionandaroseinflame
始是新承恩泽时。
Anempirepassedintoamaid’scontrol
And with her eyes she wonamonarch’ssoul.
克莱默–班译文每两句押一韵,添加了不少华丽辞藻的修饰,诸如“aroseaflame”、“allgatheredtothesunshine”之类。克莱默–班对《长恨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偏爱,《长恨歌》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便是佐证之一。且这首诗在书中不与白居易的其他两首作品同列,而是单独排在开篇第一首,表明这是他接触中国古典诗歌之美的起点,也是他认识中国式爱情之美的起点。他数年后出版的《玉琵琶:中国古诗选》(ALuteofJade:BeingSelectionsfromtheClassicalPoetsofChina,1909)一书中所译介的诗歌与这一本的内容不同,却再次完整地收录了《长恨歌》,更见这首诗对于他的意义非常。
李杨故事本身的婉转缠绵,白居易笔下诗情的酣畅淋漓,让作为诗人的克莱默–班沉醉其中,低回不已。他后来所有介绍唐诗、唐代诗人、唐明皇乃至于整个唐代的文字,都脱离不了这首诗带给他的影响。他甚至隔着时空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呐喊,要他们感谢李杨创造出了如此惊世骇俗的一个爱情故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从热爱到想象发挥再到添枝加叶,最后他笔下的《长恨歌》要比翟尔斯译文或白居易原文长得多,激情饱满,浪漫优美。然而作为译诗,未免生动有余,忠信不足。
继翟尔斯这位汉学家和克莱默–班这位诗人之后,阿瑟·韦利(Ar⁃thurDavidWaley,1889—1966)是英语世界最早专门、系统地译介白居易的汉学家兼诗人。他的散体直译尝试以英语单词的重音对应汉语的单字,形成了译文所谓的“弹性节奏”,成为现代英语诗坛开创新诗风的有益借鉴。他曾以《琵琶行》和《长恨歌》为例,列举白居易在欧洲和日本文学艺术界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情况,同时指出,《长恨歌》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恰恰在于它的悱恻缠绵,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政治或道德寓意,他对白居易诗论所倡导的“以文教牧人”的观点也颇不以为然。不过这位多产勤奋的译家明确表示过,他尽量避免那些前人已经翻译过的作品,因而《长恨歌》或《琵琶行》都不在他选诗的范围之内,他没有译出过这两首白居易最著名的诗篇。
后来译出过《长恨歌》的是威廉·弗莱彻(WilliamJ.B.Fletcher,1879—1933),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于二十世纪初首开唐诗专门英译之先河。《长恨歌》的全文英译,见于他的《英译唐诗选续集》(MoreGemsofChineseVerse,1919)。弗莱彻不再划分大段落,将原诗的每一联作为一个小节,每小节4句,格式规整,押韵严格。学界普遍认为他深受翟尔斯的“诗歌必须押韵”、“必须保持诗歌的格式”以及“必须忠实于原文”等翻译理论的影响。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是来看看弗莱彻对相同诗句的翻译: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A maiden in the house ofYang
Towedlock’sagehadgrown.Broughtupwithintheharem,Andtotheworldunknown.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A lovely form ofHeaven’smould
Isnevercastaside.
AndsothismaidwaschosenTobePrince’sbride.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Ifshebutturnedhersmiling,Ahundredloveswereborn.Therearenoarts,nograces,Butbyherlookedforlorn.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Twasinthe chilly Spring-time,
They bathedin Hua-ch’ingLake;
AndinthetepidwatersThecrustedwinterslake.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When thence attendants boreher,
Sohelplessandsofair;
ThenfirstbeatinherPrince’sbreast
Desireandtendercare.
可见弗莱彻的韵体直译大体上的确沿袭翟尔斯风格,只是在格式上,翟尔斯强调对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重现,弗莱彻则更坚持传统英文诗歌的格式。对“粉黛”“凝脂”“恩泽”这一类汉语中特有的、具有多重文化意涵的词汇,他的处理比翟尔斯自由,遣词造句相对浅近,同时也不像克莱默–班那样想当然地添枝加叶。他的译文里最有意思的是将“君王”译成了“王子(Prince)”,又为“春寒赐浴华清池”补出一个主语“他们(they)”译成“春寒同浴华清池”,加上“娇无力”译成“如此美丽如此无助”等渲染,益发把李杨故事落实成了灰姑娘故事的模式。
以上三种译文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误,或多或少的转接增删,但不论译者是重叙事抑或重抒情,他们的诠释都没有偏离我们传统上对《长恨歌》题旨的基本理解。等到了TonyBarnstone,这位美国当代诗人兼英文写作教授的笔下,《长恨歌》的英文风貌就别有一番情味了。Barn⁃stone没有译出全诗,只是截取了从开头到“玉楼宴罢醉和春”为止的这一小部分,题为“SongofEverlast⁃ingSorrow”,收录于他和中国诗人周平合作编、选、译的《中国艳情诗》一书(ChineseEroticPoems,2007)中。以上三位译家笔下的诗句,在Barnstone译来如下:
There isa girl from the
Yangfamilyjustcomingofage,
Hidden deepinherchamber
andnooneknowsabouther.
Itishardtowastesuchnatu⁃
ralbeautyinanonymity,
Andonemorningsheischo⁃
sentobeatthe Emperor’sser⁃
vice.
She returns his gaze anda
hundred charms rise from her
smile
Making all the painted faces
intheSixPalacesseempale.
In chilly spring sheisprivi⁃
leged to bathe in the Imperial
HuaqingSpa.
Her skin like cream is
cleansed in the slippery hoe
springwater.
She seems so coyly weak
whenmaidshelphertoherfeet,
This is when she first re⁃
ceivestheEmperor’sfavor.
Barnstone曾旅居中国并学过汉语,且家学渊源,对中国现当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英译与传播作出过杰出贡献。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对原诗的再现,而且注重译诗本身的诗歌性和审美性”。他反对简单地逐字逐句对照翻译,“而是在充分考量原诗的审美意识形态和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后,将译诗作为新的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姜天翔:《托尼·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翻译》)。对照之下不难看出,Barn⁃stone的翻译最切近原文,如果将他的英文回译成汉语,差不多就是这一部分《长恨歌》的白话重写。他的华人合作者对此必定贡献良多,同时也体现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交流层面的拓展,东西双方对彼此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等各方面的了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长恨歌》所咏叹之“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是故事的焦点,更是这首诗歌最动人心之处。从Barnstone节译的这一部分读来,“长恨”已无从谈起,尽管他在诗末注释中简要介绍了李杨故事的梗概。到他把“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翻译成“Whenhermakeupis done in the golden chambersheserveshimatnight, andafterbanquet in thejade towers theysleeptogetherdrunk”,且就此戛然而止,这首诗的主题就只剩下“艳情”。于Barnstone而言,译文是否与原诗的主题有距离或有多大距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服从《中国艳情诗》全书的主题。他编、选、译这本小书,是为了展示被中国儒学正统所排斥的“性爱”内容,并以此丰富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基于这个明确的方向性与目的性,李白的《秋浦歌》、寒山的《洛阳多女儿》,杜秋娘的《金缕衣》,韦庄的《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等这些通常不太可能被解读成与“艳情”有关的篇什,其英文样貌就都多了一重暧昧的迷幻的情态。
若以母语背景将百余年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译家分组,汉语为母语的是一大组,汉语非母语的是另一大组。上列数位译家都属于后一组,同时各为该组不同汉语水平的典型:翟尔斯、弗莱彻可谓“精通”,Barn⁃stone“略懂”,克莱默–班则“空白”。而他们对中国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是一致的。为了给读者也给他们自己提供东方诗情诗意的文本参照和美学信息,他们译介的动机和出发点都带着汇通东西文化的善意。他们不约而同地只翻译,不点评,意图将原作的本真态交给读者自己去认识、去评判,也表明他们面对原作共同的、谦逊的诠释态度。
若以专业背景分,这三位译家也很典型:翟尔斯、弗莱彻是汉学家,克莱默–班是诗人,Barnstone二者兼具。专业背景与英汉两种语言水平的差异相叠加,首先影响了他们理解原作的程度,其次影响了他们再诠释的角度,第三影响了他们译文的遣词造句,第四,也影响了他们对英文目标读者群的预设。于是,当他们带着对两种异质异构的文化历史、审美心理、诗歌艺术的各自经验与探求进入《长恨歌》的原文世界,再以各自的译笔作出另外一种语言的回应,便产生了各自侧重点的差异,对《长恨歌》的“本真态”及“神韵”的界定随之出现差异:翟尔斯重“史实”,弗莱彻重“诗意”,克莱默–班重“深情”,Barnstone重“情欲”。加上他们各自在技术层面上的不同处理,创设出了《长恨歌》不尽相同的英韵文本。所以当我们以《长恨歌》本土的、传统的、默认的诠释角度去品读他们的译文,似乎总难免发现这里或那里有亏于“忠信”,而译家们自己则认为他们笔下所呈现的就是原文。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拘囿,放弃返本寻根的执拗,站在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的维度去评量,则必须承认无论是翟尔斯的拘谨,弗莱彻的谨慎,克莱默–班的夸张,抑或Barnstone的断章取义,都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了能够相互比照、相互补充的英韵《长恨歌》。他们用另一种语言对《长恨歌》的解读,不仅都是将白居易这首名篇纳入世界优秀文学体系的认真尝试,其呈现的多样性也恰恰证明了原文作为审美对象的丰富性及其被深入挖掘的多重可能。换言之,以一种“互为主观”的方式去审视《长恨歌》跨越语言文化的“被诠释”,同时也是重新认识原文文本的过程。对于我们自身文学经典解读的重构,以及参与世界文学的总体对话,都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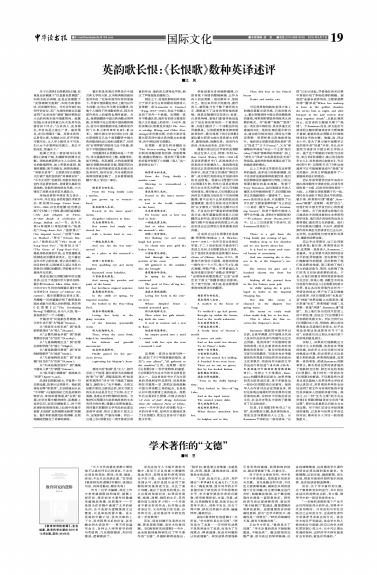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