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琴与高士、琵琶与侠客、笛与书生、筝与儿女、胡琴与常民生命性的相行相契入手,此种连接根柢地映照出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
不同乐器的近现代发展
谈民族乐器的发展,虽可从诸方切入,但“乐为心声”,中国艺术原强调与生命观照的相连,中国乐器在历史中完成的生命性又如此之强,因此,若不能在生命性上有所回归、发展,就可能导致自家立脚处的丧失。可坦白说,能于此返观者并不多。但虽不多,不同乐器在应对时潮时,因于不同的生命性及乐器特质,也自映现出彼此的不同。而就此:
古琴是高士,既与世间较无涉,乃更能自外于世间之变换;既关联于美学核心,自然不随一时之变而转;既是文人情性,所抒总乃胸中之气,也必然与其他的美学生活如诗、茶等相关;既无以也不须纳入乐队,更无所谓与时俱进。也因此,琴在近世,从严格意义讲,谈不上有什么创作。
琵琶是侠者,它有其行走于江湖、呼应人间的性格,但因个性强烈,所以对应时变的能力及主体性仍强,琵琶的当代创作在质与量上皆可观。其间,虽有走向歌谣化的倾向,但深厚的传承既在,特质乃仍显著,从人生情境、生命角色而言,亦仍具江湖本色。只是因歌谣化多了点柔软,因舞台性多了些表演,少了那份直抒本心的清朗或开阖大度的畅然。
而笛呢?近代的发展既重建了它独奏之风貌,更遥续了唐笛诗之韵致。
笛乐器的改革缘于笛音域及转调上的局限,虽做过许多尝试,例如在按孔上加键等等,却都因笛音色以及简单结构下气指唇舌乃更好应用的原因,它仍回到了“一管写清音”的原点,也仍道器相应。
不过,一九九〇年代后的笛乐也因大乐队的协奏与现代音乐(新潮音乐)的趋势,主要着眼于各项表演的开拓,韵致乃迅速流失,其书生、文人的生命形象渐淡,多的是舞台炫技的角色,相较于前期,反无法留下深契人心的作品。
相较于琴/高士、琵琶/侠客、笛/书生的素具或仍具主体,筝/儿女的当代发展就大大不同。筝五声音阶定弦面对西方音乐七声乃至十二音列、自由转调的威胁,显得更为无力,再加以文人属性原淡,面对文化变迁,乃特别随势而为,就恐追之不及,其发展因此与传统形成了一定断层。
断层首先出现在表现手法上,其次也缘于乐器型制的变化:由十六弦变成二十一弦后,筝共鸣箱大,筝弦相对须粗,乃使得行韵难用,使筝原先清亮“玉柱冷冷对寒雪”之韵不见。
新派筝与传统筝在一定程度上像是两种乐器,筝的传统,以及虽以民间生活角色出现却仍隐然遥续古典的部分又常被通俗歌谣似的制式风格或实验性、舞台性的新作取代。从文化特质、美学传统看,有心人都不能不正视这种异化。
胡琴的发展在当代最为显著,由“地本庸微”到管领风骚,从戏曲伴奏到技巧华彩的独奏、开阖出入的协奏,使它由常民走向殿堂,但其中“极尽技巧之能事”既成流行,与常民之自然、日常乃成两极,作为要角的二胡其柔美委婉、一唱三叹的韵致尤多流失,亦难免于失却自家特质之讥。
雅俗与流变
这种不一的变化,一般总以为缘于乐器不同特质,及当代人不同观照,但更与乐器在历史中完成的生命性有关,而在此,“雅俗属性”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中国,雅俗之争是观照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坐标。变迁通常来自中外接触,如汉唐,变迁也来自社会结构的改变,如雅乐、郑声之争及宋的民间经济导致戏曲的兴起,但无论哪种,其发动或变化总先来自俗文化。
俗文化,贴近生活,它不直指那文化中不变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所以既易于接触新事物,也无包袱非得排斥新事物,汉文化的人间性原极强,随生活而变更属当然。
雅文化不同,它既直指那文化中不变的宇宙观与生命观,又牵涉统治的皇室官家与拥有诠释权的文人,要变就不容易。面临文化变迁,雅文化总扮演着捍卫传统的角色,而它的拒变捍卫既使俗之变不致完全逐势而为,外来文化乃无法迳自泰山压顶,其进入遂非得一定程度地本土化不可。
琴的不变,筝、胡琴的大变,正缘于这雅俗属性的不同。然而,文化虽有此雅俗之分,文化变迁的发动虽总从俗文化开始,但在传统俗文化迅速被侵蚀取代时,雅文化则不仅扮演捍卫自身的角色,且还因认同的亲疏,唇齿的相依,乃也将俗文化纳入捍卫范围之内。由此,部分俗文化经由筛选也逐渐去芜存菁地被纳为雅文化的一环,而外来文化与原有其他俗文化的结合则成为新一代的俗文化。
这种变迁模式适用于历史中的许多事物,也可以之来观筝乐及胡琴音乐。
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筝乐,就因这一波的变化而被有心人纳为古典。可惜的是,这古典仍无力成为当代发展的参照。而所以如此,固因于这些乐曲的丰厚度,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当事者是否能以更文化性、更生命性的态度,来因应变迁。
筝如此,胡琴也一样,民间戏曲胡琴的种种不该被视为粗陋过时,反须在此观照它特质之所在,由此使胡琴的发展在传统与当代间能得兼,对接乃至融合。
生命美学的回归
中国乐器之具生命性乃因于中国的文化美学,但生命性的完成则更直接指涉中国的生命美学。
所谓生命美学,意指艺术总须关联于某种生命境界、生命情性的抒发与完成。
以琴为例,它是高士,这生命的境界就直指脱尘高洁。所以琴乐最忌媚俗,文人书画举“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用于古琴最为恰当,不仅不能媚俗,甚至忌讳有表演性,因这时就有做作媚俗的成分在。
谈表演性,舞台的夸张不必讲,曲子处理也一样,在《流水》这首名曲中有知名的“七十二滚拂”,于此做出连绵不断的流水声,也有重复的音型就如流水击石、如船夫划桨般,许多琴家因怕沦为平板,遂在音量速度上大作文章,反流于俗,而一代琴家管平湖却平稳自然地写出这两段,却益见大气。
益见大气是因如此才“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才“花自飘零水自流”,中国人说体得大化,是“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到此,人才不会以己意而犯大道。
不犯大道,就得溶入大化,体得春日花开,秋夜月明,才知人多造作颠倒,才知人只是自然之一环,而所谓的脱尘高洁正在溶入大化,非自以为有异于常人之高雅处。
于是,琴不仅不能俗,连自认高雅,都是障碍!高士是融入自然,体得春秋,超于物外。在此,生命须有山林之气,丘壑须是静观而得。
同样,琵琶是侠者,以它的表达幅度,出入雅俗,直捷大气就必是个基底,媚俗做作依然不许,即便是如今以透明的音色、变化的指法弹出人生的浪漫,也将它弹小了。
高士的人生观照从自然静观而得,侠者的境界则在现前当为中承担,这生命的大气不能拖泥带水,明朗直捷是人生化繁为简的一种境界,只有立于这个基点,才能相应它多变多元的角色而不致失足,所以说,“独坐大雄”才是琵琶的本色。
笛是书生,带有文人气,风流俊逸、悠远潇洒是它生命的特质,一样忌讳卖弄,花指繁弦会使琴失真,琵琶做小,笛的卖弄更如市井,更似难登大雅、班门弄斧之小技,而相对于琴的山林气,琵琶的江湖行,笛则需有书剑香,书是本,剑是笛清越的音色所致,否则就软了。
筝是儿女,这里可以有幽微,有淡雅,有质朴,吟猱按放正是它的功夫,它花指繁弦的副作用较琵琶大,人与人间的情感才是它的根本,生命境界在此体现的是温润体贴。
胡琴是常民的讴歌,可以激越,可以忧伤,却必得自然,这自然来自生活,胡琴当然有《二泉映月》《汉宫秋月》《草原上》等意境深远的乐曲,但这自然直抒却是原点,在境界开阔后,可跃入历史大化的感叹,但却永远有那最直接的情感,坦白说,谈境界提升,丝、竹、肉中,肉最缺乏,但能得兼,就是生活中的道。
人器、道器的合一
尽管,在上述乐器的生命性中,有些价值、有些面相在传统是更被拈提的,如琴,它有独特的地位,琴曲、琴论沛然大观,历史中,形上形下一体通透,直指生命的完成,而此完成又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具现。然而,即便如此,中国音乐、中国生命却不能以此即足,这一来因中国历史文化广袤绵延,只以一器,难拥全体,二来更因中国的道并不只在这核心中才得显现。
“道在屎溺”是庄子的拈提,“道在日常功用间”更是禅家的标举,真正的道要渗于万般事物、沁于行住坐卧,若能由此观照,诸方皆可入道。
以琵琶而论,其直捷凝练,开阔大气,相较于琴的清微淡远,其实更带有“当下即是”的禅家风格,能在此不惑于琵琶指法的花指繁弦,就如繁华转身般,反更能照见艺术或道的本然,以此切入,于生命境界之完成,与琴相比,就另有一番风光。
以笛而言,其清越畅然,映现的恰是吹管乐器的开阔性,自有一股生命舒朗清新之气。
同样,即便是筝,如能娓娓道来,声韵兼备,就能显现一种淡雅雍容的气度。
而胡琴,就如我们面对《二泉映月》般,以其器情深,若能更有超越,就扣合着中国文化不离世间的原点,在此乃“极高明而道中庸”。
原来,生命境界固必乃久乃大,固必清朗容物,但其具体样态原可有别,原可有不同生命情性的开展。
所以有山林之思者入琴,具两刃相交气慨者会琵琶,有文人之气的择竹笛,富绵绵情思者观照筝,于生活讴歌的选胡琴,而此诸种选择,固系以人择器,实亦以器择人,人器在此相互影响,所以:
弹琴若失,则酸腐严肃,过度幽微,生命乃滞于内而无以开展,能免于此病,琴人就松沉从容,淡定大气。
弹琵琶若失,就花指炫技,江湖卖艺,不失于此,琵琶家生命就开阖大度,清朗直捷。
同样,吹笛者若失,既短笛无腔,其人就小,反之生命就清越悠远,文采逸发。
筝若故显其大,反常东施效颦,拘其小,则小家琐碎,能不如此,就内外兼备,亲切怡人,得兼温婉与畅然,生命亦大。
同样,拉胡琴,若陷其中,情感即耽溺黏腻,不如此,则一唱三叹,生命的感怀就深。
总之,历史乐器原有其一定之生命性,执此器者亦必就此生命性观其长短,于器乃得有成,于人就能相应。
到此,人器合一,道器合一,才真是道艺一体的体现。而中国音乐虽大,从此人器、道器之相接处契入,正如禅门依学人情性举公案锻炼般,一超直入,亦必可期!
(本文摘自《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林谷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平沙落雁》:琴曲《平沙落雁》之解题谓“藉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禅画亦常以“潇湘八景”为题,写物外山川。在中国,艺术正直映胸中秋壑、生命情性乃至大道修行,离此即被视为“致远恐泥”的“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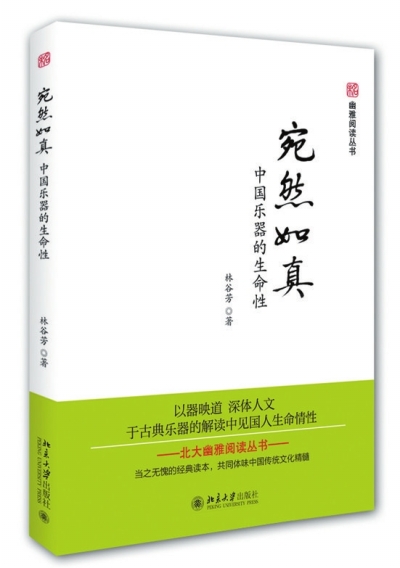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