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和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是德国作家丹尼尔·凯曼的小说《丈量世界》中的两位主人公。两位科学家探索世界的历程,大抵可以用“精纯”和“广博”进行概括。
高斯的测量
高斯,德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近代数学奠基者之一,享有“数学王子”的称号,对数论、代数、统计、微分几何、大地测量学、静电学、天文学均有突出贡献。洪堡,德国著名博物学家,涉猎科目十分广泛,一生走遍了欧洲、南美洲、北美洲,是近代气象学、地貌学、火山学、植物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丈量世界》中,作者以两位科学家的大地测量工作为线索,揭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政治、社会、人文思潮动荡变迁的历史画卷。1818-1826年,高斯受聘主持汉诺威公国的大地测量工作,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数学天赋,发明了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测量平差的方法,创建了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研发改进了日光反射仪和镜式六分仪,使大地测量的精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三角测量法是高斯采用的主要测量方法,该方法在地面上布设一系列连续三角形,通过测角的方式测定各三角形顶点水平位置(坐标)。实际工作中,高斯主持布设了庞大的大地测量网络,共确定了2578个三角点的大地坐标,为大地测量提供了充足的数据。然而,相对于野外测量工作,高斯更专注于观测结果的数学演算,共完成数据计算超过100万次。汉诺威公国的大地测量工作直到1848年才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测量工程,与高斯的严谨观测、周密运算、理论设计、数理分析密不可分。
洪堡的探险
与高斯相比,洪堡的大地测量旅程是用自己的双脚走完的。洪堡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1799-1804历时五年的自然考察之旅,五年的考察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自委内瑞拉达库马纳至新巴塞罗那,第二段自新巴塞罗那至古巴,第三段自秘鲁卡亚俄经墨西哥至美国费城。五年的考察之旅,洪堡的收获极为丰富:共采集标本6万余件,测定了空气压力、空气质量、空气湿度等自然地理数据,测量了安第斯山的高峰,探寻了亚马逊河的源头,发现了“洪堡洋流”,绘制了世界等温线图,发明了沸点高度计,发展了山地测量学,认识到地层愈深温度愈高的现象,解答了气候带分布、温度垂直递减率、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等问题。回国以后,洪堡根据考察经历整理出十本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三十卷本的《1799-1804年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新西班牙王国地理图集》《植物地理论文集》,上述资料奠定了洪堡一生的研究基础,也为洪堡带来了显赫的声誉。
《丈量世界》再现了洪堡自然考察之旅的冒险与奇幻色彩。洪堡是一位具有浓厚博物学传统的科学家,他将“永远勇于尝试,永远不要放弃”作为座右铭,力争去“记录每一天的气压,搜集每一份样本,拜访每一处洞窟,测量足迹踏过每一座山丘”。洪堡探秘自然的艰辛历程,可以从奥里诺科河之行略见一斑:1800年,洪堡乘坐小船,沿委内瑞拉最大的河流奥里诺科河划行了2700多公里,深入南美洲内陆地区,对无人居住的森林地区进行了测量制图,证实了该河通过一条支流与南美第一大河亚马逊河相通。原始森林中,洪堡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他时常遭受成群毒虫的叮咬,受到毒蛇、食人鱼、鳄鱼的侵袭,几乎每位成员都感染了热病。五年之中,面对数次死亡威胁,洪堡始终没有退缩,他坚持每天观察记录各种自然现象,测定各个地区的经纬度值。
高斯的自恋与洪堡的疯狂
阅读《丈量世界》,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不仅是一部描写科学的小说,更是一部探讨人生的剧本,高斯和洪堡的科学成就,似乎只能作为一种注脚,用来映衬两位奇人的独特性格与心路历程。
全书开篇,高斯敏感自负、蔑视凡尘的性格就显现无余,他常常因为自身的高贵灵魂寓居于平凡的身体而感到无奈,认为世上没人能像他一样真正洞悉这个世界的奥秘,即便是贝塞尔这样杰出的天文学家,都远远无法达到他的认识高度。高斯坚定地认为,自己高超的思想远远领先于这个愚笨的时代,痛恨自己能够预见,却无法步入百年之后那个美好的时代。高斯多次提及“拿破仑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才放弃轰炸哥廷根的”,这一幼稚的话语映射出高斯极端自负的心理。基于以上性格特点,高斯总是遭遇社交困局,甚至与自己的儿子都无法和谐相处。如同许多才华横溢的人物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一样,高斯的头脑中,留存着一个精致纯粹的数理世界,这个世界和谐完美,而现实世界粗鄙不堪,两个世界的巨大差异加剧了高斯的心理矛盾。
尽管高斯深爱着自己建立的数学王国,然而,相比之下,洪堡才真正称得上是“科学狂人”,甚至可以称之为“弗兰肯斯坦”。《丈量世界》中,为了验证伽伐尼电流,洪堡可以割开自己的皮肉,插入锌片与银片,直至鲜血淋漓;为了驳倒老师维尔纳的“水成论”,洪堡可以冒着生命危险,钻入墨西哥荷鲁约火山,搜集火山中的火成岩;为了证明气候不仅受纬度影响,还与海拔高度密切相关,洪堡可以写好了遗书,徒步爬上钦博拉索山5878米处,几乎命丧于山上,保持人类登山纪录29年之久。由于洪堡近乎疯狂与痴迷的科学探索热情,与洪堡一同进行五年考察的科学家邦普兰饱受折磨,他“曾经无数次诅咒洪堡被剁死、射死、烧死、毒死”。
功成名就以后,酷爱自然探索的洪堡遭受着内心的煎熬。名誉、地位、官阶、社交,这些包袱把洪堡束缚起来,使他再也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野外考察了。1829年,步入花甲的洪堡受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邀请考察西伯利亚,这次考察让洪堡倍感郁闷。考察过程中,洪堡被庞大的考察队伍簇拥,考察线路必须由政府选定,岩石和植物标本已经被当地人员提前采集好,测量数据由随行人员来完成,洪堡大量的时间被用来应酬沙皇、市长、商人。回想从前随心所欲的野外探索之旅,洪堡十分惆怅。
博物学传统与数理科学传统
《丈量世界》中,高斯与洪堡禀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各自的科学探索道路上并辔而行。二人短暂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可以围绕政治、君王、艺术、法律、死亡等话题进行热切的交谈,擦碰出闪亮的思想火花。然而,一旦回归科学研究最本质的问题,烙刻在两位科学家内心深处的宇宙观就会释放出来,把他们拉回各自的学术传统当中。在高斯看来,深入洞穴、火山、矿坑去发现知识,不过是巧合而已,世界不会因为这样偶然的探险发现而变得更加清晰,真正的科学家应该独自坐在书桌前,面对一张白纸和一架望远镜,运用深邃的数学洞见去探求世界的奥秘。与高斯相比,洪堡心中的科学镜像,更多地来自于对宇宙大书的记录与求索之中,只有尽可能包罗万象地描绘宇宙,才能在广博的知识海洋中捕获自然界统一的内在联系。
科学史上双星闪耀的例子不胜枚举。围绕某一科学问题,不同的科学家同时展开研究,他们之间竞争合作、分分合合的故事,为人类科学的演进历程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海王星的发现过程中,英国人亚当斯与法国人勒维烈各自独立展开研究,这项由数学家完成的“笔尖上的发现”甚至引发了英法两国天文学界的激烈争吵。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过程中,英国人华莱士与达尔文基于相似的考察经历,分别创立了生物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思想,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之间没有出现尖刻的矛盾,二人一起发表了各自的论文,并将进化论称为共同的“孩子”。氧化学说的建立过程中,英国人普利斯特列、法国人拉瓦锡分别围绕氧气问题展开研究,由于不同的学术信仰,信奉“燃素说”的普利斯特列将氧气称为“脱燃素空气”,拉瓦锡则通过实验证明许多燃烧过程其实就是元素与氧气的化合过程,宣告了“燃素说”的终结。
与上述事例不同,高斯与洪堡的大地测量分别蕴含着不同的科学旨趣:高斯坚信物质世界背后的数学秩序,试图通过数学语言给予世界最精致的解释,测量大地可以看作是高斯完善数学理论的一次大型实验;洪堡进行大地测量,完全出于对自然万物广博知识的好奇与钟爱,每一次土地测量,都刷新着洪堡对宇宙的认知,也体现着洪堡人生的意义。
洪堡与高斯的科学之路代表着博物学传统与数理科学传统。博物学传统历史悠久,遵循这一传统,博物学家深入自然界,广泛搜集的动物、植物、矿物等材料,对它们进行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归纳。亚里士多德、林奈、布丰、赖尔、达尔文等许多科学家都属于博物学进路。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博物学为人类带来了极为广博的自然知识,它全面记录着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真实直观的体验,并且形成了庞大的知识谱系。
数理科学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文艺复兴以来,古典数理科学传统蓬勃发展,掀起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大幕。数理科学传统呈现了一幅数学化、机械化的自然图景,自然界可以还原为精致的数学世界和物理世界。面对被数学化的自然界,科学家可以通过数理分析方法,对自然界进行更加精致纯粹的理性解码。整个数理科学传统的链条上,串联着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一系列著名科学家,这群人当中,自然不能少了“数学王子”高斯。
高斯与洪堡各自牵引着两类科学事业,宛如两条平行的直线。然而,随着高斯做出“所有的平行线都相交”的非欧几何论断,人们开始期待,高斯与洪堡这两条平行线会在什么地方相交呢?是探寻宇宙奥秘的热情?还是为自然界给出“大一统”的完美理论?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答案。也许两位奇人的交集,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正心领神会吧。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君宝得《九阳真经》之精纯,兼之悟性过人,终于建立武当一派,指导弟子七人,个个出类拔萃,武当派终于发扬光大,与少林派并立于江湖。郭襄得《九阳真经》之广博,加之优越的家庭背景和武功渊源,得以建立峨嵋一派,可惜此派日后逐渐式微,无法与少林武当匹敌。科学史上的高斯与洪堡,以及二人背后的数理科学传统与博物学传统,似乎也经历了金庸小说中的一幕。近年来,博物学似有重出江湖之势,前景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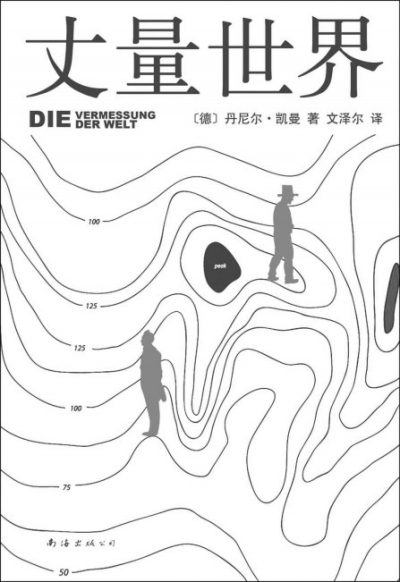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