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纳博科夫因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以及大导演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影片而知名于世,早已赢得“纳粉”无数。而许多“纳粉”得知纳博科夫还是蝴蝶研究领域某个分支的权威人物时,不禁崇拜得五体投地。这种崇拜会让他们对纳博科夫的“科学成就”作出夸大其词的描述——这也难怪,通常“纳粉”都是文学圈中的人物,或是围着文学圈打转的人物,他们很难具备科学史的眼光。
在本书正文前面有“本书所获荣誉”两页,其中一段赞美是:“继达·芬奇之后,很少有人能在科学与艺术两个领域登峰造极……《纳博科夫的蝴蝶》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奇才。”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说纳博科夫可以与达·芬奇比肩,他的蝴蝶研究已经可以算在科学领域“登峰造极”了——如此不靠谱的过甚其辞,却是出现在被许多中国公众顶礼膜拜的《科学》杂志(Science)上。
再来看本书中译本“译者序”中的说法:“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位奇人,在头顶伟大的文学家光环之下,他竟然还是一位曾长期在世界顶级学术殿堂里工作的……。”其实这篇“译者序”中的大部分意见我都赞同,但上面“世界顶级学术殿堂”这样的措词,显然也有夸大之嫌。
上面这两个例子,恰恰就是本书“推荐序”中刘华杰所指出的“纳粉”们建立的四种神话中的第一种。“纳粉”们认为,纳博科夫既然在文学上如此伟大,那他在科学上也一定是能和牛顿、爱因斯坦比肩的大人物。而这当然并非事实。
刘:
在我的理解中,你的意思是说,认为纳博科夫在文学(可归入艺术类)与“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博物学”)两个领域均有不凡的表现,这是可以的,但要是认为他的“科学贡献”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准,却有所夸大。在这样的评判中,你隐含了一个判断,即纳博科夫在文学领域里应该是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是这样吗?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科学中达到“世界顶级学术殿堂”的水准,这确实是科学史家所关心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谈的这本书,又确实可以说是一本奇书,正像译者在译者序中所说的:“说文学不是文学,说科学不是学术论文,说传记也不是专门为纳博科夫写的……”但按照刘华杰的说法,本书突出讨论的是纳博科夫的“双L人生”——指文学(Literature)和鳞翅目昆虫学(Lepidoptera)。或者我们可以说,其实,纳博科夫在文学中地位很高,在科学中也有不凡的表现,虽然单一地在文学或科学领域有不凡表现的人有很多很多,但同时在这两个领域中有不凡表现的人,就是凤毛麟角了。
所以,纳博科夫是否在科学中有世界顶级地位,在这里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他同时在两个领域游走并作出重要贡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进而,人们自然会关心,在一个人身上,这两不同领域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正如你在这次对谈标题中提出的问题:“蝴蝶对于纳博科夫和《洛丽塔》的意义”,虽然我们两人对鳞翅目昆虫学都没什么了解,但你对《洛丽塔》却因性文化的研究而颇有见解,那么,你认为蝴蝶对于纳博科夫和《洛丽塔》的意义是什么呢?
江:
其实“顶级”“登峰造极”或“凤毛麟角”之类的措词,毕竟只是文学性的修辞,并非精确的界定。
我们不妨先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能够和纳博科夫的“双L人生”相提并论,甚至更有过之者,在东西方先贤中都不乏其人。在东方,张衡作为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文学家之一,还精通天文学和星占学,至少如今的月面环形山中,有一个是以张衡的名字命名的。在西方,《鲁拜集》绝对是诗歌艺术中的瑰宝,作者奥玛尔·海亚姆(OmarKhayy⁃am)却是历法专家,还创立了一种借助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的方法。这两个例子中的科学成就,和纳博科夫的眼灰蝶分类研究成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再看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登峰造极”这样的措词也明显是有问题的。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就不用说了,不可能有人会认为纳博科夫可以和这些人比肩。那么退而求其次,随便说吧,乔伊斯?司汤达?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群星灿烂,纳博科夫能够令人信服地凌驾于他们中的哪一个之上?
在文学史上,纳博科夫的名字永远和小说及影片《洛丽塔》联系在一起。这部小说描绘了中年男性和未成年女孩之间的恋情,创造了洛丽塔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足以青史留名,那是没问题的。但世间的“粉”往往非理性,一旦“粉”了谁,难免无限推崇,任意拔高,必誉之为古往今来第一人而后已。所以刘华杰在“推荐序”中特别澄清了“纳粉”们的四类神话,实属对症下药。
最后,对于“蝴蝶对于纳博科夫和《洛丽塔》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目前的答案是:没有意义。这两者完全可以是巧合。当然,我期待你能够改变我的想法——例如,告诉我大鼓书对于科学编史学和性别科学史的意义?
刘: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想改变什么你的想法。就“蝴蝶对于纳博科夫和《洛丽塔》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你给出的答案是没有意义,纯属巧合,这当然也是一种答案。尽管“意义”所指的是什么,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不过,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发现一些特有的、与他人不同的东西,而历史研究显然不只是叙述一个故事,你也曾说过,叙述当头,立论就在其中了,这里的立论,应该是某种特殊的观点吧,否则也就没有必要“立”了。
而且,历史研究的方式之一,是在关于某个人、某件事、某个问题的不同“事件”之间建立一种“有历史意味的因果联系”(注意这不是指那种更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不只是把它们看成巧合。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会问出那个问题。就像你接着调侃性地问的,大鼓书对于科学编史学和性别科学史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一位科学家,或科学史家,或涉及到性别研究史的研究者,一反常态地迷恋于大鼓书(因为通常人们自然觉得大鼓书与之无关),或许这还真是一件值得给出说明和解释的事呢!一开始,当你把那个问题作为我们这次对谈的标题时,心里想的就是巧合这个答案吗?在这本书的第十三章,“文学与鳞翅目昆虫学”,还真的就纳氏的小说和他迷恋研究的鳞翅目昆虫学的关系进行了不少梳理,至少,在一个有特殊性的人的身上,这被认为是存在着某种关系吧。
或者,我再换一个方式来问问题:你觉得,像纳博科夫这样出于兴趣而在文学和昆虫学中取得成就,这一现象有什么值得注意、分析和评论的价值吗?
江:
定这个题目时,我倒并无先入之见。因为这个题目中的“意义”,既可以是探讨蝴蝶对纳博科夫及其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可以探讨蝴蝶对于我们理解纳博科夫及其作品的意义,而后一种“意义”就非常广泛了。
另外,关于这次对谈的题目,还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我们通常在使用这样的句型时,往往有某种默认的假定。比如,如果我们同意“蝴蝶对于纳博科夫和《洛丽塔》的意义”这样的题目可以成立,但是反过来,“《洛丽塔》对鳞翅目昆虫学的意义”能够成立吗?恐怕就很难成立了。又比如爱因斯坦也拉小提琴,如果我们同意“小提琴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意义”这样的题目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会同意“相对论对小提琴艺术的意义”这样的题目能够成立吗?
至于第十三章“文学与鳞翅目昆虫学”这样的题目,无疑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只要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当然就可以讨论这种“与”的关系——这其实就是你换了方式问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可以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来尝试回答。
你知道,“跨界”这种行为,往往会给人带来快感和满足,甚至带来某种成就感。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我本人就是如此。中国人说的“玩票”或“票友”,其实就是跨界。纳博科夫完全可以说是“鳞翅目昆虫学”的票友。
如果跨界之后,又能在两界都获好评,那这种满足感就更强烈了,那就是进入“名票”行列了。如果将纳博科夫就视为鳞翅目昆虫学的“名票”,应该是毫无问题的。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跨界的难度是在逐渐增加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跨界并非易事。而跨界后还想玩成“名票”,难度就更大,所以才能给人带来成就感。“纳粉”们推崇纳博科夫,如就跨界这一点而言,倒是可以傲视一大堆文学巨匠了——我上面随口提到的八位,好像谁也没有跨界和“名票”的著名事迹。
刘:
你讲的这些观点,原则上我也都可以同意。不过,似乎我们关注和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比如说,我们都会赞同认为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对其相对论可能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意义,但或许从事艺术教育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毕竟“意义”这个概念可以理解得或松或紧。又比如说我也喜欢跨界,对跨界的心理感受也与你差不多,但如果只把意义限于跨界,我觉得似乎还是差了点什么,跨界的心理感受毕竟主要还是属于纳博科夫个人的,而无论是作者的立意,还是对读者的吸引力或受欢迎的要点,似乎都有超出跨界的表面现象,而更关心其背后的意蕴。
比如,在当下,此书的卖点之一,是其博物学内容,而当一个文学家又从文学跨至博物学,更不用说其跨界的成功,这其中难道不是有些值得我挖掘的东西吗?前不久华杰的学生翻译的卢棱植物学通信,不也是另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在向植物学跨界吗? 华杰也强调从卢梭对植物学的研究而联系到科学传播和科学史的考察,从而对我们以往只将卢棱当作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看法有所修正。又如牛顿,如果我们只关注其《原理》,而无视其炼金术和圣经研究,或只将其视为个人的跨界,那肯定会影响我们对于牛顿的理解。在一个人的身上,各种不同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不相关甚至彼此冲突的兴趣和研究,彼此间肯定是有其相互影响的,只不过这些影响可能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那么明显和直截了当。
因而,我觉得,本书恰恰为我们打开了一种观察的可能性,让我们去思考在当时,人们会怎样理解博物学、理解文学(文学的表现显然会有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更广泛的关联),以及两者间可能有什么样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这正是此书的重要价值之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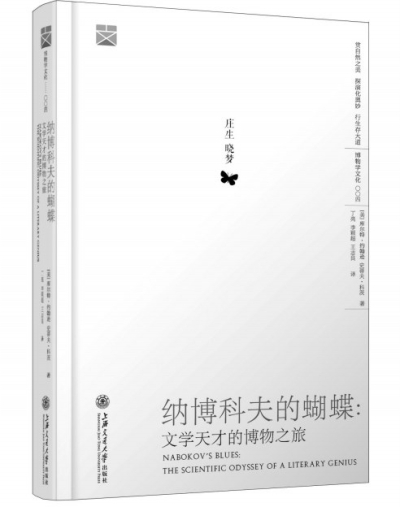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