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获读张永言先生为荣誉主编,蒋宗许、陈默、蒋信、傅娜编纂的《〈世说新语〉大辞典》(下简称《大辞典》),仅正文、附录就有548页,凡140余万字,堪称皇皇巨著,为之赞叹不已。
《大辞典》的主要编纂者蒋宗许先生等作者,在1992年四川人民版《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先生主编,下简称《辞典》)已经取得了很高水平的基础上,又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和积累,历经二十余年的浸淫研读,融会贯通,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进行了较大幅度增补和改进的力作,着实不易。相比《辞典》,《大辞典》收词、释义更全面、详尽,更符合《世说新语》专书语文词典的性质和要求。
具体来说,《大辞典》在词目、义项增补、释义更正、例证及参考文献补充等方面,均出色当行。仅就收词而论,当年《辞典》收词立目时,完全依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的《世说新语索引》,未能对原文逐一覆核辨析,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漏收。仅《大辞典·前言》中列举的Y、Z两个字母,就失收了约三百五十余条,全书失收词语近1300条——而这些词目,《大辞典》均已补上,数量十分可观。
四川人民版《辞典》有一类失收是因为对原文属读错误而造成的。例如“交合”条,释为“交好;交情结合”。引例为《世说·识鉴》3:“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大辞典》编者指出:“揆之文意,上言‘求交’,下言‘合’与‘不合’,若以‘交合’切分,则显然错谬。”(《大辞典·前言》第3页)“交”应属上为句,“而卿意怀不可交”作一句读;下文“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作一句读,如此标点,则怡然理顺了。
在词语释义方面,《大辞典》较之《辞典》有所改进、提高。以“猜”为例,《辞典》收了“①疑;怀疑”和“②畏忌”二义。但《世说·假谲》6:“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这例“猜害”如果解释为“怀疑”或“畏忌”,未免隔靴搔痒,难得其义。《大辞典》在“猜”下据此例列出了“①残忍”一义,又补“猜害”词目,释为残害,坑害,并举《宋书》《北齐书》等佐证,比较熨帖。又如,“人间”一条,《辞典》释为“世间”,而《大辞典》則补释为“世间,朝廷及从仕的婉语”(第265页)。后面这句补充很重要,用“朝廷及从仕的婉语”来解读《世说·捷悟》6“郗司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等例,就十分顺畅了。
《大辞典》充分吸收了学界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一书在手,精华尽收。我们看到,编者留心搜集、整理爬梳《辞典》问世后二十多年间学界相关的新成果,汇入相应词目,并在词条末尾列举参考文献,这对读者来说是很方便和实用的。
在《大辞典》中,编纂者经常征引当今活跃在汉语词汇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之说,既表示渊源有自,不掠人之美;同时也为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例如,“恶见”条下,引述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76页);“绝妙好辞”条下,引述启功《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文章(174页);“理致”条下,引述王东《语言研究》2008年文章(193页);“吴语”条下,引述马瑞志(1968)、陈寅恪(1980)和何大安(1993)的文章(193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部分词目下,列举了不同意见,增广异闻,为专业研究者乃至一般读者都提供了方便。例如,“款杂”条,方一新(1990)释为“空泛芜杂”,而汪维辉(2000)则释为“亲密”,编者虽以“空泛芜杂”说为主,但也列举“亲密”说的不同意见,二说并存,以资参照。“标位”条,虽然编写者倾向于以“标作”为是,但在条目的最后,也列举了“标位”之释(见18页)。凡此,都为读者提供了可供比较权衡或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和余地。
此外,在补充参考文献尤其是海外参考文献方面不遗余力,多所攈采收集。先看国内相关研究。如“冰矜”条,《大辞典》释义之外,举了王云路《中国语文》1996年第6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97:469和黄灵庚《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的三种论著(19页),为读者提供了线索。又如“不听”条,作者先后列举了叶爱国(1997)、谢质彬(2000)、萧红(2001)、方一新(1996/2003)和史光辉(2003)等五人的6篇文章(26页),可谓详赡。在外文资料方面,《辞典》原本就做得十分出色,而据《大词典·前言》所言,《辞典》出版后,“张(永言)先生随时关注着发展动态,权衡抉择,在底本上做了大量的迻录。《大辞典》将张先生迻录的相关信息已悉数补入”(前言,第8页)。《大辞典》新增补了大量的海外参考文献,阅读、使用本书的读者都可体会到。
《大辞典》文化、百科词语的收释更全面、准确,为读者阅读《世说》提供了方便。例如,“郭象”条下,《世说·文学》17记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此例涉及魏晋时期《庄子注》的著作权,属于史实问题。《大辞典》详列冯友兰(1927)、(日)村上嘉实(1941)、王叔岷(1946)、(日)福永光司(1964)、楼宇烈(1980)、汤一介(1983)、杨明照(1985)、(日)泽田多喜男、加藤究(1989)等近十位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述,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探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线索。同理,《世说·文学》1记载郑玄学成东归后遭马融追杀事,“马融”条列举日人池田秀三《马融私论》(1980)、冯浩菲《马融追杀郑玄说质疑》(1997)等论著,可以参考。——凡此,都极大地开阔了读者视野。
当然,《大辞典》个别词语的释义或可斟酌,也有少许排校疏误——均所谓大醇小疵,无伤大雅。
总之,相比《辞典》,《大辞典》百尺竿头,又进了一大步,嘉惠学林,功莫大焉。今得以先睹为快,不敢独享,故付诸笔墨,聊为喤引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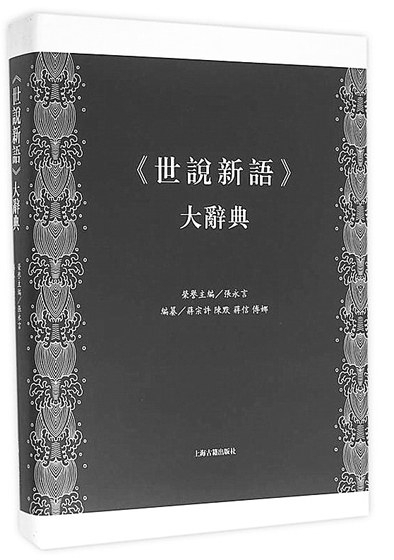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