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0日,文化研究理论大师、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因病去世,享年82岁。时隔两年,《理解斯图亚特·霍尔》一书出版。该书由张亮教授主编,汇集了世界各国知名学者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代表性论文,为读者描绘了霍尔一生的学术图谱,立体展现了霍尔不同阶段的思想面貌。正如张亮教授在序言中所说:“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六七十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开创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些‘身份’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内在统一起来的线索。”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霍尔?
“新左派思想家”霍尔
1950年代的英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民族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夹击,对英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英国的左派政治体制经历了激烈的自我检查过程。这恰恰为霍尔等左派思想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路径,即处在二者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化批判模式。虽然当时很多人将新左派的做法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分析范式仍旧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如在对当代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上,霍尔就坚持认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下才能够维持下来。”但这并不表明霍尔完全向正统马克思主义回归。霍尔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了霍尔后期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拒绝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二分模式,转而探讨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虽然此时霍尔的分析模式仍旧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但实际上它已经蕴含了其后的文化研究转向。尤其是,由霍尔领导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对葛兰西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出发,霍尔开启了他的第二重身份。
“符码学家”霍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霍尔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实现了文化理论的彻底转向。霍尔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生活的符号维度”。这样“社会意义的生产就成为一切社会实践功能的必备条件,而社会和符号的关系,才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由此出发,霍尔将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生产意义范畴的方式来强调各种内在关系”,转换成为一种“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的媒介话语模式。霍尔将媒介“意义和信息”描述为“一种借助话语横组合链中的符码操作并且在‘语言规则’以内形成的特殊组织的符号工具,这就像传播或者语言的所有形式那样”。霍尔认同语言系统先于并且决定着“现实(re⁃al)”的观念:“许多事件的意义只能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当中得以呈现。当某一历史事件在话语符号之下传递之时,这就受制于那些使语言可以表意的所有复杂且正式的‘规则’”。因此,霍尔认为,话语并不是“对‘现实’的‘透明’呈现,而是通过‘符码操作’来对知识进行建构”。
在此基础上,霍尔遵从编码/解码的基本分析模式,融合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文化主义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传媒、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和意识形态理论及种族、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当代文化研究的重点问题进行探讨,确立了其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身份。
“黑人他者”霍尔
1980年代开始,霍尔开始涉足种族、阶级与性别领域的研究,并开始深刻反思自身的黑人身份。关于黑人的身份,霍尔指出:“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也就是说,种族性不是普遍地存在的,而是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既是由经济和历史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又受到其他偶然性的影响。霍尔进一步运用此模式对当代英国的种族和阶级问题进行分析,他指出,种族是“阶级所‘寄’于其中的形态,是阶级关系被经验的中介,是阶级所占用的形式”。但是种族的形态却是偶然性的,是可以通过对霸权的斗争而得到改变。由此出发,种族和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依赖于对霸权主义的反抗。
这种反抗体现在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上。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是未完成的霸权工程,是一种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保守的低效率的保守主义,是使包括黑人在内的大多数人成为他者的极权主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霍尔在批判霸权主义的同时,仍旧坚持了阶级和种族话语的可塑性和偶然性。
斯图亚特·霍尔究竟是谁?是来自牙买加的黑人新移民还是英国中产阶级的奖学金男孩?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抑或是一直批判体制的黑人他者?他的身份如此多重,以至于我们无法从其数量繁多的学术著作和自我叙述中找到一条完整的逻辑线索来串起他丰富多彩的一生,从而对其身份进行清晰的界定。正如霍尔常爱说的那样:“两者都是。”他的身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兼容。正是他这样的特性,构成了后人研究其思想的最引人入胜之处。斯人已逝,精神常存。霍尔思想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一座宝藏,将继续熠熠发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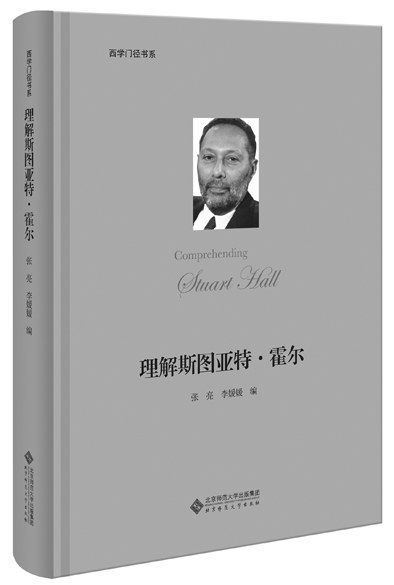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